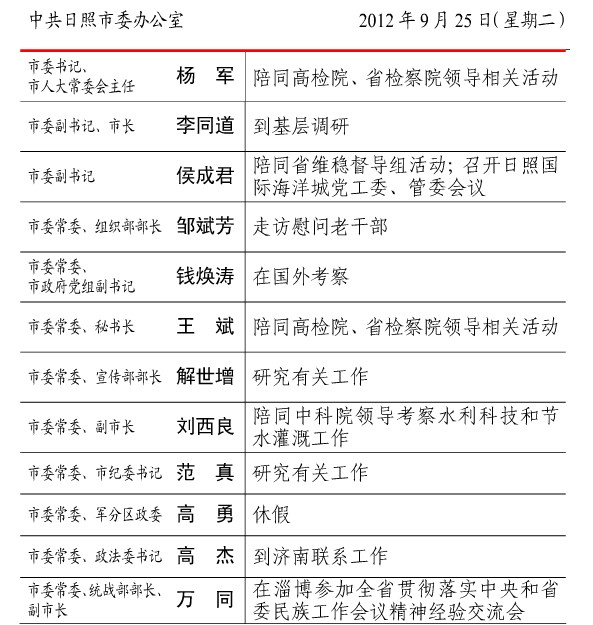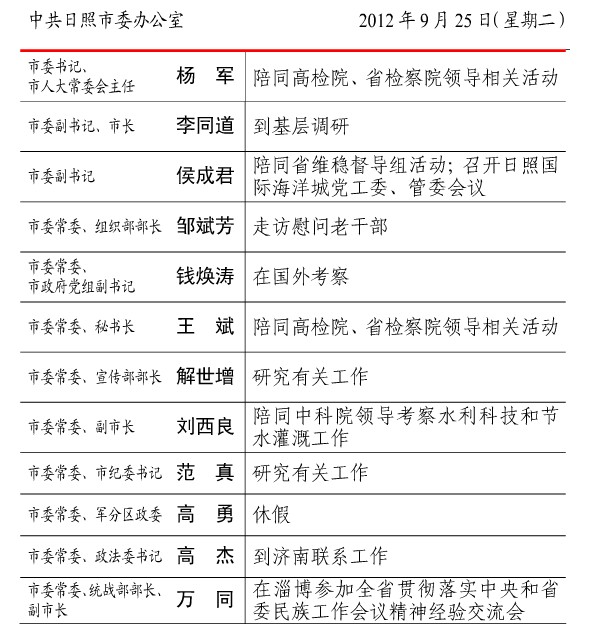徐扬的姑苏繁华图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擅长人物、花鸟草虫的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用了24年时间创作了一幅名为《盛世滋生图》,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反映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又名《姑苏繁华图》,进献乾隆皇帝,以赞乾隆盛世。这是继宋代《清明上河图》后的又一宏伟长卷,全长1225厘米,宽35.8厘米,比《清明上河图》还长一倍多,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画面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介狮和两山间,入苏州郡城、经盘、胥、阊三门,穿山塘街,至虎丘山止。作者自西向东,由乡入城,重点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苏州)、一街(山塘)的景物,画笔所至,连锦数十里内的湖光山色、水乡田园、村镇城池、社会风情跃然纸上。
粗略计算,全幅画有各色人物1万2千余人,各色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各种桥梁50余座,各种客货船只400余只,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完整地表现了原作中气势宏伟的古城苏州市井风貌,是研究250年前“乾隆盛世”的形象资料,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画卷布局精妙严谨,气势恢宏,笔触细致,十分细腻地刻画出了江南的湖光山色、田园村舍、阊胥城墙、古渡行舟、沿河市镇、流水人家、民俗风情官衙商肆,描绘了苏州城郊百里的风景和街市的繁华景象,形象地反映了18世纪中叶苏州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百业兴旺、人文荟萃的繁盛景象,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鲁迅先生曾将传统文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另一类是帮闲文人。帮忙文人,就是那些给主子出谋划策、位居重臣的文人;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向主子献诗献画,“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是必然的。
徐扬终于意识到,自己如果久居“画画人”之列,必将永处于卑微的政治地位中,永远做毫无话语权的家奴,永远成为可有可无的俳优。
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是,他当即向乾隆上书,希望能接续自己作为读书人的素志,参加科举,鱼跃龙门。当时,乾隆还十分赏识他的画技,就让他以国子监学生的身份参加科考。徐扬奋力拼争,可结果却依然是名落孙山。改变地位的努力失败了,他无比颓丧。可皇帝的“唱诗班”里还少不了像他这样的人才,于是,乾隆干脆钦赐他七品“内阁中书”的头衔,圆他的做官梦。
乾隆以官位为诱饵,引诱士人为自己卖力,玩弄伊等于股掌之间,这类手段,他早已运用得驾轻就熟。他知道: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利越厚,财富的多寡取决于官位与权力的大小。
他表面上反腐倡廉,并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可事实上,正是他,用官位、权力和财富吸引来一大批为其所用的依附者。许多依附者长袖善舞,纷纷给他献上“奇珍异宝”,从而有效地规避了“反腐”的利刃。
徐扬,以画家敏锐的双眼,发现了这一玄机。他也要有所动作。
乾隆二十四年(1759),徐扬一举绘制完成了《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该图以当时繁华的苏州城为背景,状写自太湖至虎丘近百里的风光山色、地理民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园林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借此来歌颂乾隆朝的太平盛世。
徐扬自称,作《盛世滋生图》的目的,即有感于本朝“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因而“摹写帝治”。而事实上,他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出于巩固自身“一等画画人”职位的需要。宫廷画家群体之中,竞争何其惨烈,使他不得不投乾隆所好,急于拿出一部歌功颂德的大作品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盛世滋生图》全长1241厘米,画心高39厘米,纸本设色。图中人物多达12000余人。河中各式舟船应有尽有,约近400条。街道上店铺林立,市招高扬,可辨认的各类市招竟达260余家。又有各式桥梁50余座,文化戏曲场景10余处,对盛清时期苏州的面貌进行了完完全全的“实录”。
然而,成也实录,败也实录。
该图成功之处,即在于不仅展现了盛清苏州的喧闹市肆,而且全面展示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佳构等丰富的内容。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典籍之缺失。内容十分详实,从提供给世人“乾隆年间苏州城市文化的丰厚信息”这一层面上来说,《盛世滋生图》堪称不朽佳作。
于是,有人为之大唱赞歌,说它堪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事实上,此种说法明显属于言过其实,单是在审美趣味方面,两图就迥异其趣。《清明上河图》的创作风格,就是将美简单净化,行内称为“遏制修饰”,继而将原本素净的元素美化。这种“理性追求简朴”的审美观,与《盛世滋生图》所极力表现的“物资丰盈”之繁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盛世滋生图》为了歌唱繁华,刻意营造出了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倒性情绪。仅棉花棉布店就画了23家,饮食副食店更是画了31家,重复的什物太多,又追求面面俱到地描摹各行各业,缺乏艺术的加工、提炼与创新,导致场景繁沓又不精致,艺术之魅力大打折扣。
而《清明上河图》,则达到了“广阔而不粗疏,缜密而不琐碎”的境界,即便是百十人与急流一起骚动的过桥场景,在奏起最激越澎湃的乐章中,画家张择端也依然保持着演奏家的冷静,画面人物张驰有度,显现出“劲发而不露”的内敛品质。
街头人物,也被画家用极富表现力的笔触勾勒得个性纷呈。那个城门前桥头行乞的孩子,印证了繁华背后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领域,恰恰是徐扬万万不敢涉及的禁区。
绘画艺术的一个最主要的命题,就是要在平面上诱发我们对物理及精神空间的想象。《清明上河图》结尾处有一个人,手提着盒子,肩背着包裹,回头向画面结尾方向张望,他在问路,却又为何回首?他在问些什么?又在盼些什么?这一景象留给了读者永恒的想象,体现出张择端高超的捕捉瞬间的能力与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而《盛世滋生图》中,除了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的民众,就是“万卷书香,受业于先生之席”之类的图解概念,再就是格式化的戏剧表演与婚礼场面,在层出不穷的“视觉盛宴”中,读者的想象空间被挤压得逼仄无比。
具有创作个性的艺术作品,意味着它的内容和形式包含着某种新鲜的、个别化了的、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显露出艺术家对生活、对美的独特发现与个性化处理。只可惜,徐扬为了迎合乾隆“尤重实录”的审美趣味,抑或被长期的“摄取实景”的创作范式禁锢了思维,终于与民间画家的那种对美的独特发现与个性化处理的创作方式擦肩而过,最终浪费了一次从艺术审美的高度——超越清朝宫廷纪实绘画整体水平的天赐良机。
如果说徐扬创作《盛世滋生图》,表现苏州市民生活的风俗图景,尚存在一丝自由的创作冲动,尚洋溢着思念故园的创作热情,那么乾隆二十九年(1764),创作《乾隆南巡图》,则完全是奉命行事了。由于卷帙浩繁,徐扬的工作持续了六年时间,其中有多少次画出小样呈供御览,有多少次秉承乾隆的意志进行修改,他已经记不清了。
凭借着在“物理”、“画理”的空间转换与陈述方面显示出来的出色的把握能力与融合能力,凭借着沉稳凝炼、细腻绵密的用色,凭借着平远的构图与优游从容的意趣,徐扬又一次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
与《盛世滋生图》相比,《乾隆南巡图》在艺术水准上又有了进步,然而,这部作品依然没有摆脱乾隆阴影,依然没有突破清代宫廷纪实画的窠臼——不过是将当时的具体场景原样摹写下来而已,只具历史价值,毫无艺术创新价值可言。
对于这样一种趣味,当时有一位民间画家——沈宗骞,在他的传世名作《芥舟学画编》中,就毫不客气地评价说:
“非古贤事迹及风雅名目,而专取谀颂繁华,与一切不入诗料之事者,谓之图俗。”
因此,沈宗骞不屑与宫廷画家为伍,他贫居乡野,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想。
乾隆三十七年,徐扬“内阁中书”六年俸满,奉旨记名以“主事”任用,改任内阁典籍。乾隆四十年,又实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在刑部,创作个性已经全然泯灭的徐扬,依旧用画家的敏锐双眸,去发掘案卷中的纰漏,他还想在政界干出一番作为。然而,中国官吏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政绩,而在于跟上级的密切程度。
可是,徐扬的上司根本不把徐扬放在眼里,因为他不是出身于科举正途,连“举人”的名分都是皇帝恩赐的。帮忙文人依然鄙视着帮闲文人。而此时,乾隆的欣赏口味又发生了变化,他已经腻味于纪实绘事画的宏大排场,开始着迷于纪实人物画的温柔敦厚了。徐扬早已成了皇帝的秋风团扇。
他该走了,为了追求一只虚幻的“铁饭碗”,他失去了创作个性,失去了自在生活,也失去了良性发展自身特长的万千机会。他那愁怨而憔悴的身影,在斜阳的伴随下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