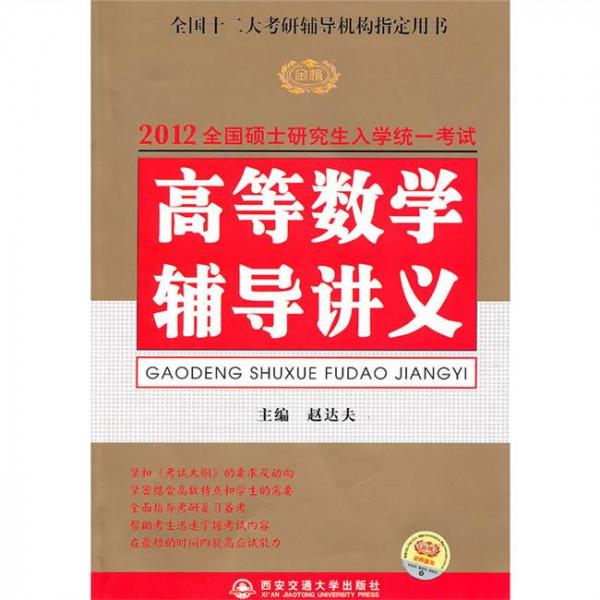赵毅衡广义叙述学 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建立一种广义叙述学
文本作者将此文的主要内容,在几个学校做过演讲,也在叙述学的专业会议上做过发言,得到的是一片沉默:没有人赞同,却也没有人反驳,更不用说著文支持或驳斥,似乎这个建议中没有任何值得争论的内容。但是对一些小说叙述学中的细节问题,西方学者已经讨论过多年的问题,中国学者的争论却很热烈,争论的中心点是:究竟谁对西方权威的理解正确。
这个局面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叙述学界还没有准备面对一个全局性的新课题。原因倒也简单:西方叙述学界尚未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真的必须留在一百年来的旧习惯之中,只能让西方人先说,我们才能接着说、跟着说吗?难道中国学界至今没有提出新课题,思考新课题的能力?
1.“最简叙述”的定义
最近二十年在各种人文和社会学科中的“叙述转向”(The Narrative Turn),声势浩大,应当是历史悠久的叙述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契机,从目前局面看来,反而给叙述学带来难题。
从叙述学向“广义”的转变,类似一个世纪前语言学向符号学的转变:哪怕小说依然是最重要的叙述体裁,从此必须建立在一般化原理的基础上,但是这个一般化,将把叙述学转变为人文学科共享的基础。新叙述学,不过自称是后经典叙述学,还是后现代叙述学,还是“多种叙述学”(narratologies)都必须迎接这个挑战。
但是“新叙述学”有没有决心为涵盖各个学科中的叙述,提供一套有效通用的理论基础,一套方法论,以及一套通用的术语来呢?新叙述学家有没有迎接这个挑战的愿望呢?
对此,新叙述学家各有不同的回应方式。赫尔曼在为《新叙事学》一书写的引言中认为“走出文学叙事……不是寻找关于基本概念的新的思维方式,也不是挖掘新的思想基础,而是显示后经典叙事学如何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1]弗卢德尼克在专门讨论叙述转向时,态度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容忍。她说“非文学学科对叙事学框架的占用往往会削弱叙事学的基础,失去精确性,它们只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叙述学的术语”。[2]
按这两位新叙事学的领军人的看法,所谓“后经典叙事学”依然以小说叙事学为核心,只是从各种其他叙述 “汲取养分“。而本文的看法正相反:叙述转向是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在广义叙述学建立之后,将会是小说叙述学“比喻地使用(广义叙述学的)术语”。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叙述的定义,“扩容”以涵盖所有的叙述。要改变定义,就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新叙述学的领袖之一费伦斩钉截铁地表示:“叙述学与未来学是截然对立的两门学科。叙述的默认时态是过去时,叙述学像侦探一样,是在做一些回溯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实在已经发生了什么故事之后,他们才进行读听看。
”[3]另一位新叙述学家阿博特也强调:“事件的先存感(无论事件真实与否,虚构与否)都是叙述的限定性条件……只要有叙述,就会有这一条限定性条件”。[4]
过去性,是小说叙述学的立足点,而要建立广义叙述学,就必须打破这条边界。远自亚里士多德,近到普林斯,都顽强地坚持过去性边界,但是他们已经遇到难题:为此不得不排除现代之前最重要的一种叙述类型------戏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mimesis),与叙述(diegesis)对立,戏剧不是叙述。二千三百年后,家普林斯在《叙述学辞典》中提出过一个对叙述的最简定义:“由一个或数个叙述人,对一个或数个叙述接受者,重述(recounting)一个或数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
普林斯补充三条说明:第一条就是叙述要求“重述”,而戏剧表现是“台上正在发生的”,因此不是叙述[5]下文会说到,排除“正在发生的”戏剧,也就排除了影视,电视广播新闻,电子游戏等当代最重要的叙述样式。
有的叙述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犹疑,自相矛盾。阿博特认为哪怕“现场报道的赛事或新闻”也是过去:“我们在阅读或听的同时也能意识到报道中介涉及的瞬间,这些瞬间发生在时间的踪迹从随时消失的绝对现在进入表达它们的媒介之时”。
[6]阿博特这段话是说:从“绝对现在”进入“媒介表达”有个“瞬间性的”时间差,使现场也成为过去。但是不久,他就开始抱怨电子游戏的叙述,认为与“委员会会议,战斗,大会,有咖啡间歇的研讨会,滚石乐,派对,守夜,脱口秀”等等相同,都是“体现了一种对叙事已知性的烦躁不安”。[7]那么到底叙述学要不要坚持“过去性”?
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叙述意识的本质,而且关系到接受方式。现象学着重讨论主体的意识行为,讨论思与所思(noetico-noematic)关联方式,利科把它演化为叙述与被叙述(narrating-narrated)关联方式。
利科在三卷本巨作临近结束时声明:关于时间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time),与关于意识的时间(time of consciousness),实际上不可分:“时间变成人(human)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形式变成时间经验时,才取得其全部意义”。
[8]这样,叙述的接受如何相应地重现意图中的时间(把叙述“变成人的时间”),成为他们留下最大的理论困惑。
经过叙述转向,叙述学就不得不面对已成事实:既然许多体裁(例如广告,例如现场转播)已经被公认为重要的叙述体裁,那么叙述学必须自我改造:不仅能个别对付各种叙述门类,也必须有能总其成的广义理论叙述学。门类叙述学,很多人已经在做,有时候与门类符号学结合起来做,应当说至今已经有很多成果。事实证明,门类叙述学绝不是“简化小说叙事学”就能完成的:许多门类的叙述学提出的问题,完全不是旧有叙述学所能解答的。
我个人认为,从叙述转向波及的面来看,广义叙述学对叙述基本特点的描述,叙述的最基本定义,应当既考虑叙述的发出,也考虑叙述的接受。本文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讲述,就是叙述,它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
1. 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
2. 此符号链可以被(另一)主体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
本文的这个定义虽然短,牵涉到八个因素:叙述主体必须把人物和事件放进一个媒介组成的符号链(即所谓“情节化”),让接受主体能够把这些人物和事件理解成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文本。情节如何组成才成为有意义的,实际上接受者重构方式的产物。
这条定义的关键点,是排除从柏拉图开始的叙述必须“重述”这个条件,被叙述的人物和事件不一定要落在过去,事件中的时间性------变化,以及这个变化的意义------是在叙述接受者意识中重构而得到的。也就是说:时间变化及其意义是阐释出来的,不是叙述固有的。这样就解除了对叙述的最主要限定,叙述转向后出现的各种叙述类型,现在都可以占一席之地。
2. 第一种叙述分类:虚构性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我们文化中各种体裁的叙述,进行最基本的分类。
叙述研究首先遇到的最基本分野,是虚构性/事实性(非虚构性)。要求事实性叙述必须基于“事实”,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它期待接受者理解它是“事实性”的:“事实”指的是内容的品格;所谓“事实性”指的是对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联方式,即接收人把叙述人看作在陈述事实。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内容不受叙述过程控制,要走出文本才能验证,而理解方式,却是叙述表意所依靠的最基本的主体间性。
有一度时期,“泛虚构论”(panfictionality)曾经占领学界。提出这个看法的学者,根据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所有的感知都是被语言编码的,而语言从来总是比喻性的(figuratively),引起感知永远是歪曲的,不可能确切(accurate)”[9]也就是说,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本质”使叙述不可能有“事实性”。
这个说法过于笼统,在历史学引发太多争议。例如很多历史学家尖锐地指出,纳粹大屠杀,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历史学虚构。[10]
叙述的“事实性(非虚构性)”,是这些叙述体裁理解方式的模式要求。而不是其文本固有品质。法律叙述,政治叙述,历史叙述,无论有多少不确切性,叙述主体是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编制的文本,接受者也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重构叙述。
既然是事实性的:叙述主体必须面对叙述接受者的“问责”。例如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说她在波黑访问时受到枪手狙击,她就必须在记者追问时对此负责。如果真有此事,那么民众或许可以从希拉里的叙述中读出伦理意义:“此人有外交经验和勇气,堪当总统”。希拉里把叙述体裁弄错了,就不得不承受其伦理后果:哪怕不是有意撒谎,至少容易夸张其词,不具有总统品格。
《中国日报》环球在线消息2008年2月5日报道,希拉里做了个关于未来的叙述:“如果美国国会无法在2009年1月(下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前结束伊拉克战争,我作为总统也将会让它结束。”这话是否虚构?如果从问责角度,可以说既是又不是虚构:2009年希拉里是否能成为总统是个虚拟的问题,所有的广告,宣传,预言,承诺,都超越了虚构性/事实性的分野------它们说的事件尚未发生,因此是虚构;它们要人相信,就不可能是虚构。
因此这些关于未来的叙述,是一种超越虚构/非虚构分野之上的“拟非虚构性”叙述。之所以不称为“拟虚构性”,是因为背后的叙述意图,绝对不希望接收者把它们当作虚构,不然它们就达不到目的。
因此,按虚构性/事实性标准,叙述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1. 事实性叙述: 新闻,历史,法庭辩词等;
2. 虚构性叙述:小说,戏剧,电影,电子游戏等;
3. 拟事实性叙述;广告,宣传,预言等;
4. 拟虚构性叙述:梦境,白日梦,幻想等。
这个分类卷入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虚构性叙述,本质上就是谎言,因而不能以真假论之。但是叙述的底线必须是“真实性”的,不然无法被接受被理解。因此虚构叙述必须在叙述主体之外,必然虚构一个叙述主体,能做一个“真实性”的叙述:讲话者(作者)只是引录一个特殊人物(叙述者)对另一个特殊人物(叙述接受者)所讲的“真实的”故事,呈现给叙述接受者(读者,听者等)。
例如斯威夫特《格利佛游记》是虚构,但是格利佛这个叙述者对他讲的故事“真实性”负责;例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虚构性叙述,但是其中的两层叙述者雷博士和亨伯特教授对叙述之“真实性”负责。
这不是说亨伯特的忏悔都是事实,例如亨伯特说自己被洛丽塔诱惑就很不可靠。但是他的忏悔是作为“真实性”的叙述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