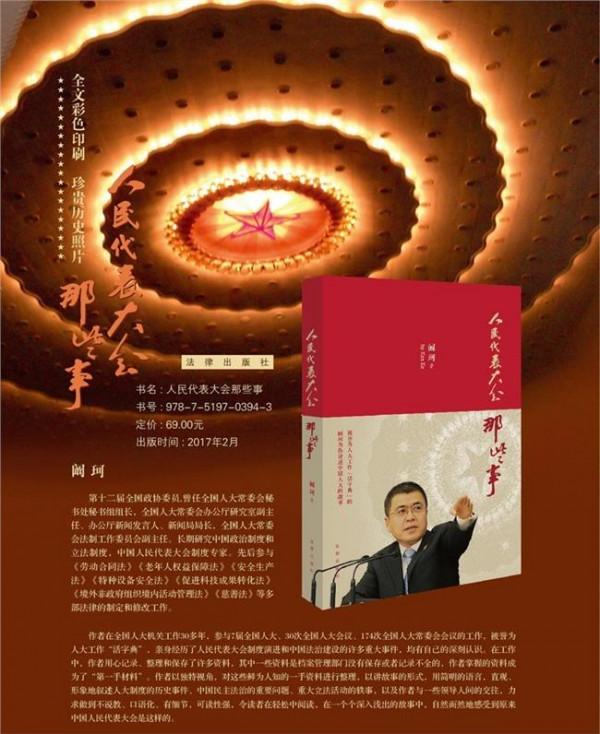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 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方法及其限度
主持人简介: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主讲人简介: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秦前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秦前红教授在中国宪法学科中是最有现实感的,是与时代脉动最相关联的宪法学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方法及其限度》涉及到当今中国大家都关注的主题,这个主题涉及到政法问题、宪法学、政治学,而且可以上追到古希腊、罗马到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近代以来苏俄的政治和我党49年以来的政治,与检察权、检察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权力需要监督,那么如何实现权力监督,这是30年来我国政体国体面临的重大问题。最近有关方面对国家监察制度议题的资助,秦教授正好把他具有现实感的宪法学研究深入进去,在这个领域中,秦教授是最主导性的理论推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个集中反腐败机构。对比马拉松式的司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几乎是横空出世的,是一场百米冲刺!尽管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目前的反腐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至少解决不了反腐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问题。
面对反腐“去库存”与结构性腐败之间的张力,如何对腐败增量做到零容忍?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理论上探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改革逻辑非常必要。
一、问题的引出:试点取样与制度取样
从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取样来看试点考量,浙江、山西、北京等三省市分别具有民企、国企与政经中心等特点。
首先,浙江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中国改革开放伴随一个命题:“腐败是否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改革开放要重视民企的贡献,处理好民企的负资产、负能量问题,不要纠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有一项数据显示,打击腐败力度越大,民企投资热情越小。
按照这个数据,打击腐败的后果之一就是民企不投资,而民企不投资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因素。在浙江试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可以考量民企投资与打击腐败的关联关系问题,并积累与民企相关的反腐经验。
其次,山西从经济上讲是资源依赖型与国企垄断型的省份,同时是腐败的重灾区,在山西试点可以积累国企反腐败的经验。最后,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腐败机构通常面临政治地位、政治能量都远高于自己的腐败组织和个人,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反腐也要通过试错积累经验。
在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方面,我们该如何建构,建构过程中又该如何吸取古今中外的智慧,进行制度取样?
我认为,国家监察制度主要可以有三种制度取样。
第一种是自秦以来的御史制度。这个制度到明朝发展到巅峰,出现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监察制度自古有之,从秦御史制度开始,中华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延续,科举制度、言官制度、监察制度,学统、政统、道统相区隔的制度等,都功不可没。御史监察制度最先的设计是异体监督,后来蜕变为雌雄合体(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合一),蚕食了乡绅自治制度,蚕食了学统、政统与道统相分离的思想自治空间。
第二个制度模板是孙中山的监察院制度。在“五权宪法”的制度架构下,设置监察院承担监督职能。按照孙中山的设想,监察院之所以必要,在于限制权力的专横,以打破过去王朝兴替的周期率。孙中山设想搞监察院的时候,有几个前提是不存在的:独立司法不存在,新闻自由不存在,社会支持不存在,因此才要去搞监察院。如果有了这些制度,这个监察院就是可有可无的。
第三个制度取样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廉政公署高效而权威,但香港回归后的廉政公署制度有其发挥作用的特定条件,我们在进行制度借鉴时必须明察,不可率尔操觚。
以上三种制度模板各有利弊。概言之,中国大陆不可能沿袭历史上的御史制度,不可能沿袭台湾的监察院制度,不可能沿袭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根本不可能照着一个固定的模板去设计国监委。正是由于三种制度模板各有利弊,以至我们现在选择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样一种制度。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在逻辑推演上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
二、两种改革的逻辑与结构性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教授提出了两种改革逻辑。其一,规范主义改革逻辑,即尊重宪法和法律权威,尊重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保护人权。其二,政治制度变革逻辑。变革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自古以来,变革莫不是变法,于是打破条条框框与领导层宣称的“重大改革与法有据”的法治思维的改革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
那么,如何妥善处理这种结构性张力?若干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潜藏着,今天又浮现出来。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良性违宪”论。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反对良性违宪,上海文史馆郝铁川教授赞成良性违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后,必然会出现良性违宪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又浮现出来,需要认真对待。(相关观点具体可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编注)
其二,权力属性。近代立宪主义发展后,尽管国家机关不一定完全对应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基本还是一个权力的三分模式。台湾“监察院”演进的时候,先被确定为一个政治性的民意机构,后强调独立性,成为一种准司法性质的权力。
国务院系统的行政监察,加上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职务犯罪侦查,再加上党内的纪律检查,国监委拥有这么多职权之后,这个机构差不多成了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党权于一体的机构。立法机构的性质是表达法意、设定议事规则,行政机构的性质是执行,司法机构的性质是判断,不同性质的机构有不同的运行机理和相应的组织机构规则。未来的国监委如何界定其性质并建构其运行准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其三,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会“熔断”司法改革吗?过去的司法改革设计从来就没有要把检察院反贪、反渎、职务犯罪侦查的职权拿走,而且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改革方案都没有这么写。但现在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意味着相关的司法制度都要重新设计,与检察制度相关联的审判权、侦查权问题也要重新设计。
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改革,其理论研究似乎从来是热闹不深刻。过去的检察理论对检察制度的定位绝大多数是不准确的。对应于检察院的自侦、自捕、自诉权,过去曾有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叫人民监督员制度,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写入了四中全会报告。过去,人民监督员是检察系统一家的事情,四中全会后搞成司法行政系统、检察系统两家的事情。全国的人民监督员规模已有数以十万计。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为了解决检察院自侦、自诉、自捕的问题而生的,当上述三项职能转而隶属于国监委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跟着转入国监委、重新包装“上市”,还是就此休止,确实需要好好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给司法改革带来的问题还有:司法改革本身即有改革的碎片化问题(比如说,最高人民法院设计法院系统的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设计检察系统的改革,公安部设计公安系统的改革,司法部设计律师业务方面的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现有司法改革可能更加难以为继,目前已经出现了制度客观效果与制度初衷相背离的情况。
举例来说,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是十八大以后司法改革中重要的战略举措,走了很多程序,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试点。
公益诉讼交给检察院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考量,检察院的自侦权是一个支撑公益诉讼的重要武器,检察院可以通过反贪、反渎、职务犯罪侦查将公益诉讼强力推进。现在检察院被剥离了上述权力后,其公益诉讼如何继续顺利进行,这也是未来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大难题。
另外,如果国监委的性质不定,也会带来一些制度设计上的难题。如果国监委的职权只是行政权的性质,那么它的行动当然得接受司法审查;如果国监委行使的是司法侦查权,那么它得遵照《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要求,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司法改革要求党政机构不能干预个案,而包含党的纪检权力的国监委,其主要职能却是查处个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又如何处理?
三、民主与法治并举必须成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前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体来说是一个法治改革的思路,但其实应当民主与法治并举。区别人治、法治的标准,就是能不能管住一把手,管得住一把手的是法治,管不住一把手的是人治。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之后,在我国,法律权威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不匹配。
四、监察全覆盖及其限度
要达致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必须恪守法律,即监察机关须尊重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并须恪守审判独立的宪法原则。
第一,全覆盖问题。国监委讲的全覆盖,是指凡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公务人员,只要是拿国家工资、接受财政供养,就都在受监督范围。我做了个估算,中国大约有8000多万财政供养人员。按照刑事犯罪学的原理,查一个人至少影响三个人,那么监察覆盖8000多万财政供养的人,理论上至少影响到两三亿人口。
全覆盖的第一个问题,如何监督人大?人大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是,其他所有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那么国监委的监督,到底是监督人大的什么?我以前提过:可以监督个人不能监督机关;可以监督人大的工作人员(如人大内设的宣传处、政研室、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不能监督人大代表。
另外,中国的人大除了其特殊的宪制地位,还必须遵循近代以来的代议自治原理,通行的包括规则自治、机构人员自治、纪律惩戒自治。中国的人大当然也是一个代议机构,能够逃脱代议机构的一般规律吗?
如果全覆盖可以监督人大代表,那么人大代表的言论保障权、人身特殊保护权怎么去实现?还有一个难题,中国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不许监督人大代表,就意味着那些具有党政职务的人不能纳入国监委监督范围。那么上述理论是否要做一个修正,即不许监督开会期间的人大代表?
第二,中国的制度架构中有自治制度的设计,自治分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的基层自治。中国多年来出现了“上面万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所有社会管理职能向基层延伸,所有的村委会干部,所有的村长都变成了吃皇粮的。那么是不是要把村长、村干部都要纳入全覆盖的范围?监督怎样覆盖基层民主自治?如果覆盖后,自治空间如何保持?
第三,政协的领导是财政供养,但是政协毕竟在法律地位上不是一个享有公权力的机关,不是国家机关,为了全覆盖,那么是否就要让政协改变性质,变成国家机关?全覆盖对司法机构的人员怎么监督?未来的国监委可不可以对办案中的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早些时候台湾是可以的,后来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一定会损害独立司法,因此,现在台湾的监察院仅仅是对司法人员的违纪、伤风败俗行为进行纠举,对独立司法权是不可质疑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不是也考虑到了与独立司法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
第四,修不修宪的问题。有些学者主张,依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由全国人大制定“国家监察法”即可。我认为,不能仅仅制定一部单行法,有关问题还需要通过修宪来解决。因为对《宪法》第六十二条,不可用文义解释,而必须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
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所指全国人大可以制定有关国家机构的法律,仅仅是说,可以将宪法上已经有的机构通过立法将其职权具体化。而改变一个政权组织形式,新增一个机构,必须是宪法保留的问题。
第五,调查权问题。这是整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里最拉锯,也让社会最聚焦的问题之一。开始仅仅是宪法与行政法学者之间的争辩,后来基本上把很多部门法学者都拉入战局了,现在已经打成一团。一个很简单的关注点是,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交国监委后,国监委有了12项权力,对物的方面可以去扣押、冻结,对人的方面可以去留置。
那么,调查权究竟是行政权的性质?还是司法权的性质?有人说,这与我何干?但其实,调查权的性质、属性定位,关系到刑事诉讼法可不可以进入这个空间,关系到律师能不能介入。兹事体大,律师不能介入,是不可思议的。
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很多精细化的研究。比如,这个调查权是单纯的行政权,还是单纯的司法侦查权,还是两种属性都有?或者要分阶段厘清性质?查党内违规的时候是党内纪检调查权,查行政违纪时是行政调查权,走司法程序的时候是侦查权。
如果完全定位为行政调查权,那么取证可否作为刑事诉讼法证据,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可以用行政强制措施?还有,留置的决定批准权在谁手上?近日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对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郭海进行的调查,已经暴露出上述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调查权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犯罪领域,否则会制造人权灾难。
第六,审计制度何去何从?最先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时候,是想把审计制度并入国监委,采取监审合一模式。六中全会公报强调了政协、人大、国家监察、审计四大监督。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审计监督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犯罪线索的手段。
未来国监委与审计部门的张力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点。另外,把行政监察系统并入国监委后,行政部门还需不需要监察系统?监察系统并入国监委后假如只履行一个廉政监察职能,如何保证行政系统有执行性?还涉及行政效能监察,行政效能监察如何设计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最后,检察机关部分机构和职能转到国监委后,检察院在宪法上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检察院之所以称为法律监督机关,那几项职权起了重要支撑作用,当它们被拿走后,检察院还叫法律监督机关吗?
(本文据作者于2017年4月2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张元济法学讲座”第二讲中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由作者本人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