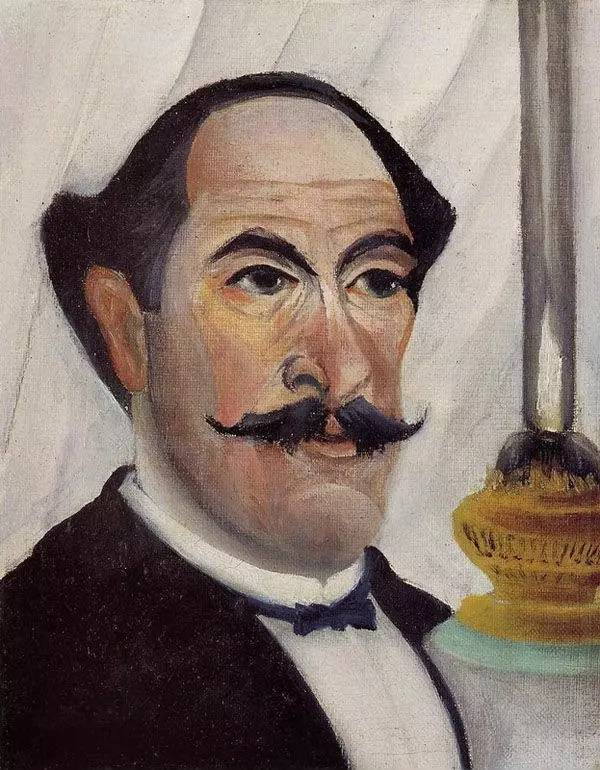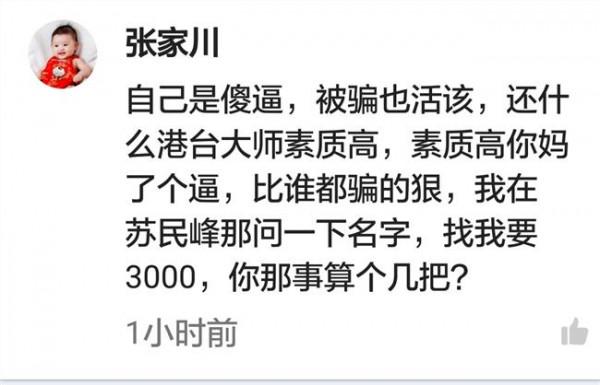陈丹青张大春 陈丹青、张大春、刘瑞琳谈理想国文化沙龙
全球的新浪网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文坛开卷》,我是文坛。在出版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人和书的相遇,他们一直在默默坚守着他们的出版理想,说到这群人,其实就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嘉宾是刘瑞琳老师和北京贝贝特。今年是北京贝贝特十年,贝贝特出版了一系列好书,今天还有两位嘉宾张大春老师的《小说稗类》,还有陈丹青老师的《荒废集》、《退步集》续篇等等,十年之际在北京举办理想国的年度文化沙龙,今天一起谈谈大春哥还有丹青老师的新书还有理想国年度文坛沙龙。
丹青老师是第一次来到《文坛开卷》,特别关心丹青老师的新作,听说最近也要在贝贝特出来新作是关于写鲁迅的。
大春哥先谈。
大春哥先说说你的这次,因为《小说稗类》在几年前已经在贝贝特出版过,这次要重新出一个精编版,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这个书在台湾已经是15年以前出版的,可是后来又增订了大概一倍的篇幅,到了北京在广西出版社贝贝特这边出,我就想说是不是应该再增加一点内容,还在琢磨。主要的,我关心的是自己作为写小说的人,对于自己从事的事,应该有一些想法,因为在台湾过去数十年来,所有的文论,几乎全部由学院的教授们,研究者们或者批评家们,他们从国外移译而来,也就是说把西方现成的某些理论看能套的就套,不能套的把头割一割,想办法戴上去象样。
这个在整个华文语境里,包括叙述策略,包括语言素质也好,甚至写作的动机,未必吻合原先的理论的发明。
身为当代人,一直在创作,总对创作这件事情可以有一点反省。我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把《小说稗类》这个书就写成了,以专栏的形式来写的。简单说是创作者应该对自己所体会到的某一些包括工匠技术或者某些美学有清楚的认知,吾日三省吾身,小说小说,大概是这样。
丹青老师以前关注大春老师的作品吗?
我很荣幸在1989年就认识。
对刚才说的《小说稗类》有读过吗?
我读大春的小说,第一很有快感,他的语言,一上来说话就像刚才的男中音,特别有兴奋感。但是我一读下去一直有自卑感,尤其前年在听他上课,我坐在下面听他一堂课,我的自卑是理由的,而且远远不够自卑。
他什么让你自卑了?
他分析一个字史诗里一个字,就讲了一堂课,中国的大学教育里,中文教育里我相信没有这样的老师,最一流的优秀老师里未必能这样讲课,我这样要得罪很多老师,但是好像有资格这样说,因为我接触过这一层面的老师。大春是职业的写手,我是业余的。第二他的文类牵涉很广,小说兼文论或者历史小说,他都写,他是横跨好几个领域,所以我读的时候,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您最喜欢他的哪一部小说?
我喜欢他历史小说,有点像重新写过的历史小说。
比如说呢?像《聆听父亲》算不算历史小说。
《聆听父亲》对我来讲像家传一样的东西,当然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有一些内容是靠我六大爷在他生前给我写的一个家史,叫《家史漫谈》,根据这个漫谈做一些口头查访,包括我姑姑,我妈妈,稍早一些,我父亲还在的时候,我们俩父子俩经常谈这些,我给它编织在一块,很难说它是小说,但是很难说是历史。
这部材料对我来说,回头去看见我这个人以及我面对的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怎么向他去诉说五代以上包括我在内这些老人们曾经给予的一些教养,看起来有点小说的气味,我宁可把它当做是一部唠唠叨叨的散文,讲给孩子听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就是一种小说写作的形式。
刘老师和大春哥有没有发现,丹青老师今天来一直属于特别谦虚的状态。我记得当时在《退步集》续篇的时候,写单篇的时候,在鲁迅文学纪念馆写的,当时是一个讲座,一上来也是这种感觉,我只是鲁迅的一个读者,我不是专家。
真的不是谦虚,谦虚是你有这个水准,但是你把他放低一点。我真的在我这个水准上讲这个事情。刚才你说到《聆听父亲》,我的感动除了我刚才说的那部分,还有我很少见到在大陆这边的写家,在书里面他是好儿子,同时又是好父亲,刚才我们一路过来,他一直谈他的女儿,谈他的教育问题。
很多我的同类也会跟我说起他们孩子怎么样,但是那是另一种说法,他关心的女儿是关心所有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又聆听父亲,其实不是聆听父亲,是聆听更广义的上几代人。
所以不光是非常能写的人,写得很好看的人,同时后面真得有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在这儿已经很久,你想做一个好儿子,想做一个好父亲,未必知道怎么做,我从来不管我女儿的功课,没有好好听过我的父亲,更不会写出来。
但是在他来说,我相信这个跟台湾有点关系,我去过写过一篇文章,一种德性的普遍的草根状态都还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张大春,你不会太奇怪。可是忽然在这里出一个张大春《聆听父亲》,会非常做作,很讨厌的一篇文章。在这儿会变得很真实,说不完的东西,都会很惊讶,他是这么看这件事情。
大春老师刚才说到后来的话题,丹青老师很想念,我看到那篇文章说很想念鲁迅先生,最近要新出来的这本书《笑谈大先生》,我知道之前在《荒废集》、《退步集》续篇都有两三篇写到鲁迅,为什么这次专门出了一个集资,专门谈鲁迅?
我因为是业余的写手,很多话题从来没有觉得有资格写这个话题,但是忽然有人说你来写写看,我就会做。我第一次去《笑谈大先生》是鲁迅博物馆的孙郁馆长要我去,他那个馆经常请外界的人去讲讲。我去了以后,我不想鲁迅讲什么,讲鲁迅,我有资格讲吗?这种情况下,就去讲了。
选了两个我认为可以不用去碰我不懂的东西,觉得它很好看,很好玩就讲了。讲了以后,我以为讲过就讲过,他的孙子周令飞一直叫我,叫了我五次,陪他到各地去演讲,这样有另外五篇,加起来是六篇,时间是从05年到08年左右,共三四年。
北京、长沙、上海都讲过。分散在两本杂乱的集子里,有些读者会说,他手上有《退步集》续篇,演讲在那里,问我,你讲鲁迅在哪里,有些读者很粗心,发现没有在手边,有些读者读过,说能不能出单本,香港的一个出版社曾经把前三篇写了一个单本,现在算起来到今天有五年,六篇讲完,没有再讲过,就出一个合集,不知道有谁愿意读。
读过您写过单篇的读者,认为您笔下的鲁迅是还原了鲁迅的本性,您这么看吗?
没有人能还原哪个历史,我们都在想象这个人。我给出我自己的想象。我相信任何一个台湾的读者如果对鲁迅感兴趣,台湾的读者香港的读者都谈过他们心目中蛮真实的鲁迅,一定跟我说的不一样,我曾经想过写另外一篇文章,因为台海隔阂有60多年,这60多年足够出现一个两岸又非常不同的文化,跟民国非常不同,尤其是话语上不同。
两岸三地的人,比方说一个老民国人,一个现在的台湾人,一个现在的大陆人,三个人一块谈鲁迅,谈胡适,谈陈独秀,谈所有五四时期的人物,会谈三个鲁迅,而且未必说哪方谈的是假的或者完全不对的,最后谈出来不是三个胡适,三个鲁迅,是谈出三地三个时间段里,文化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很难涉及一个是非,但是我相信我跟大春一起来谈胡适,当然我懂胡适很少很少,但是一定跟我想的胡适不一样,他会很惊讶我这么看胡适。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丹青刚才的发言涉及到从鲁迅一个人或者一代人或者比一代更广泛的近代历史印象。刚才所涉及的世代是中国跟世界交往之后,在寻找一个文明标准,并且试图建立一套文明的过程里。我看丹青的焦虑不是针对一个特定国家,比如我们说马克吐温一向对他的美国很愤懑,鲁迅对他的时代中国一向很愤懑,易卜生对他所在的丹麦很愤懑,不是恨那个国家不成钢,而是这个国家的文明跟他想象和所接触的教养内容有冲突。
我发现丹青长期的关注,是对中国的文明在今天的处境到底还要回到建立新文明的坐标里找到哪些参考。比如中国在民国那段时间脱漏了什么东西或者太急功近利去掌握了德先生、赛先生之余,又失去了哪些细腻的教养内容,他长期关心的是这个。
我忽然想到,我很喜欢看胡兰成讲鲁迅,讲的不多,鲁迅那会批判中国,等于姑娘早上梳妆打扮,梳着梳着突然不高兴,觉得镜子里不好看,觉得不开心。这个对极了。鲁迅看了一定会给他说中了。我们这边讲的批判国民性,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鲁迅看了会气死,不是这个意思。
您觉得他是什么意思?
就是梳着梳着不开心。一个人在讲一个很大的事情,有一个非常生理性的,很简单的原因。
大春哥也像丹青老师这么看吗?
我早上起来不大梳妆,他梳妆时间比较久。
我没有头发可以梳。
新书里是不是要用鲁迅当时很多的照片,而且照片会很多。
总得用一点,我好像是因为画画的,总是离不开图象。比方说我说鲁迅好看,这是跟他照片有关。是那个年代我们能够看到的五四时期人物照片给我的印象,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是小孩子就会有判断,这个八字胡一弄挺好看。
现在我对图象的看法当然多得多,我总觉得有一部分,我认知的事物,实际上是图象告诉我的,文字再说没有用,他不顶一张图象。我老是说中国古代是写着写着有诗为证,我现在写着写着有图为证。有时候看郭沫若一张脸或者林语堂一张脸,在文字当中是呼之欲出林语堂是这样的性格,说不出来,图片一放,是这个性格。
这次有很多图片,让网友品读图片的时候,品读鲁迅,是这样吗?
在我谈到的人事当中,只要有图片,我都愿意放一放,假定读者当中可能有一个人可能跟我小时候一样,是这个样子。样子对我来说是性命交关。因为人类对样子的需求可能比文字要早,图象史比文字史早大概多少万年。我相信一个动物在看东西一定跟人一样,动物没有文字语言,但是他非常清楚危险迫近了,其实他是靠看来了,我到现在一直信赖对图象的辨认和判断,跟文字在一起发生,会让这本书更有意思。
说到鲁迅,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大家比较关注一个事情,同样写鲁迅的汪晖的抄袭事件,刚好是清华的老师,不知道两位老师关注过这个事情吗?
我到了上海,到了香港,到了北京,朋友们都提这个事情,我们对前后文不是很清楚,我也跟汪晖先生过去有一小段时间在香港的认识。他是一个极有发明能力的思考者。我也觉得一个人学术成就不应该单纯地从某一个个别的片段上做整体的论断。
我看到了某一些引述,我觉得他所谓的抄袭事件,其实用典式的抄袭,把那个典故放在某些论述里,或者说改变了原先典故的样貌。这个我猜想你要说他是假的,那毫无疑问在学术严格的规格上面来讲,他这样比较大名气的学者,看起来有思想家架式的人,这个错误似乎是好像伤害很大。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包括台湾的某一些随时在报章杂志上移译或者介绍西方的某些思潮、论点,甚至成套成套的理论架构的,也常常做这样的事,只是怎么样让他的借用、转用,看起来不着痕迹,并且有的时候还带点发明的意味。
我不是一个学术人,所以我没有学术规格上的严格的禁忌。用典好像也是中国人从古以来都挺熟悉,而且挺习惯的。学界有他的判断,我是平常人,我有我的判断。
您可不是平常人,你非常会用典,一肚子典,用典和抄袭是两回事情。我没有看过他的《反抗鲁迅》,我也没有看过汪晖先生的几乎任何著作我都没有看过。所有学者的文章我都没有看过,抱歉。我在他们的范围里,我无法判断这件事情是有还是没有,甚至是对还是错。
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一个职业的抄袭者,至少我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我几乎所有创作,而且可以说中年以后最重要的创作全部是抄袭,全部是抄袭经典的,古典的绘画图象,巴罗克,还有抄袭新闻照片,抄袭我所能找到的,我认为值得抄袭的图片,非常大。
而且清清楚楚告诉你这是抄袭的,会在下面标明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告诉大家我在抄袭。而且这是有道德支持的,这是后现代的被确认的一种方式,他们有个词叫挪用占有,所以在这方面,如果你可以换一个词叫抄袭占有,也可以。
我是职业的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特别喜欢抄袭,我说过我到老了,实在没有创作力,我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去临画,我刚刚从俄罗斯回来,大概抄袭30件以上的董其昌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喜欢,我没有道理,在抄袭过程中,我像董其昌一样好。
我最近在写毛笔字,写书法,也有这样的体会,我读帖大概有30年,几乎天天读,在家的时间,每天晚上会读帖,有的时候读几个字,有的时候不见得临,现在养成习惯,说话的时候手都会临。这个临感觉会让你更贴近原创者,原苏东坡、米弗,猜想他是使用硬的笔、软的逼或者是毛笔是长的笔或者转了笔以后,转了多少角度,好像比创作还要灵。
生理层面进入身体,把它再嚼一遍。我非常向往罗兰巴特用引文来写作,从不同的作者来引,他自己也没有做到,我最近刚刚做了小的尝试,去俄罗斯给画家写一个游记,在写以前,就想好了,要用所有的托尔斯泰引文穿起这篇文章来,大部分是我自己来写,如果没有他的引文,会乏味很多,我也没有资格谈这么大的俄罗斯,但是很多事情我觉得他谈得太好了,我得停下来听托尔斯泰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用得好不好,我正在写,没有写完,上篇已经发表了,下篇正在写。
刚才大概谈了作品,还谈了关于抄袭,今天很吃惊,听到丹青老师这么说,接下来还要谈很重要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刘老师一直在倾听,现在特别想听听刘老师怎么说,作为出版社,去做这么大的年度文化沙龙,真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说起来有水到渠成,因为有这么特别好的作者,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会做很多日常的都是沙龙式的互动活动,比如我们会在丹青书店,一些小的书店,一些场所做读者和作者的见面会,其实这些都是沙龙了。另外每年在北京贝贝特生日的时候,在公司里有party,有媒体专场,大家坐在一起,自由聊天,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年度沙龙。做到现在,今年开始,想把它做得更有开放性,更有社会性,才有沙龙的想法。
当时为什么不叫贝贝特,为什么要叫理想国文化沙龙?
理想国是广西师大要做的重要品牌,广西师大出版社得到同行的认可,但是是出版品牌,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或者能有更大的发展,可能要有一个更具包容性,更有前瞻性,同时内涵更丰富的文化品牌,我们就想到叫理想国,为什么选择理想国?我们感觉它应该能把跟年轻人的心相互感应,相互沟通,因为这个词是固有词。
我们现在想用它是想跟原来的意义有所区别。我们的理念是想象另一种可能。这个意思不是说理想国要倡导某一种理想或者要给人一种类似乌托邦似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比如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但是让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意思,我们觉得是年轻人愿意思考和想象的,理想国对我们来说是开放性的,每个理想都是平等的,很多很多理想聚在一起,五彩斑斓,那就是一个理想国。
所以这次活动很庞大,有这么多名家对话,包括大春老师要跟小宝老师对话,丹青老师要跟谢泳老师对话。
不一定会庞大,但是会蛮丰富,因为请来这么多人,每个人不一样。忽然他们大合唱,每个人有自己的声部。
很好的交响乐。在台湾也有印客文学营等等,丹青老师可能会参加类似的沙龙,对这次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两位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对这样的文化沙龙的形式有什么样的看法?
台湾有相当长久的有超过30年的办文学营,听起来是营,好像是军队的意思,像夏令营,是作者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在一起交流,看起来像上课,也像交流的形式,让学生有创作目的需求,也有创作动能的这些学生在实际的导演之下立刻写作。
这种写作跟一般的沙龙不同,台湾已经很多年不太有作家、编者或者是这一行里面的人,经常举办座谈会的状况,没有了。因为台湾在过去将近20年来,最主要的谈话活动都放在政治口水上,所以名嘴要不就是爆料,要不就是骂街,这也是很遗憾的。
这次到北京来,听说9月有这么一个活动,我就在想我们几时会办这样的活动,或者我们多久没有办这样的活动,真得很感慨。这是社会经济利益和某些内在的需求撞在一起,使得文化人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愿意聚在一起谈谈。
台湾曾经有这样的年代,大概70到80年代间,我还觉得蛮热闹,用你刚才的形容词是五彩斑斓。这个很珍贵的,当一个社会突然之间对某个特定的偏枯的或者非常天时的一体,有了不可自拔的兴趣的时候,一种广泛的对于美或者对于技术,这种心情会丧失。沙龙看起来会不必要。当沙龙或者是跟文化一体有关的沙龙看起来不必要的时候,这个社会很难再自豪了。沙龙比较没病,比较健康。
是一样,很奇怪。台湾是另外一种理由,因为民主了,因为有两党,开始吵架、口水,这些东西就少下去了。中国是别的原因,中国在80年代其实类似的沙龙,非正式的,或者正式的文艺沙龙非常多,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候。其实不太务实,好就好在它务虚,大家谈天马行空,人文、国家、历史、文艺这些。
到80年代末以来,被人为地很强硬地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大家转到经济方面去。这些年媒体开始又来操办这些事情,参加过几次兰州的活动,《新周刊》、《新京报》之类,去捧捧场,那大多数是颁奖活动,也是媒体必要的活动,带点广告性质和散播价值观,颁奖给一些文艺精英这些。
这个当然在美国、在一些先进国家媒体世界里都发生。我想瑞琳,贝贝特要办这个活动还是跟这个性质不一样,还是想介绍几乎从18、19世纪,从西欧一直到五四以来,差不多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过那么几段真得挺理想主义的,务虚的,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的一个聚会。
理想国的意思在我来说就是不可能,不可能才有意思,我们才会想办法。
谴责这种活动叫有谈无根。这个心态从字面就可以知道,他想叫你把根砸在那,稳稳的,别动,牢靠一点,你老实一点。可是你的根去谈往往是刺激或者激发,真得是特别的思维方式,很多历史上重大的思潮都是由谈而来。
说到这里,要说一个网友的留言,是新浪微博的网友,叫菲冷翠的涡旋,这个活动让我想起西文化运动。这是网友的留言。这次的访谈是一个直播,在新浪微博早早做了预告,很多网友的留言,时间关系只能先挑两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陈丹青老师,在《满卷西风》提到的咖啡店等等,都是你亲身游历过,玩过吗。
没有听说过《漫卷西风》,我想不出这么浪漫的名字。
我非常喜欢陈丹青老师,主持人帮我问问他会不会通过新浪微博、博客这种方式,常常地跟他的粉丝交流?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办这种活动,我在大学呆过,我非常惊讶,我从来没有见过年轻人的生活就是乏味到可憎的地步,就在这20年来,尤其在这10年来,跟文革时期的青年比,跟50、60年代我能记得中学生、大学生比,不要跟五四时期的学生,我不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在就学年龄期间曾经乏味到这种地位,像现在这样,好像没有过,可是这个时候正是年轻人最想知道世界跟年长的人交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正好这是网络时代,网络让这个情况可能变得更可怜,大家在那里找朋友,跟幽灵,跟虫子在夜里叫,你听见没有,我在这里叫。
好可怜,网络固然非常好,有活人的,作者很想见到读者,我们都在巴结读者,伺候读者,据说有人读我的书,受宠若惊。
我也愿意见到读者,像穆欣先生这么了不起的引者,想写读者论,最伟大的读者,他自己也是读者,他读前辈,读古人,我相信每个作者都是读者,他这个活动会提供至少那么几个小时,几个下午,大家见见面,见了面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但是人就想见面,很奇怪。
所以这位不但是读者,还是大春哥的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您好大春好,您在台湾的news98大书场,是否会整理成册出版?
这个书场在我频道节目里已经说了快12年了,11年了。从开台到现在,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即使不在,也预录存档,我说了聊斋、西游、三言二拍,除了三国、红楼两部名著,没有找到合适的说法,现在还在说《东周列国》,我的说法跟评书的前辈不同,他们都能背下来,我在广播里有抄本,我做一些不同的解读,我会做一些解释,包括某些字怎么用,包括文本,在语法里。
有点像国文课似的。这种形式似乎不能够拿来,直接转回去变成出版品。
有人说愿不愿意出有声的,出版碟子。看起来工具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听我节目的人,下午听了,晚上还可以听重播,之后这个声音没有了,更好。因为我们不需要用反反复复的方式,来去对这个声音感觉厌烦。
大家多多地聆听大书场,在期待丹青老师和大春老师的新书,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在这儿跟所有网友说再见了,非常期待,我个人也特别期待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办得像你刚才说的色彩斑斓。
我期待听众,来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不要那么老被动听写作者的说话,他们愿意表达自己,把自己也表达出来,多说话,不要像听报告一样,我厌恶学校里的权利关系,永远台上台下。
我们会提前从网上征集他们的问题,也希望他们现场互动。
现在年轻人都是孙子,前面坐的都是领导。我厌恶这种关系,这就把一切弄得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