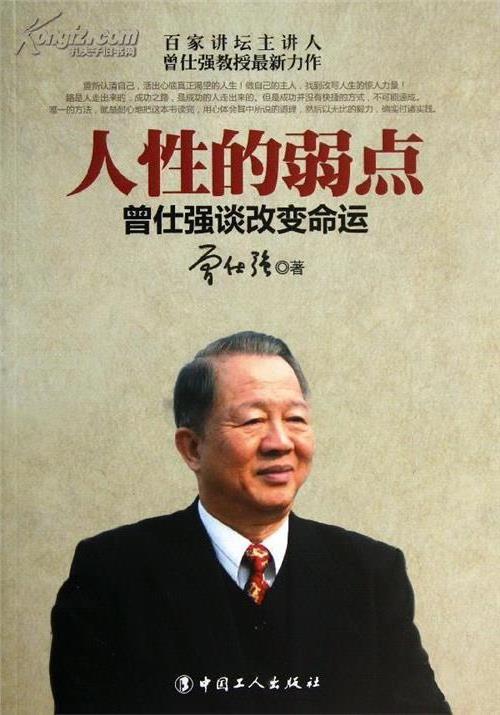改变命运的74刀 高中生捅杀老太致死曾被期望上清华
宋成今年29岁了,过去的14年间他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也许表面云淡风轻上着大学,有着美好的未来。但只有他自己明白,自己的内心究竟承受着怎样的痛苦与煎熬,14年前他捅出的74刀让他从人变成了魔鬼,就此一生被改变……
深藏着一个秘密,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看守所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
4月的南方,阴雨连绵,有些湿冷,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肤白皙,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黑得发亮。
谈话时,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并不躲闪,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细长,像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戴着手铐,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时不时张开,再用力握紧。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快14年了,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天刚黑,她推开邻居家的门,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走进院子时,她觉得有东西黏脚。在微弱的光线下,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
血案
客厅敞着门,亮着灯,朱梅英立即看到,邻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点,她吓得怔住了,随即开始大喊。
受害人浑身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脚的液体,正是血液。
警笛声很快响起。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足足有三四百”。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弯腰穿过警戒线。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尔有人走过,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隔着窄窄的巷子,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涨潮时,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尸体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那段时间,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推演案情。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高中生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扫描过许多毛发、指纹和车辙子印,这次却有些“看不透了”。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送检血滴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高中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直到宋成上中学,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陪写作业,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直到高中毕业,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读初中后,“我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闲书”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时候,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这所高中“二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当地人戏称它为“泰兴最高学府”。人们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被害人居住地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
网吧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向死者家属忏悔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死者家人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的午后,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后来王伯官以“孙女没人照看”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事实上,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就此跑掉,跑进另一种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让她别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救命”声。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声音太大,声音太大”,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
行凶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他仍觉得当时脑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见,被人知道——一个名校优等生,逃课、上网、扒别墅院子栏杆,根本解释不清楚。他绕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事发后,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7年间,院子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因为妻子遇害时,王伯官待在厂子里,他便发誓,案子一天不结,就一天不回厂房。没过几年,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鬓角冒出白发,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
案件卷宗
这14年间,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过上两遍”。与此同时,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散发着“发霉和腐臭”的味道。
尽管如此,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以后的每天早上,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清洗了沾满血的手。旁边的厨房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
双手沾满鲜血
走出洗手间时,他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便跑上二楼,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他循着声音,来到后院,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傻子”,没有“威胁”,就走出客厅,翻墙离开。事实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