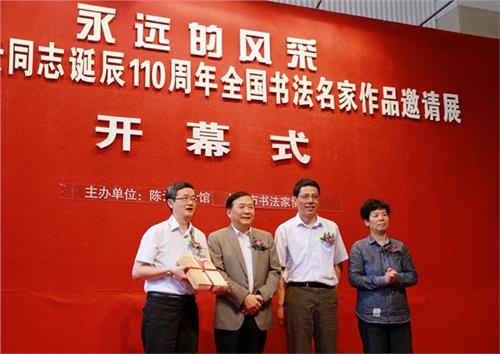周午生教学 教学有道人如其画——纪念萧朗先生逝世六周年
天津美术网讯 2016年5月27日,是著名画家萧朗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日子,本网刊发萧朗先生之子萧珑于2010年8月撰写的怀念萧朗先生的文章,同时附上16幅最新发现的萧朗先生早期作品,谨此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国小写意花鸟画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
忆父亲
文/萧珑
时至今年的九月四日,敬爱的老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百天了。在这段日子里,心里总是觉得空荡荡的,可回忆却又是满满的。眼前一幕一幕的就如同电影的蒙太奇,几十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眼前闪现。
在兄弟姐妹当中,我陪伴父亲的时间是相对较长的。因此对于他的性格,他的好恶以及他的追求有着很深的了解。在我们做儿女的心目中,母亲是慈祥的,而父亲却是严厉的。在父亲步入老年之前,由于平日里他不是沉醉于他的艺术就是忙于工作,因此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
然而,对于父亲那双总是表情严肃的眼睛,我们确是非常熟悉和在意的。和一些传统的家庭一样,我们的家教很严。从小我们就被父母告诫,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说话、吃饭、走路、睡觉、接人待物等等都要有规矩,而且这些规矩都往往是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
我小时候的一天,晚饭是母亲最拿手的烙饼。由于我不喜欢带有焦皮的,就顺手在一沓饼中翻了几下。
父亲当时就火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扔,一声不吭的转身离去。后来听母亲说父亲以为我是在挑饼的大小,所以生那么大的气,以至于连饭都没吃。虽然这其中有父亲对我的误解,但父亲在做人上的严格却让我刻骨铭心。
父亲教育我们,很少动手,可往往是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就足以让我们明白做错了事。这一点对我影响非常大,让我明白作为父亲在教育孩子上面更多的应该是身教,而母亲更多的是言教。还有一次,一位同事来家里找我谈工作上的事情。
当时我正在完成一个设计图,所以就边低头工作边和同事谈着。这期间父亲曾到我的房间来过,当我们父子双目对视的一瞬间,他的一个眼神让我感到似乎我又做错了什么。后来父亲郑重其事地专门和我谈了此事,他说当你与人家谈话时,不管谈些什么,不管你认为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都要正视对方的眼睛,都要认真聆听对方的讲话,因为那是表示对与你谈话者的尊重,更何况人是一心不能二用的。
父亲的严谨自律的人生态度并不仅仅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事和教育我们身上,同时更多的反映在他对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中。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画与京剧,与武术,与中医等国粹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讲究功夫(技巧),遵循程式。
然而,一个事物的特点,有时往往同时会是这个事物的缺点,甚至是致命的缺点。中国画对于功夫的苛求和对程式的固守,往往会成为束缚艺术灵魂的枷锁。父亲始终很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掌握中国画的技巧上,父亲所下的工夫可以说是非常深的。且不说他日日夜夜追随花鸟画大师王雪涛先生的十余年,以及其间广泛学习的五代宋元直至民国的花鸟画经典之作,就是平时的笔墨研习、书法训练等必修日课更是从不间断,即使是在从事政府的外事接待工作和中学执教期间也是如此。
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举家迁往天津后就一直住在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里。那时候我还很小,父亲在中学教书。半夜从梦中醒来的我总是看到父亲仍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写画画,每每皆是。
然而,对已经掌握的与老师作品相似到乱真的笔下功夫,父亲感到的并不是满足,而相反的是惴惴不安。他深知娴熟的技巧,高超的功夫并非艺术的本身,那其实只是艺术的表现手段而已。
艺术的灵魂在于创造。他经常对人说,学老师,沿着前人的东西深入时非常难。而当你学会了要离开老师,从前人的东西走出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时就更难。是啊,父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广西回到天津以后,一直在苦苦探索和追求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此,他可以废寝忘食,醉心艺境;可以淡泊名利,闭门思画。也正是为此,他可以放弃人家携重金请他画熟悉题材作品的要求,而对所画的一只他认为有新笔新意的小鸡欢欣鼓舞,兴奋不已。
父亲对于中国画的创新也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画必须创新,必须与古人或是过去的艺术有所不同,必须有所处时代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他从不反对任何在艺术创新上进行的尝试。
有一次,我拿了一本介绍实验水墨作品的画集给父亲看,本来以为恪守传统的他会加以排斥。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认真的对我说:实验水墨这种提法很好,艺术离不开创造,创造就需要进行实验。既然是实验,就说明没有成熟,你就要给人家时间,给人家空间,允许人家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对于这种实验,我们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从一位耄耋之年的传统艺术家的嘴里听到这番话,着实令我为之震动。
也许是因为步入暮年,进入高龄后的父亲没有了以往那种严父的威严,给予我们的是更多慈祥的微笑。现在回忆起这些,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体会到真正的父爱是什么,那是一部永远也读不腻,永远也回味不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