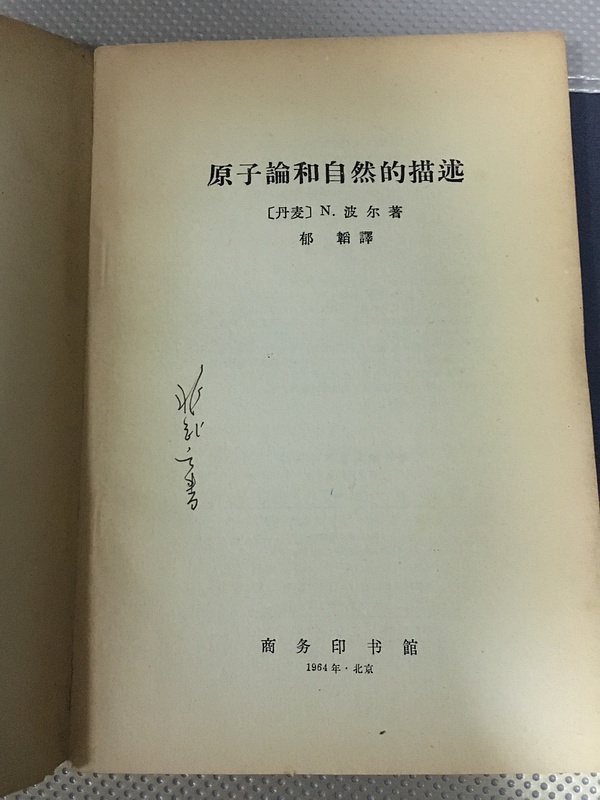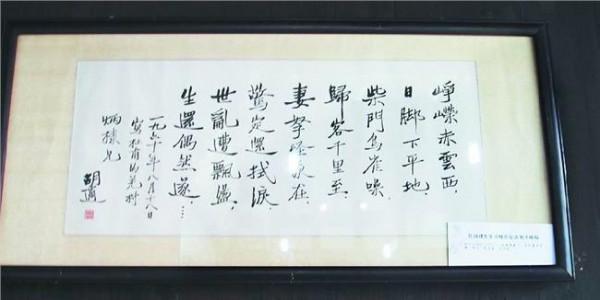雷海宗的墓地 何炳棣: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忆雷海宗师
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他满含深情怀念他的老师、已故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证出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学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学界一般认为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编者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但可喜者有三。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
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
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
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
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
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
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
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
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
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
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长期停滞。
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书及其他发表的论文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
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算,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三十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o.1)创刊之庆。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才放弃了刘歆1122B.
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
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虽在电话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
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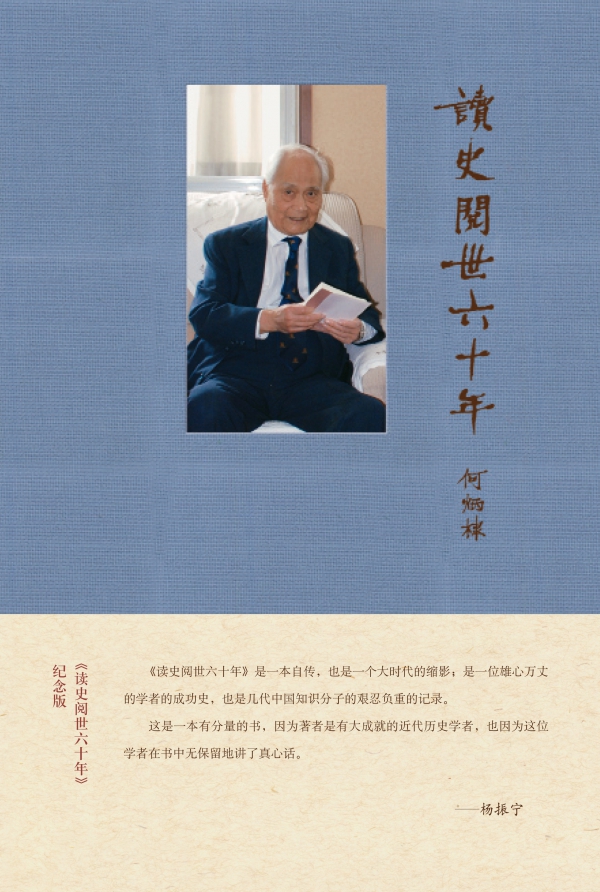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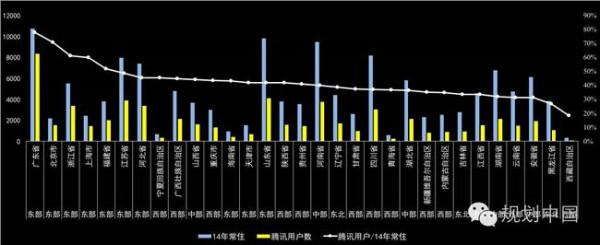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obi] BY:何炳棣](https://pic.bilezu.com/upload/7/44/744074d31531f48edc1e109074d9d200_thumb.jpg)
![>蒋廷黻mobi 读史阅世六十年[mobi] BY:何炳棣](https://pic.bilezu.com/upload/7/71/771e58752510d8da769c61156be8f19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