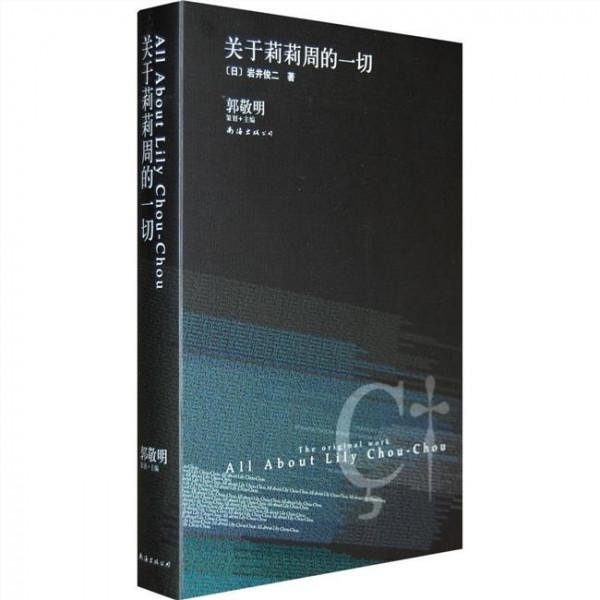张戈美术 著名自闭症青年张戈和她的艺术家妹妹
张戈,1985年生,中国第一例“儿童孤独症“的患者,
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自闭症第一人”。
吴川:1988年生,张戈的妹妹。
几个月前,去南京重访张戈一家。张戈和妈妈站在地铁口迎接我。她的个头比妈妈显得高一些,她穿着深色的格子外套,短发,圆圆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但目光却显得有点失焦。
“阿姨好”她在妈妈的提醒下向我打招呼,伸出手来。我握住她的手,手心是凉的。这是2016年3月底的下午2点钟,街道两旁樱花和桃花烂漫地开着,空气里弥漫着花香。
我们坐在客厅里交谈。张戈听我们谈话,她想插话,想让我看她喜欢的东西。她拿着一只塑料珠子串成的花猫对我说:“小脸猫。”我回答她:“真好看!谁送你的?”她默然不答。——后来我才明白:脸猫是她给妹妹吴川起的昵称。因为她自己是“大脸猫”。
我们家有两个重心,那就是我和张戈
1988年,张戈在南京脑科医院被陶国泰教授诊断为患有儿童孤独症(自闭症)。她是南京最早被诊断的几个孩子之一,当时她才三岁。
在她和父母前面是一片可怕的空白,没有医药没有教育机构没有专业教师可以求助,甚至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孤独症”到底是个什么。痛苦徘徊之后,他们下决心自己来教张戈,同时想办法把她送进特殊教育学校。
就在这时,吴苏星怀孕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给父母带来了新的希望。为了“转运”,父母决定孩子跟母亲姓,给她起名叫吴川。
最起初,父母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是为了让张戈在将来能得到照顾。当时,有个好友责备妈妈这样是对妹妹不公平的。这个责备像阴影一样一直埋藏在妈妈内心深处。她一直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妈妈,没有钱,没有学历,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需要的教育;担心因为照顾大女儿,耽误了小女儿的成长。
长大后的吴川认为:“父母在教育上做得最好的是给我自由。”
等到吴川拿到赴美签证的那一天,吴苏星对女儿说:“我终于不欠你什么了。”女儿不明白,她继续说:“我把你培养成人,让你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从此以后你想做什么,不用担心被姐姐或是我们拖累了。”
后来我问吴川,当时妈妈这样说,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她回答说:其实我不记得妈妈说过这样的话。^_^
因为张戈,他们一家都与自闭症结下不解之缘。张戈父母是南京最老的一批自闭症家长,也是最资深的志愿者之一,20多年来一直参加各种孤独症公益活动。自从海伦博士创办孤独症公益组织“五项目”以后,一家四口都成为 “五项目”志愿者。
吴川为“五项目”做过翻译,现场翻和翻译文件都有。她本科毕业举办作品展,卖画所得一半捐给了五项目。“能帮一点是一点,积少成多。”
作为张戈一家“家人一样的朋友”,海伦博士一直有一个疑虑:在一个对自闭症缺乏意识、容忍和服务的社会里,拥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姐姐是如此的特别,难道吴川就从来没有为此而感到过有压力吗?她为什么没有对要承担的责任而心怀怨恨呢?
吴川的解释很简单:首先,张戈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好姐姐,她对我很温柔。其次爸爸妈妈总是很支持我,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很多机会去发展。其它的家庭只有一个重心,而我们家有两个重心,那就是我和张戈。
(一家四口)
而这位已经和她们一家人交往了24年的朋友——海伦的理解是:“因为吴川和张戈的父母给她们两个都提供了爱、支持和鼓励。虽然中国有些家庭担心一旦有了第二个孩子,患有自闭症的第一个孩子就会受到冷落,但是他们一家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他们并不是想用第二个孩子来代替第一个孩子,而是让第二个孩子作为一名成员来加入他们,完善他们这个家。
长久以来,父母一直都把重心放在两个孩子身上。张戈15岁时从特殊学校毕业,张戈妈妈为了她辞掉了工作。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两个女儿相处,张戈爸爸放弃了升迁和高薪的机会。那么结果如何呢?夫妻两人互相分担责任,两个孩子得到了父母的关爱并且知道她们确实是家里的重心。”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张戈的父母:“你们到底更喜欢哪个女儿?”,他们总是说:“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她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都喜欢,不偏心。但是我们和她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不可以作比较和衡量的。”
2003年,张戈一家获得“感动2004——中国十大真情故事”评选活动的提名。后来他们获评为全国“100个幸福家庭”之一。
她最好的一点是她是我的姐姐
吴川2015年拿到艺术硕士学位,现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城郊。她有两份工作,一个是艺术家助理;另一个是老年公寓活动协调员,负责各种艺术相关活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这种自由的工作安排使她有很多时间搞艺术创作,参加各种展览。
她很喜欢自己的生活。“我一直觉得最理想的生活并不是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而是生活慢慢的,稳步提升的状态。”
每天打开邮箱,她都能收到姐姐张戈的邮件。由于姐姐的表达能力所限,邮件几乎没有任何内容。她很少回复,但每一封都会打开来看。姐姐有时也在微信上和妹妹聊天。说是聊天,也就是打个招呼。
吴川对姐姐最初的记忆是大约三岁到六岁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幼儿园,姐姐上小学,爸爸骑自行车带我们。我坐在爸爸前面,姐姐坐后面。”
因为“我一生下来就有姐姐”,吴川不能接受“没有姐姐你会怎么样”这种假设,她说“我很感激我不是独生子女,因为有了姐姐,我更学会分享。”
“占取父母时间和资源的百分比和孩子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她也不肯说“有这样一个”姐姐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你忽悠我呢!”她调皮地说。
对于比张戈小5岁半的妹妹来说,姐姐一度是令人仰慕和依赖的。小的时候,在妈妈的指导下,姐姐照顾妹妹也管着妹妹。小学时,妹妹的作业一直是姐姐检查,妈妈只负责签字。
妹妹喜欢粘着姐姐玩,但是如果有别的玩伴,她就会把姐姐撇在一边。等小伙伴走了,她又会缠着姐姐。
(有个姐姐让我粘)
当有不开心闹别扭的时候,妹妹便只管哭,妹妹一哭,姐姐也跟着哭,于是别扭也就闹不下去了。其实好多事也怪不得姐姐。比如——姐姐帮妹妹收拾书包,照着课表一丝不苟。但是有时老师临时通知换课,妹妹明明已经放好了书,姐姐却又把书按课表换回来。妹妹上课找不到课本,急得直哭。
姐姐刻板地爱整洁,不管什么东西都要马上收拾。妹妹写大字刚写完墨迹未干,姐姐一下把本子合上,结果字迹全模糊了,只好重写。
妹妹哭泣、告状的结果是,妈妈告诉姐姐:“让妹妹自己收拾书包。”“妹妹的写字本不要收。”张戈收拾桌子时,再看到妹妹摊在桌子上的写字本,就会自我提醒“妹妹的写字本不要收。”
另外一方面,吴川很早就意识到,姐姐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她必须照顾姐姐。“爸爸妈妈总是对我说:‘姐姐需要你的帮助。你是她聪明又能干的妹妹。’”
她喜欢和姐姐一起玩,做她的小帮手。在吴川3岁的时候,由于大人禁止进入公共游泳池的儿童泳池区,她就担任起了引导、照顾8岁姐姐的任务。她帮姐姐在更衣室换衣服、教姐姐游泳。她很享受当一个“聪明的妹妹”,一个小领导、小老师。
这种经历对于她的学校生活很有帮助,她从小就表现得比大多数同龄人成熟、大方,能够帮助同伴、分享成果、协助老师做各种组织工作。从幼儿园到中学,吴川一直都是班干部,初中时,她是各种协会的负责人;高中时,一直是班长和科学课的班级代表。在各种文体活动中崭露头角。
姐姐去上班,妹妹忙于求学,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但是姐姐还是想方设法照顾妹妹。读高中时妹妹晚上补课、自习,回来已经快10点钟了,姐姐总是算好时间到车站去接妹妹,帮妹妹拎包。“有人接你放学回家总是一件很好的事,特别是当外面很黑、时间很晚的时候。”吴川回忆。
妹妹也习惯于保护姐姐。一家人一起出门,如果姐姐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总是引发一些异样的目光。“我就会瞪眼反看着那个人直到那个人觉得不好意思而不再盯着张戈看了。”当姐姐因为一些说不出来的事情难受哭泣时,妹妹也总是去安慰她。
因为姐姐,家里经常有媒体来采访。作为“张戈的妹妹”吴川也经常被记者提问。吴川小时候很喜欢出镜,而且会在记者的提问下说出“我永远和姐姐在一起”的豪言壮语。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她慢慢察觉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个患自闭症的姐姐”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接受媒体采访、反复被问同样的问题也变得令人尴尬和厌烦。终于有一天,当有记者要求采访她时,她哭着拒绝了。
在中学里,她走读,时间被功课和业余活动填得满满的。她有很多亲近的同学、朋友,但他们彼此很少谈论家事。她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都知道她是个开朗活泼,成绩好、有美术专长的女孩,大家都不知道她有一个身份叫做“张戈的妹妹”。
“既然他们无法理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告诉他们了。”
1999年,姐姐从特殊学校毕业了无处可去,2008年他们全家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呼吁为姐姐和其他成年孤独症孩子提供就业机会。这是吴川在国内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节目播出以后,吴川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在屏幕上认出了她,“张戈的妹妹”就这样曝光了。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人因此而歧视冷落她。相反,她的美术老师对她的品质和努力十分赞赏,祝福她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和姐姐在生活上取得的进步都让我对于做她的妹妹、被别人叫做‘张戈妹妹’而感到骄傲。”吴川说。
一个是开朗活泼、成绩优异有艺术天赋的学霸;一个是语言能力有限、智力缺损、兴趣刻板狭窄的孤独症患者,这样天差地隔的姐妹俩在一起如何相处呢?
“找各种方式傻笑,逗她玩,有时候让她读故事给我听,搭乐高玩具,毛绒玩具……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和大脸猫交流方式。很多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我跟她在一起就重复很多她喜欢的,别人觉得没有意义的话。只要她开心就好。”
“我们俩合得来。尽管她不能直接告诉我她的感受,但是我知道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我们就是了解各自的感觉。”她很笃定。
2008年,吴川离家赴美。
到了美国,在聊天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同学都有一个有残障的亲友。兄弟姐妹、叔伯阿姨……大家很坦然地分享和他们相处的故事。吴川讲了姐姐的故事,同学们都很喜欢她,觉得她很可爱。
“有一个孤独症的姐姐”不是一个耻辱和负担,而是被人理解接纳、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契机。
妹妹去了美国。张戈一开始很不习惯,总是到处找妹妹。但是当她习惯了家里没有妹妹以后,妹妹再回来,她又觉得妹妹太吵,把家里弄得乱糟糟。
关于以后要不要照顾姐姐,吴川的回答毫不含糊:“我一定要照顾姐姐啊,因为我是她妹妹,我不来谁来。”“我可以让她活的开心,活的有意义。”
“如果你今后的家人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怎么办?”
“那我就和姐姐浪迹天涯喽。”当年这个女孩27岁,她用满不在乎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















![张驰男歌手 张驰[内地著名流行歌手]](https://pic.bilezu.com/upload/9/0b/90be3976066b92b744e8d60af72d77e1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