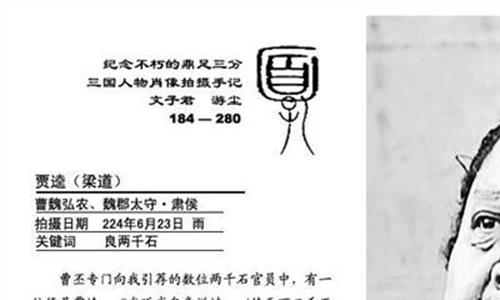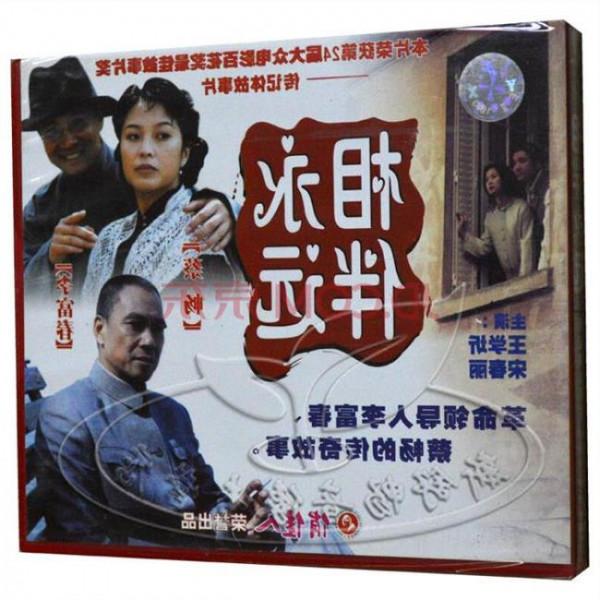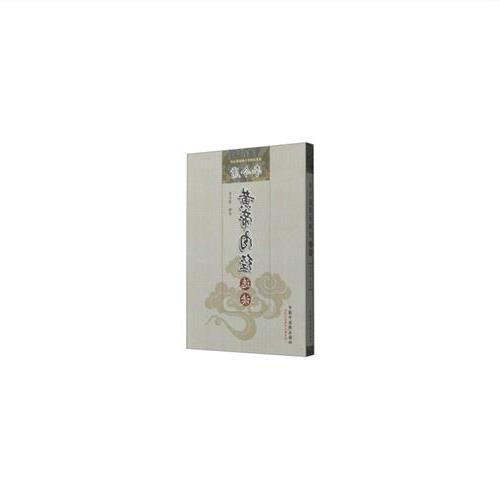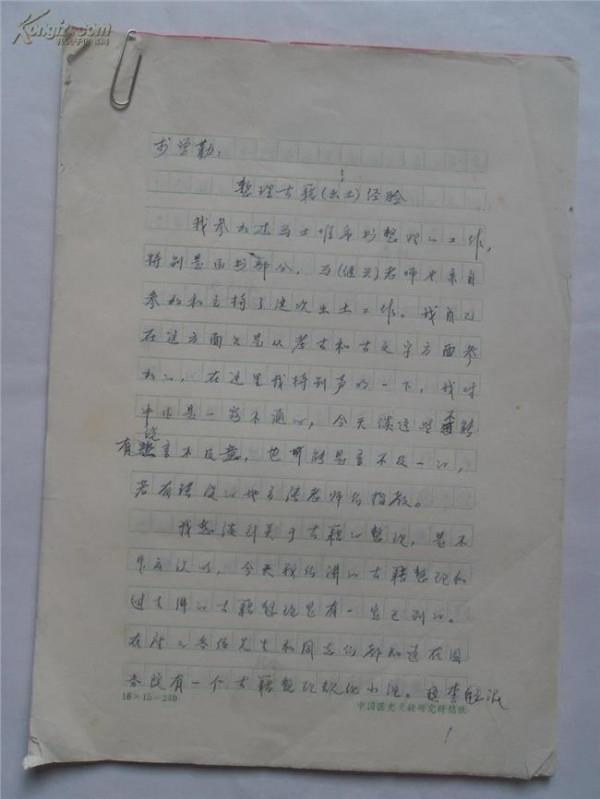字源李学勤 李学勤:中国学术的源起
演讲人简介: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走出疑古时代》(1995)、《古文献丛论》(1996)、《四海寻珍》(1998)、《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等20余部及学术论文约500篇。
关于中国学术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些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很早,不过它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界的重大问题并引起争论,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清代中叶后。为什么在清中叶以后?大家知道,在清中叶以后,逐渐兴起一个叫“今文经
学”的学派,今文经学学派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为尊孔起见,说中国学术的主要来源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孔子以前,是“万古如长夜”,没有学术。所以从推尊孔子出发,今文经学派更多地把孔子以前的学术传统,越来越加以贬低,越来越加以淡化,甚至于否定。
这个发展趋势从今文经学兴起之后越来越强化。强化到最极端的例子,我想在座的老师同学都是很熟悉的,就是四川井研的廖平,即廖季平。廖季平先生跟我们湖南有很大关系,大家知道,他出身于四川的尊经书院,受业于王闿运,王闿运是一位今文经学家,可是王闿运先生没有他这样的观点。
到了廖季平先生,他的经学有六变,越变孔子的地位就越高,越变孔子以前的学问就越少,到了最后,他居然提出中国汉字是孔子造的,孔子以前是没有汉字的,孔子以前的字可能和西方的字一样,是横着写的,到孔子出来之后,孔子造了六书,造了汉字,中国才有了文化。
我想这一点,已经将中国学术的源起问题讲得特别极端了,这个论点和我们历史上传统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孟子就说过孔子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结前人。
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继往而开来,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他也总结了过去。这与廖季平先生讲的,恐怕就完全相反了。如果什么都从孔子开始,那还叫什么“集大成”?也不能叫他“大成至圣先师”了。
古书里说得很清楚,在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我们以前读书的人总要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讲“诸子出于王官”,诸子都是从王官而来。再看其他史书里面,关于孔子以前有很长的学术文化传统这一点没有怀疑。
比如今天我们坐在书院这里,书院是怎么来的呢?我想根本是从孔子杏坛讲学而来,这就是书院的一个模型。后人根据孔子讲学设计一个制度,建立书院。可是书院还有另外一个学习的模型,就是中国自上古以来的学校制度。
书院是和上古的学校制度不同的,它一方面参考了上古的学校制度,同时又考虑到自孔子以及七十二贤以来的讲学制度,由此形成了书院。我在岳麓书院说这种话是班门弄斧了,这里是中国书院史研究的中心了。可是中国的学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在古书上是说得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礼记》中的《文王世子》,它讲在唐虞的时候就有了学校,叫“成均”,现在韩国还有“成均馆大学”,为什么叫“成均”呢,也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说法。
近代以来大家都说古书未必可信,是后人的说法,不一定可靠。我想最好的发现就是我们终于在甲骨文里发现了“太学”,“太学”在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里就有了。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不要看只有两个字,它很确切地证明了至少在商代的晚期已经有了太学。我们中国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看来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太学,并由此再追溯到商代。
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是一件方鼎,叫“荣仲方鼎”。这件方鼎上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学校的情况。最近我才知道荣仲方鼎不是一件,还有一件,铭文是一样的,不过第二件花纹比较清楚。鼎的时代是西周成康时期的,我把铭文写一下:
王作荣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荣仲錫庸(?)一、牲大牢。已巳,荣仲速内(芮)伯、(胡)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彝。史。
先看“王作荣仲序”,“序”就是学校,这个字大家有点疑问,有人说念“宫”,其实甲骨文中的“宫”从来没有这么写,这是个“序”字。要是它念成“宫”,整个铭文都读不懂了,念成“序”就懂了。而且我们有证明,过去著录有执尊、执,也提到“序”,赏赐的两种东西中,大家肯定猜不到,是笔。
一般的赏赐有赏笔的吗?因为是学校,所以就赏笔。这个“笔”字不是我释读的,其他先生早已释读过了。“王作荣仲序”,“荣仲”是学校的主持人。
在十月又二月,就是十二月。因为是王作序,所以这个“子”一定是王子,“加”即“嘉”,就是奖,奖给荣仲什么东西,我猜想“庸”就是一件铜钟,还有太牢。下面已巳那天,荣仲又请(“速”就是“请”,“不速之客”就是不请之客)芮国、胡国两位侯伯的孩子入学。芮国见于《尚书·顾命》。
从这个例子,大家就看到当时确实有学校,这里讲的制度,都是和礼书的记载相接近的。我们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在商代、西周初年的时候,有相当好的学校制度,这种学校培养“国子”,北京现在还有“国子监”。这种学校的教学内容为《诗》、《书》、礼、乐,必然包括学术的成分,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说孔子是“集大成”,那么孔子以前的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比如说孔子以前有没有著作遗留下来,我们当然说有,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诗》,有很多篇都是在孔子以前的,还有《尚书》,同样很多都是孔子以前的。我知道最近有好几位博士生是写《逸周书》的,《逸周书》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不是全部,但肯定有相当大的部分,比我们想象的多,里面有些东西很明显是西周的,比如说《世俘》、《商誓》等等,可以举出六七篇,有些是西周直接流传下来的,有些经过了改编,但包含有西周的内容,这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逸周书》主体的一大部分,也应该是如此,有一些篇在先秦的文献里都引了,如果你不否定这些先秦文献的话,你就得承认。比如说《左传》襄公十一年,晋悼公的臣子魏绛所引《书》“居安思危”,引的就是《逸周书》的《程典》篇。
还有《战国策》的《楚策》,虞卿和春申君的谈话。春申君黄歇,大家都知道,那是战国末年的人,虞卿这个人在史料里记载他是传《左传》的,他的著作有《虞氏春秋》。
虞卿引《春秋》一段话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就是《左传》襄公十一年里魏绛所引。过去康有为等连《左传》都不相信,今天没有人不相信《左传》,因为今天许多发掘材料都证明《左传》是正确的。例如淅川出土青铜器记楚令尹王子午,字子庚,这只在《左传》才有,除了《左传》,去哪里查王子午字子庚呢,所以它是可信的。
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的余地。我们很少有人很好地研究《左传》、《国语》里面春秋时代的学术。春秋时代对于《诗》、《书》、礼、乐的解释是怎么样的,其实在《左传》、《国语》里有很多。我们通常所讲的《周易》,《文言》的头几句就来自《左传》。这些到底讲的是什么,春秋时代人的学术世界是怎样的,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研究。
在座的各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话题,这里面涉及我们对于古代文献论证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我最近读到张京华博士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题目叫《顾颉刚难题》,他提出一个如何研究古代文献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文中引到顾颉刚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的一段话,顾先生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这里指的是谁呢,张京华博士说是指王国维,王国维《古史新证》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下面顾先生说:“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
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分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这就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逸周书》一样,有几句你可以证明它们是春秋时候就有的,那么你能证明其余也是春秋时候就有的吗?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一想就明白,我们对于任何史料,包括近现代的史料,要求证明它的所有内容为真,这是做不到的,根本就做不到。
包括近现代史的所有史料,都不能要求将所有各点证明为真。
那么我们怎么说一个史料是可信的呢,我们得看里面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能够证明里面有些点是特别好的,确实是真的,这就可以增加其他各点的可信性。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没有任何记录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史书也不能说什么都是真的。
特别是古代,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的。古人编一个年谱,好多地方都能证明它不对,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整体,问题是它的可信性有多大,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
应当从量的方面看这个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来讲这个问题。不知我说这话对不对,如果错了,各位可以群起而攻之。
我们再回到学术史,刚才谈到了商、西周,关于孔子以前的西周那段古远的时代,要求我们拿出太多史料来,这是做不到的,哪有那么多材料啊?如果有够多的材料的话,就用不着来讨论了。从能够得到的信息,我们看到孔子学术传统的久远与深厚。
过些年我们岳麓书院也将成为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中心了,我相信岳麓书院这一方面的发展会非常迅速,很快会成为全国与世界简帛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些年里,我们发现的出土的战国秦汉的材料有一点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战国时代的人承认有六经,这一点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学术史,就会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了,比如说汉代只有五经,因此就认为先秦的时候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虽然六经之说见于《庄子·天运篇》等。汉代人为什么说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呢?因为《乐经》已亡,所以只剩下五经了。
更有人说古时从来没有经。我们现在证明,当时确实有六经,而且《乐经》也应该有文字。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两处都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次序和《庄子》完全一样,时代也和《庄子》一样,郭店简在公元前300年再加一点,当然《庄子·天运篇》不是庄子本人写的,可能是他的弟子写的,可是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已认为有六经了。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样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
这也是中国学术源起的重要一点。《诗》、《书》、《礼》、《乐》、《易》、《春秋》从来就属于主要的教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清代的学者,他们主张:《诗》、《书》、《礼》、《乐》是没问题的,《易》、《春秋》很晚才进入经的范围。
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是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因为孔子晚年好《易》,孔子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
这种说法现在非常普遍。《易》、《春秋》当时是不是具有和《诗》、《书》、《礼》、《乐》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还可以讨论,至少它们已经逐渐地走向那个方向,那个趋势在春秋时代已是如此。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我们把这个问题接着讨论一下。《春秋》比较容易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在很早的时候就作为教材了。我必须说明,《春秋》是个大名,不是儒史的专名。这个例子很多。问题出在哪呢?因为过去的人最喜欢、最经常读的是《四书》。
《四书》里《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给人一个印象,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这当然是对的,是这么回事。
可是这不等于说《春秋》只有鲁国叫《春秋》,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在《注疏》里面已经讲清楚了,当时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个名。
至于为什么那个叫《乘》,为什么这个叫《梼杌》?到今天也没人能讲懂,讲不明白。《春秋》乃是大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墨子》,《墨子》里面就讲清楚了,不但有鲁国《春秋》,而且还有周的《春秋》、燕国的《春秋》、宋国的《春秋》、齐国的《春秋》。
你不能说鲁国的才叫《春秋》。《春秋》就是大共名。我们看《国语》,在《晋语》与《楚语》里面都有晋国人和楚国人讲到历史教育。在《晋语》里面有一个晋国的司马侯就说:“教之《春秋》,以感动其心”。
他教的《春秋》当然不是鲁国的《春秋》,特别不是孔子写的,那时孔子还没有出现。楚国的申叔时也是这样,大家知道楚庄王为太子找老师,老师去问申叔时,申叔时也说“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耸善抑恶”是史的作用,就好像孔子说史有褒贬一样。不管是晋国的教育还是楚国的教育都要用《春秋》,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左传》昭公的时候晋国的韩起,就是韩宣子,在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就说:“周礼尽在鲁矣”。《易象》不会就是《易》的经文。有人说《易象》就是《周易》,那这话就等于说晋国就没有《周易》,如果晋国有《周易》,那他又何必惊叹?在《左传》、《国语》里面晋国用《周易》占卜的事好多,他怎么会没有《周易》呢?这一说法本身就不对。
所以《易象》这本书,一定是一本讲易象的,类似《易传》的书,它是讲《易》的象,而不是《周易》经文本身。
这就看到了当时在鲁国已经有一种易学。这种易学的存在在《左传》中很多,后来就吸收到孔门的《易传》中间。这些都是早于孔子之前的易学。“《鲁春秋》”,这说得很对,鲁史不是周、燕、宋、齐的《春秋》,而是鲁《春秋》。韩起一看到这个,就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明白周王朝成功的道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不是没有学术,而是有很多的学术,而且学术是在六经。《诗》、《书》、《礼》、《乐》为主,《易》、《春秋》后来也成为重要的学术,这是当时的学术传统与教育。孔子对六经都有所述作,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是“集大成”者。
我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要否定孔子的作用。“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因为孔子修《春秋》,里面有所褒贬,带有他的道德、政治、伦理的原则,跟原来不同。这样的“微言大义”,是不是都像《公羊》、《谷梁》讲的那样,我们还可以讨论,可是无论如何它是有的,这点是不会错的,所以,孔子对于这方面,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孔子本人是不是作《易传》,我们不知道,但《易传》一定作于孔门,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里面包括了很多孔子关于《易》的讨论。
如果有些人不信这些,那么现在我们在上博的竹简里面发现了《诗论》,看下孔子怎么讲诗。孔子讲诗确乎有“微言大义”,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出里面的一些观点,跟后来从《毛传》看到的有些很不相同,有些地方还很开明,很特别。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孔子确实是讲了,因为《诗论》的内容,唯一的可能是弟子的笔记,肯定是孔子当时讲的,不是后人编造的,想编也编不了。它就是一个笔记,孔子讲《诗》的笔记。从《诗论》里还可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大家知道《诗论》整理的时候,有一个想法:《诗论》是不是可以证明有很多的佚诗?结果证明当时孔子用的《诗经》跟现在本子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当然文字是不一样,这个不奇怪。
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你能说他不是经学家吗?如果说当时没有经学,是成问题的,所以说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经以外各家就是“子”啦,包括儒家也在内。这样就看到中国学术确实是源远流长。
我们还应该特别谈谈《周易》。近些年我们有些发现,证明《周易》不是晚出的。这方面我们做过很多的讨论。《周易》这本书的时代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有一本小书叫《周易溯源》,试图在不涉及其思想内容的情况下,从文献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周易》这本书,包括它的《经》、《传》部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结论平淡无奇,就是证明它是很早的,《易传》也比较早。《周易》经文我个人意见就是像《系辞》说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那么,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呢?
我过去曾经提出一个材料:北宋的时候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中方鼎铭末有筮数,将它转化为易卦之后,正好说明铭文的内容,但这毕竟是个推论。前些时候,在陕西西安长安县西仁村出土了两个陶拍子,上面刻的卦数我觉得足以证明《周易》的年代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陶拍子?在座有考古专家,都知道古代陶器是盘制,拿泥条盘起来,搁在陶钧上转,转的时候,得搓它、弄它。陶器表面上有时候要做成纹饰,就找一个东西来拍它,拍出纹饰来,这个工具就是陶拍子。陶拍子其实也是陶的,就像一个蘑菇形的东西。
长安西仁村这一带是西周陶窑遗址,关于陶拍子的简报发表在《文物》2002年第11期上,有两件,都是采集来的,是西周中期的东西。一件上有四个筮数,四个卦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师》卦,一个是《比》卦,一个是《小畜》卦,一个是《履》卦。
这就是四个卦,一个陶拍子有四个卦。另一个陶拍子有两个筮数,一个是《既济》卦,一个是《未济》卦。大家要知道这六个卦分成两组,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师》、《比》、《小畜》、《履》是《周易》上经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是《周易》下经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卦。
每两个卦是互倒的,把它们刻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这和《周易》经文的卦序一样。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当时可能有精通易道的贤人,遭了难,给抓起来烧窑,他就刻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无论如何,从卦序等方面看,这证明当时不但是有经文,而且还有易学。
这些例子使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在孔子以前,不光是《诗》、《书》、《礼》、《乐》,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集其大成,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开创私人讲学,所以说他是“集大成”者。
最后,我想用几分钟把我最近写的小文,也是我的想法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印在曲阜师大编印的《孔子文化研究》上。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有人据此说孔子是不谈“性与天道”的,像孔子的高徒子贡都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可见孔子整天谈的都是政治、道德之类,不言“性与天道”。
我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不但谈“性与天道”,而且谈得很多。马王堆帛书里面的《易传》、《二三子问》等都是讲“性与天道”的,新发现的《诗论》中谈“性”、“命”的也不少。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特别引用了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的说法。
金景芳先生已经过世了,他整整活了九十九周岁,论虚岁,就是百岁的学者。他说这段话不是说孔子不讲“性与天道”,而是说“性与天道”是一个很难了解的问题,即便是子贡都以“不可得而闻也”兴叹。
这就对了,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性与天道”是很难了解的,子贡叹息孔子讲的有些他听不懂,他是客气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马王堆帛书里看到了子贡跟孔子之间关于《易》的谈话,他们谈的就是“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的意思,按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说听不见。古代的语言里面“听”和“闻”,“视”和“见”不一样,意思不同,层次也不同。我们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是说没有眼睛,或者是瞎了,或者眼花了,而是看了而没有辨别它。
“听而不闻”,从耳朵来说可以听见,但从心里头理解才能叫作“闻”,所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的谦辞,说孔子关于“性与天道”之论深奥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实际是讲“性与天道”的,把孔子说成不言“性与天道”,这种解释是对孔子的根本贬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篇就是专门讲“性与天道”的,如果说这些不是儒门的,跟孔子没有关系,那就完全错了。
今天我讲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孔子正是孟子所讲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前头是长得很,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有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性的新发展,是承前而启后。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