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南京 张旭东北京大学 张旭东: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在美国看北大人事改革
近来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的争论。这既在意外,也在意中。
本来,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聘任、评估和升迁淘汰制度是该校自主权限内的事情,应由该校全体师生讨论决定,无需其他人在一旁议论指点。但北大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象征意义却使这所校园里发生的变化成为所有思考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前途和命运的人都要来关心的事情。
这是北大的麻烦,也是北大的福分,拔高了说,是北大的命运。反过来讲,北大人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人们对北大的关切并不一定是对此一家情有独钟,而是在北大身上寄托了对中国大学之本质的思考和对中国文化之前途的理想。北大作为一所具体的大学能否担当起这样的思考和理想,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同属于命运的范畴。
无论关心北大的人对这所学校有多高的期待,在现实中,它的发展却由种种环境和时代的因素所决定和制约。众所周知,北大这次的改革方案以争当“一流大学”作为目标,但对“一流”的理解或“前理解”却可能建立在一些更抽象、更隐秘、但往往更普通、更流行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上。“市场化”和“全球化”无疑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
以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内长期形成的心理优势,谈“创一流”当然不是指要跟国内兄弟院校一争短长,虽然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北大这家百年老店已经日益感到来自国内其他大学的竞争压力(这当然是件好事)。北大谈的“世界一流”,参照系自然主要来自外部,含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国际上多拿金牌,以不负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味道。
然而和体育竞赛不同的是,世界上有公认的“一流大学”,但就什么是一流大学,却没有公认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且不说近代西方大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传统和取向之间的竞争和互补关系,就说当前美国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
versity),虽在世界上占尽优势,但就近看,各学校之间千差万别,各有所长,也各有各的问题。若做一般的归纳,则只能得出些一般性结论,如杰出的教授;拔尖的学生;巨额的资金;精良的基础设施;极高的声誉,等等不说人也知道的东西。
其实,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内,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必然是对民族和国家命运有所担当、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有所承诺的精神殿堂,而不只是一般知识和技能的超级工厂和传授所。按这个标准,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出一所大学,在其本国的地位可与北大在中国的地位相提并论。
哈佛、牛津、柏林、巴黎、东京、莫斯科固然都在各民族的历史上享有一份光荣,但没有哪一家像北大这样同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如此深切地交织在一起、对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负有如此自觉的使命、承受着如此殷切的民族期待、又在师生中间激发出如此之高的自我期许。
北大的校史本身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精神神话。哈佛再“牛”,却绝不敢夸口能把全美国最好的学生一网打尽,而北大即使在颓势中对此也“当仁不让”。仅就这一点就可以想见,北大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实为所有美国常春藤名校加在一起也达不到。
这一切所谓的“虚名”并不解决现实中的北大的问题,反倒给北大上上下下造成一种压力。并非因为学校真觉得不改革就对不起那些“万里挑一”的学生,而是“形势比人强”。日益商业化的社会把一切都标上了价码,北大从前用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的力量”和计划经济体制度提供的种种保障和特权,如今已被新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所取代。
北大如今能给学生的东西和北大自身存在的意义一道,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新的物质环境里面被重新审视。
同时,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化进程把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强行纳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中。在这个新的分工和等级体系里,北大正面临一种难堪的身份转变: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正在渐渐变成一所名牌“留美预备学校”。
但如果北大已在理论上承认,学术无国界,所有大学都必须服从一个绝对的、超越民族国家时空的国际标准,那么当北大把一批批立志进中国最好的大学的孩子们招收进来,随即发现他们已经站在北大的肩膀上把目标瞄准了“世界一流”的欧美大学研究生院,又怎能责备他们呢?除了立志自己成为国际一流大学,北大又能如何?
本文无意质疑北大改革的动机和必要性,也承认北大在许多具体方面同西方一流大学存在相当的、一时难以弥合的差距。我想说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北大这次的改革既然以外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参照系为前提,以全面系统地改变一所学校的面貌为目的,就应该公开地、明确地对这所学校根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作出新的说明。
一个按照“一流”标准运作的北大,可以是一所肯定自己传统中的正面因素,并能够把它们更好地发挥出来的大学。
但如果北大把“一流”抽象地定位在同国际接轨,同美国研究型大学全面竞争的标准上,结论恐怕只能非常令人丧气:北大在中国是天之骄子,在国际上,若按某些单纯的量化标准,很可能连二流也排不上,“赶超”的时日即便不是遥遥无期,也旷日持久,恐怕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亲眼看到。这或许就是网上有人所说的“自取其辱”的意思吧。
仅就办学经费这一项看,北大曾在过去三年里得到国家18亿人民币的财政支持,令国内其他大学艳羡不已。但在西方研究型大学中随手抽样,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资金投入规模对于办西方标准的“一流”大学,只是杯水车薪。我目前任教的私立纽约大学(NYU)年度预算超过15亿美元,折合120亿人民币。
我以前曾任教过的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在美国50所研究型大学里面位居中游,但年度预算亦达十多亿美元。
NYU去年募捐活动受美国经济不景气影响打了折扣,依然在3-4亿美元之间。两年前宝丽来(Polaroid)公司老板去世,一笔就捐给学校1亿美元,被专用来在文理学院设立讲座教授席位。美国研究型大学本来就热衷于以高薪在全世界范围内网罗人材,有了这样的横财,挖起人来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纽约大学拥有大量房地产,是位居天主教教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的第三号地主。即便如此,校长和校董会仍然念念不忘NYU在美国大学的富人俱乐部里只是小弟弟。
《纽约时报》曾报道哈佛大学的基金规模超过古巴国民生产总值。当我和一位在哈佛工作的朋友提到此事时,她竟然吃惊地说:“只相当于古巴的国民生产总值吗?我还以为是荷兰呢。
”哈佛富可敌国,但若问普林斯顿的人,他们会不屑地说,大学财力不能看总额,要看人均。据报道,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基金按在校学生人数平摊,超过50万美元,远在哈佛之上,但却还比不过一些只办本科教育的私立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在办现代研究型大学这件事上,钱固然不是万能,但没钱却万万不能,这大概算是“硬道理”。但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体系,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并不是靠硬性指标和硬通货起家,而是植根在中国本土的特殊土壤之中,随着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血脉成长起来。
自晚清以降的各个时代,在中国大学里面汇集和生长的,并不是统统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交换或估价的商品或“成果”,而是一个民族凝聚在“知识”和“学术”里面的历史、经验和思考,是几代人为之献身的理想和意志的结晶。这也是大学改革根本不同于企业改革的原因所在。在此,“效率”、“合理化”、“
竞争”这样的现代企业管理概念相对于大学的根本使命,哪个是手段,哪个是目的,应该不言自明。事实上,除了行政、财务、后勤和科研服务等方面应实行科学管理外,大学的核心领域,即研究和教学本身,在根本上是排斥“效率”、“竞争”、“合理化”这类思维的。以笔者在美国大学读书和任教的亲身经历,可以说美国大学是最没有“效率”的地方。
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大学可资北大和其他中国大学效仿,但若技术层面的学习、移植、赶超变成体制性的“同国际标准接轨”,就会动摇中国大学作为中国文化和社会自主性的守护者和象征的自我定位,进而伤及中国大学的底气和命脉。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治大学又何尝不如此,忌讳的是翻来覆去,一会儿这个样板,一会儿那个模式。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立校之本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理念,而是同中国大学一样,来自大学自主性和国家命运之间的深刻的联系。
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自我理解和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却可以因某种想当然的政策而一蹶不振。人们可以轻易地可以计算出一个在学术市场成为商品的名牌学者的身价,但却无法计算一个学者成为学者的社会成本和学术本身的价值,更无法对学术生产的内部规律进行“管理”。
脱离大学根本的自我定位谈“竞争”和“效率”,或许在企业管理的意义上有所收益,但却会把学者整体推入一场由市场化意识形态为主导、技术官僚为裁判的老鼠赛跑,这样生产出来的“学术”,客气地讲是中规中矩的学院八股,不客气地讲就是一堆连回收价值都没有的垃圾。
仅就财力这一个方面而言,北大或国内任何其他大学的一流目标,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所谓“国际水准”上。若是非要赶全球化的快车,按种种武断的硬性标准同美国大学体制“接轨”,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就等于将自己有形和无形的总体资源统统按一比八(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率)缩水,在想象中的国际市场上,以贱价拍卖的方式“入世”。
以这样的逻辑,中国人文学科“接轨”的最佳捷径大概就是同海外“汉学”或“中国研究”领域“横向协作”。但如果北大文、史、哲等传统大系的“学术国际化”只限于同西方大学的东亚系交往,甚至把西方中国研究的范式和行规视为当代学术的圭臬,那
么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进军就只能抵达西方学术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内容就永远只能在“国际学术”体制中作为一种局部的、为外在的意志所支配的地方性知识存在。在此少数国内学者或可以感受一下“置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但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离学术本身的距离,就不可以道理计了。
若再舍近求远,把近年一些国内读英文,出国读中文,在东亚系拿了学位、却同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隔了又隔的海外留学生当作“国际人材”请回来淘汰自产的“土鳖”,以正国内“专业学术训练”的视听,中国学术的买办化、殖民化指日可待矣。
这样的“一流”心态若在国内演成风气,势必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一轮俄国式的“休克疗法”。如此脱离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的“转轨”给迫于流弊、急于通过改革走出困境的中国大学造成的结果,恐怕只能用“他生未卜此生休”来形容。
邯郸学步式的创一流,到头来不仅与“一流”无缘,连二流也做不到,往往只落得一不中不西、亦土亦洋、上不去下不来的“不入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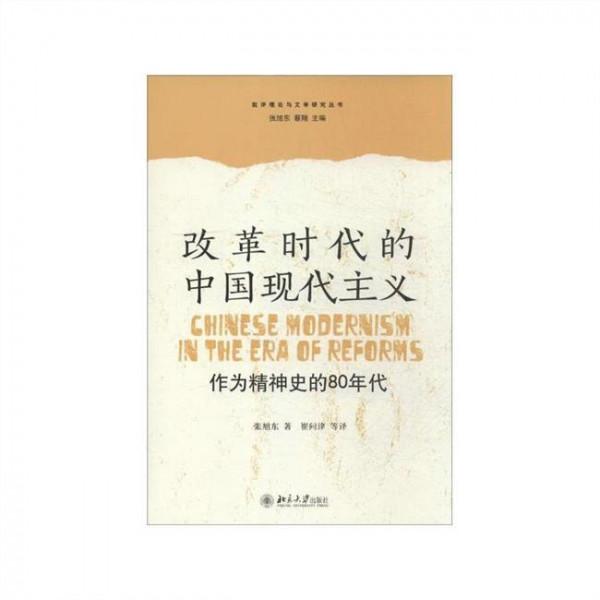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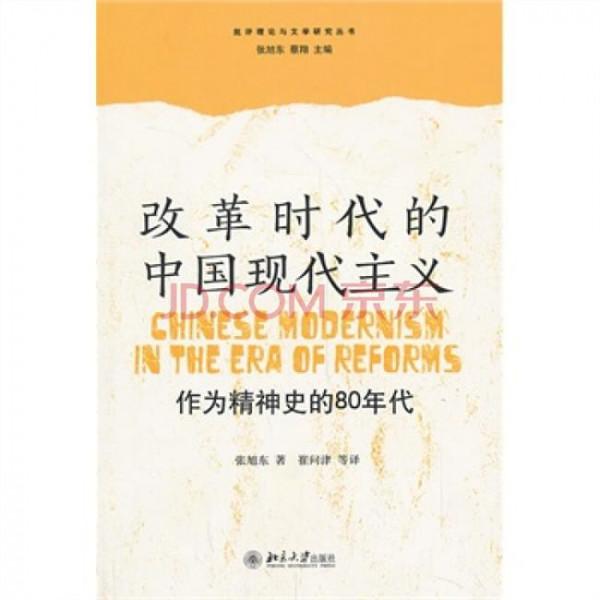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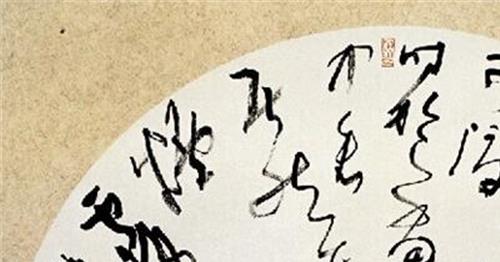






![>张旭东新华社 张旭东[新华社记者]](https://pic.bilezu.com/upload/0/03/0031438ba1be3f9b94eb14eefe6e60f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