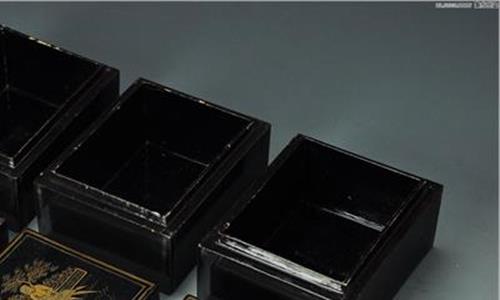塞林格九故事 九故事的钥匙在哪里——关于塞林格的《九故事》作
写到这里,天色已晚了,空气的温度迅速地转凉,从窗户旁边的穿衣镜里能看到外面两幢高楼的空隙间天边沉重寂静的暗云正在变成一个整体,只余下几小朵淡紫的云浮在上面,还多少染上一点微红的晚晖。电视里在放着罗斯特洛波维契独自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在一个古老的空荡荡大教堂里,他已经老了,有时解说,用语言与钢琴,示范巴赫作曲时的特点音符组合方式,“……因此在演奏中就必须加入自己的潜意识,因为有些声音在现实中是听不到的,你必须以潜意识想象。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沉浸在大提琴的演奏里。在我看来,塞林格就是这样的一个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的演奏者。无论是残酷还是悲哀,或者是绝望与感伤,都被他在一种淡定而自然的状态下充分地加以演绎,他演奏的不是可以听得见的声音,而那些现实中听不到的声音,他在想象中捕捉到它们,轻缓地动它们,抚摸它们肌肤与纹理,给它们以新的生命状态。
他是不动情的,就像不动声色一样,他只是希望以它们本来的样子完成一种想象世界的构建,他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过程和效果,他无所不在,而又置身事外。
他并不提供一种约定的线索,以供你顺其摸到作品的核心,因为那样的线索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圆环中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点。
当你感觉到某种东西的时候,任何一个点都可能是入口。 在这九篇小说里,居于中间的,是那篇相对平和许多的《下到小船里》,它甚至带有其它篇小说所没有的一丝亮色,因为它暗示了某种和解,成人与孩子在内心深处在情感深处的那种瞬间感应与理解。
跟塞林格笔下的所有孩子差不多一样,四岁的男孩莱昂内尔也是个敏感、孤僻、而又自闭的孩子。两个庸俗的女人对他父亲的随意谈论与恶意评价,轻而易举地就伤了他的心,就像面对以往任何伤害一样,他选择了逃避与躲藏,这一次他躲到了小船里。
而他的母亲波波,那个不漂亮却能默默地善解人意的女人,以其特有的方式,一点点靠近他,不厌其烦的小心破解了他设置的一切障碍物,进入到他的世界里,使他与自己和解,并且顺利地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带到温暖的感觉里,最后他们是一起跑回家的,莱昂内尔获得了胜利。
那么在此之前的其它时间里,她作为一个母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在她身边的他,又何以变成这个样子的呢?这种疑问,不能不让人对这种短暂的和解状态产生更多的疑虑,今后她与他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谁都不能预料。
这种疑问,不能不让人对这种短暂的和解状态产生更多的疑虑,今后她与他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谁都不能预料。
另外一个带有某种和解色彩或者说理解调子的故事是《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骄傲的女学生吉尼向来看不起周围的同学,无疑她的判断其实来自于其性格以及那种还比较简单而又模糊的印象性思维。
尽管开篇就描写她的有点小气的特征,与一起打球的同学塞利纳计较车钱之类的事情,但其实作者要写的却是她的宽容与理解力。在吉尼来到塞利纳的家中,无意中碰到了塞利纳的退伍不久的哥哥以及哥哥的朋友,他们的那种参战后的反常状态,深深地触动了她,她不但没有对他们产生厌恶的感觉,反而开始在聆听的过程中生发出了同情怜悯之心。
她是那种容易就理解了他们的处境与糟糕的心态。以至于最后她主动与塞利纳和解了,甚至连那块让人不舒服的三明治都没忍扔掉。
她知道内心的伤害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多么容易发生的事。她怎么会有这样的心胸与感知能力呢?无法知道,但你能知道的是她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弥足珍贵的。 塞林格笔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被严酷生活现实轻易打垮的,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别的什么现实遭遇。
他们都陷在一种心理困境里不能自拔,找不到任何出路与希望。孩子们是很难理解成人世界的。尽管他们可以想象猜测,但不会找到答案的。而青年人的遭遇与状态,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相对比较切近些的现实。
与令他们感到不安与拒斥的成人世界相比,青年人的世界则让他们感到了那种莫名的有些模糊的心痛与恐慌。在《笑面人》里,通过那个近乎童话的“笑面人”的故事,塞林格把一个内向得有些自闭的青年在现实感情经历中的挫败感折射得淋离尽致,与笑面人的悲惨遭遇相比更为可悲的是,笑面人除了那个侏儒欧姆巴跟动物们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那个叫玛丽-赫德森的总是穿着海狸皮大衣的姑娘,是小说里除了酋长之外最为神秘的一个人物。
她的神秘与笑面人、酋长的神秘是不同的,她的神秘是身份与生活的神秘,显然通过反复强调的穿着以及抽的香烟就可以知道她家境富有,甚至可能还是个已婚女子,可能还有个婴儿等等,其它的呢,就无从知晓了。
杀死“笑面人”的,其实并非是什么无情无义的那对父女,而是现实。同样,让酋长与玛丽相遇又分开的,也是现实本身。这个现实是什么?是容不下“笑面人”的世界,也就是容不下童话也容不下异想天开以及一点点单纯浪漫的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并不是死,而是死之前的无尽煎熬。
当然这些不可能是一个九岁的男孩所能想到和懂得的了,但足以让他回到家里之后继续在床上发抖。那个罂粟花瓣面罩,则似乎暗示着弱不禁风的天真想象。
天真总是死于现实之手。尽管还有爱。 与绝望相伴的,常常就是爱了,最强烈的爱的背面,就是最大的绝望。没有爱,就没有绝望,反之也是如此。只要死亡还没有真正来临,那么绝望与爱就会始终相伴在一起。
当然,它们也可能会在死亡来临之前在一起彼此消解化为虚无,什么都不留下,除了一片灰烬。就像光盘播放完之后,电视屏幕是蓝色的,镶嵌在电视机那狭窄的黑框子里。在《九故事》里塞林格所描写的最微妙而又纯净的爱,也就是那篇《为埃米斯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了。
说它微妙与纯净,是因为它就像一首没能完成的乐曲,不,不只是没能完成,而是仅有几个音符的曲子,可能连个最基本的和弦能否够得上都难说,或许只是一个音符,按下去,不再延续其它的音符,余下的只有不绝如缕的泛音。
战争让人离开了家,漂泊异乡,也给人带来意外的偶然相遇,一个年轻的军人跟一个出身高贵的早熟少女相遇该是件多么奇妙而浪漫的故事啊,但关键并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相遇,是一个孤单的人,发现了另一个孤单的人。
孤单的人常常是习惯于自我封闭的,只有另一个真正孤单的人才有可能轻易地触动并打开他的心扉。埃米斯这个早熟的十三岁女孩,之所以能让“我”终生难忘,只是因为她发现了他是孤独的,发现了他有一张敏感的脸庞,其实也就是发现了他的敏感的心。
她的难以让他忘怀,还在于她除了同样敏感孤独之外,还有着坚定、高雅的气质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寻。而这一切恰恰是“我”所没有的。
战争是能够使现实世界充分显露其污秽与凄苦的面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些微的甚至有些模糊的单纯的爱意,才显得如此的珍稀难得。战后的“我”显然是已是心如死灰了,如果他心中尚有余烬未熄的话,那么就一定包括对埃斯米的怀念,在他的与他人充满隔阂的生活状态下。
在描写污秽与凄苦经历的后半部分,给身心俱伤的他带来些许慰藉的,就是埃斯米的那封信。或许就是因为这封模仿成人的口气写出来的一本正经的信,给了他一些生活下去的力量与温暖。
那块在邮寄的过程中弄碎的特别的手表,并不是什么幸运符,而是一个女孩子最微妙而深沉的爱,对父亲的,对他的,都是怀念,它的表面破碎了,显然,它所承载的那种时光也就随之停止了,他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时间里了,就像他再也不能恢复为健康的人一样。
这篇小说或许并不是《九故事》里艺术成就最高的,但毫无疑问是最为感人至深的,它的情绪与感情是如此的压抑,又是如此的绵延不绝。埃米斯的弟弟查尔斯的那个关于墙角见的谜语,真是关于孤独与孤独相遇并发现的最好的见证。在这个充满污秽与凄苦的现实世界里,它就像一抹略微有些怪异但又非常天真可爱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