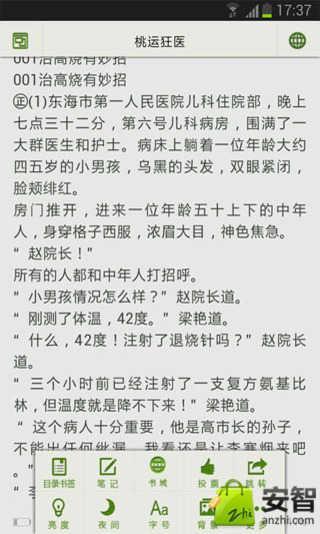张惠雯欢乐 张惠雯:关于幸福 《欢乐》创作谈
在致路易·科姆南的一封信中,福楼拜写道:“您体验过烦闷吗?不是一般的、平常的烦闷——此种烦闷来自游手好闲或疾病,而是那种现代的、腐蚀人心的烦闷——此种烦闷能把一个聪明人变成走动的影子、能思想的幽灵……有时我们自认已经治愈这个毛病,但某一天一觉醒来却感到比任何时候都痛苦……”我有时在想,许多现代小说,谈论的多多少少都是这种“现代的、腐蚀人心的烦闷”吧,无论其内容是空虚、孤独、冷漠、情感的匮乏或是别的什么。
如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喜欢读教人如何体会“幸福”的鸡汤文章。那么多媒体在调查这样的问题:你是否幸福?什么使你感到幸福?一方面,幸福似乎是个深不可测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幸福似乎又简单得成为一种“模式”。
譬如,你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他们怎么会散了呢?他们很幸福啊!收入又高,房子车子什么都不缺,孩子听话、学习又好……人们归纳总结出一个成年人“幸福”模式:不缺钱,有孩子,孩子学习好……人们认为这种“幸福”是人生最重要的成就,认为打破这种幸福模式是残酷的。
但其实,这其中没有一条涉及幸福,这只是合乎社会要求的富裕、完满。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个生活于“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谈,如果你能窥见哪怕一丁点他的内心世界,你几乎都会发现那种无法治愈的、现代的烦闷,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
我们把幸福的“条件”都扔到一边去,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稀缺。那种发自内心的、充盈着灵魂的欢乐也几乎同样稀缺。大概正因如此,这个时代寻欢作乐、逃避孤独的方式比以往都多。
从感恩节开始,经历圣诞节的高潮,直到新年过后,这段时间里节日那么多,聚会一个接着一个,就像小说《欢乐》里竖琴家伊莉莎所说的那样,连“空气里都布满欢乐”。在儿子出生前,我会喜欢参加一些聚会。并非我是个喜欢交际的人,事实上无论参加多少聚会,我始终羞于和不熟悉的人交谈,始终会在交际场所感到尴尬,到最后总会厌烦着匆匆告辞。
但再也没有比这种节日派对更好地了解一个地方风俗的方式了,也没有更好的观察那么多人、汲取小说养料的机会。
有时候,你会突然看到前一分钟还在大声开玩笑的人独自站在某处,一脸的落寞。或者,你在某次聚会上和她说了很多话的某个人,在另一次聚会上又和你成了陌生人。聚会就像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生的缩影,人们尽力说啊欢笑啊结交新友啊,但实情却是在制造一次短暂的麻醉和失忆。
这样的聚会上,偶尔会有些昙花一现般的人物,他们突然地、出于某种巧合(有时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要对你一吐衷肠。因为现代人似乎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宁愿把秘密说给一个陌生人听,也不告诉身边那些人。有位华人男士,据说非常富有,他告诉我,他母亲来美国看望他,他很高兴,但这也给他们家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他的外籍妻子和女儿都不爱吃他母亲做的饭,于是,妻子带着女儿天天去馆子或回岳母家吃饭,两三个月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人吃晚饭。
他说这些话时,带着无奈的诙谐,但我感觉到事情也许并非吃饭那么简单,在这背后,是一种非常深的“隔膜”,一种冷淡的、缺乏情爱的夫妻关系。另一次聚会上,有人给我讲了一个中国“凤凰男”的故事,这男人通过奋斗在美国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还娶了一位台湾女子为妻,但他无暇照料他仍在中国山区的父母。
他和这女子在生活、消费习惯上诸多不一致,但也努力维持着和睦。直到他父亲死后不久,他和妻子去科罗拉多滑雪,因行李箱丢失,他妻子在滑雪场商店又购买了许多东西,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同去的朋友听到他们在酒店房间里争吵……后来,我脑海里差不多有了这么一个影子,他身上有我听来的这两个小故事。
我想,如果一个男人在丧父后很快就能携妻女去滑雪度假,那另一个男人为什么不会在丧母后还去参加节日聚会呢?这未必是无情,可能只是软弱。就像小说里的“他”一样,当你无力于从悲伤中理清什么东西,那倒不如把自己托付给幻象般的欢乐。
2015年的圣诞节前,我参加了一个只有女士参与的派对,那对我来说是一次印象很深的聚会,非常安静、感性,可口而简单的意大利食物,还有竖琴和小提琴的独奏和协奏。参加聚会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中产阶级妇女,其中有一半是欧洲移民。我发现她们中有一位在听演奏时眼泛泪光。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单纯的音乐之美,还是被触及了什么回忆,她是否有什么痛苦?后来,我把这个演奏场景用在了小说《欢乐》里。
在外人眼里,那两位男士和我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都是生活体面、家庭幸福人士,但他们自己是否幸福,这是一个问题。而看似幸福的人是否得到了心灵自由,那又是另一个也是更大的问题。生活在某种显而易见的幸福模式里的人们,或许既无幸福也不自由。
在我的小说主人公那圆满的、镜面一样光滑的生活表象下,是冰冷的、死气沉沉的关系和无法得到安慰的孤独。至于他想要的幸福,不过是如王家卫所说的“有一个温暖的伴侣”,所以,在聚会上,他的目光往往投向别人的伴侣、别人的家庭,因为他疑惑着那些人是否真的有他自己没有的幸福。
人们会通过努力改变许多事情,譬如形象、财富、地位,而不幸福或不自由,这倒像是他们最无力改变的。面对真实的不幸,人们往往选择逃避、无所作为,那种软弱、虚脱甚至能给人一种快感。
孤岛般的、深层的自我,那种几乎不可改变的烦闷和消磨,如影随形的死亡与欢乐场景交织的虚幻感,以及沉溺于生活失败的虚脱,使我的男主人公在一个欢乐的聚会上变成了“走动的影子、能思想的幽灵”。
有时,当人们在谈论这个或那个幸福的人时,我会忍不住套用卡佛的题目在心中嘲讽一问:当你们在谈论幸福时,你们在谈论什么?这也许是小说家的刻薄吧,但我觉得我们那双用于观察他人的眼睛最好同时有着同情和怀疑,就像我们的心肠最好既尖锐又悲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