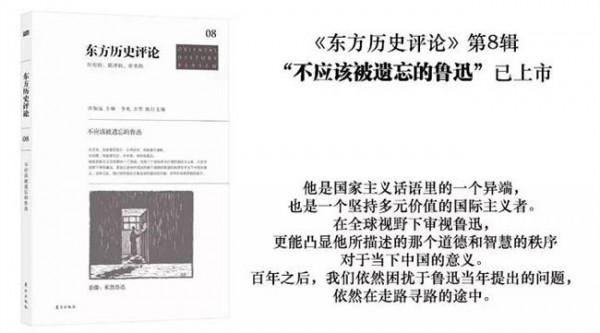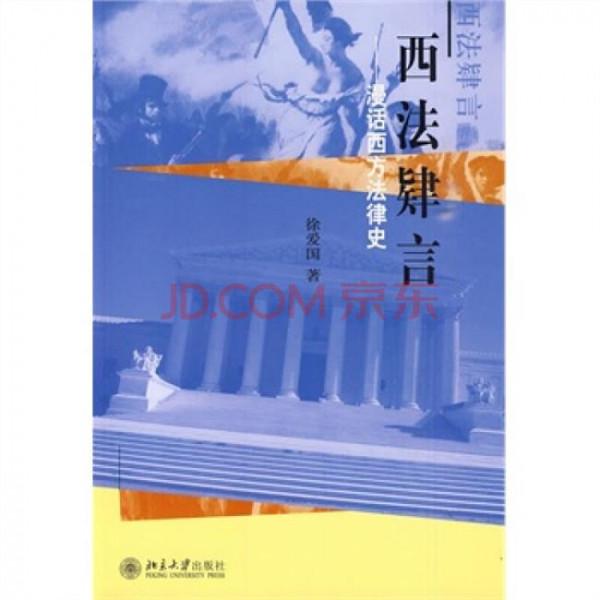许章润梁漱溟 许章润 :论梁漱溟对西方法律的理解
在近代中国接引西方法意与法制的智识活动中,以现代「新儒家」名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思虑迄未得到应有的疏理。而就其在体贴中国固有人生与人心的意义上对于西方法律与法理及其在中国的移用的观照而言,正有为专门的法律从业人员虑所不及而需要我们后人用心体会者,梁漱溟乃其中突显之一例。
这里,笔者通过分析梁氏对于西方法律精神与传统及其社会─历史成因,西方法律价值与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及其与「老中国」的冲突等课题的论述,揭示梁氏思想中的另一侧面,同时,借此视角,展现现代新儒家在法的领域接续、阐发中国固有传统时,接引异域文明的心路历程。
一 梁氏对于西方法的省察,基本上是在「公法与私法」、「历史与现实」以及「价值与功能」的三组范畴中作业的,分别触及了西方法的意义源泉──法之为法的合法性;历史维度──法是民族精神与地域生活的展现;和现实根据──法是服务人生而熨贴人心的生活样法。
第一,就公私二元、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而言,梁氏体认西洋的法律一如其政治,乃「德谟克拉西的法律」,也是「科学的法律」。
而一言以蔽之,西洋社会─政治的组织与运作盖在于「权利为本,法律解决」这八个字。「权利为本」,意味着个体与团体、国家与社会各有其权利,而各以其权利为核心,所以此疆彼界,「权力」与「权利」,必须明确规划,「订定明白」,而这便也就是法;意味着经由「表决」等众多工具理性的复杂技术性操作而筛选、凝结民意,民意中的多数──压倒一切的优势人心──即为法律。
用梁氏的原话来说:「西洋的所谓法律,就是团体里面大家的一个公意;而团体公意如何见呢?就得由票上见。」又正因为此后纠纷,循此解决,法律当然成为不二准绳,所以更反过来要求「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
滥觞于罗马法精神而表见为现代型的公权与私权概念的出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等等,便都是大树新枝、顺水之舟了。这其中所蕴涵的政教分离,道德与法律两清,个体与群体的相反相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而一以实现社会心理所期待的那个「公道」(justice)为鹄的的原理原则,乃是近世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
相形之下,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伦理则「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遂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非权利观念而立;同时,传统中国这一「不像国家的国家」,无阶级的流转圆通的「四民社会」,「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通常时光,「国与民更仿佛两相忘」,遂造成传统中国法律虽早发达,但却不走西方型的私法─权利意识的路子,亦无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的分别。
就此而言,与普世观念下的中国「天下秩序」的组织与维持既不靠教会的宗教,亦不靠国家的「刚硬之法律」的样本相比,辜汤生讥嘲西方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吓唬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峻刻之语道出的实乃「片面的深刻」,也是常情,而梁漱溟对辜氏此说不止一次地征引,亦正是所谓有感而发,心同理同。
职是之故,梁漱溟才慨言:「离开宗教而有道德,在中古西洋殆难想象;离开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国家弥觉希罕。
然而在旧日中国却正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恰与所见于西洋者相反。」而这一切,又都是各自历史积累所得,有在法律之先的社会发展事实预为铺垫,慢慢生成演来的。
第二,从历史维度而言,西方精神本身乃一纷纭歧出、粲然大观的综合体,不仅有晚近「最新思潮」与启蒙运动后的「新思潮」的对立,而且更存在着彼一思潮与此一思潮的扞格。
如梁氏所述,欧洲自近代初期起,发挥个人主义、权利思想,成就了现代的西方社会,这是对于中世社会的反动的结果;而最新的思潮则是随着经济上的社会本位,法律思潮亦随之主张「社会本位」与「义务本位」观念,所以,个人对于国家,当初只希望它不干涉者,此时转而希望它积极负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1919年的德国宪法等,于人民的消极权利外,复规定一些诸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积极性权利;同时,如何运用自己的财产、受教育、工作以及选举投票等等,亦均成为人民的义务,所谓权利与义务的一元化。
梁漱溟并引狄骥(Léon Duguit)的「社会连带关系」(solidaritésociale)理论为己说作证。
在他看来,此次西方前后思潮的调和,根本精神不仅是基于国家与个人的对立,更是出于调整个人与个人的对立这种格局的需要,而这种「两面各自主张其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的机制,在他们不仅是补偏救弊的时势使然,更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技巧,但从中国儒者的理想的眼光看来,此不免「固执一偏,皆有所失」。
实际上,梁漱溟在此道出了一个法律规则需切合人心,而确能服务人生,从而与多数人的社会价值若合符契,成为人们乃可信托的外在准则和内在凭借,从而实现法律规则与法律信仰内外一致的问题。
第三,这种表现为法律架构的近代民主政治,在梁氏看来,其价值与功能在于「合理」与「巧妙」两项。所谓「合理」,就在于它使得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即公民权,而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干涉过问,其直接结果便是对于个人自由权的确认,而凡此诸端一以宪法制度笼统,并落实为具体的司法保障,特别是司法独立与程序公正的设置,而此政治与社会安排达于人心,法意与人意融通,一以法律(特别是宪法)为「最高」,即为宪政与法治。
因此,这里的「合理」不仅是指「合理性」,亦意味着「合价值」;所谓「巧妙」,则在于「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
前者表现为立法、司法与行政的三权分立,其中,就司法而言,形诸陪审制、律师制度、公开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及其任免制度诸项。就后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宪政制度下的民主运作,「政权从甲转移到乙,平平安安若无事」,美国总统也好,英国首相也罢,经由选举制度疏通「漂亮角上台」的安全机制。
出于对权力本身固有的自我腐蚀性的怵惕,梁漱溟深感如何救济国家权力滋生的危害与腐败,实是现代政制与法制的第一大事,而传统帝制则为恶容易──如他所说,为恶的机会都预备好了 ──为善不易,既无法救济,沉疴不治,便只有暴力革命一途,一乱一治,牺牲太大,而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妙处,就在免除这样可怕的牺牲,而救济了上说的弊害」,这一切托赖于现代政党政治的配合运用,催生政象常新,「其结构之巧,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
正是有鉴于此,如梁漱溟夫子自道,终其一生,对于以英国宪政为代表的西方近世自由主义宪政传统,一代儒者的他「始终倾服」。
二 若借用梁氏本人的用语,则他所解读的造成西方近代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的深切根源,原不外「人生与人心」两项。就「人生」来说,相对于帝制中国,近代西方「社会构造」的「新异的色彩」可用「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一言以蔽之,全部的机运全在如何调理集团与个人的关系上。
要之,西方社会自来为一团体/集团生活的样法,自宗教开端,以至于经济、政治,处处皆然,而集中表见为宗教的团体性、阶级的团体性和国家的团体性三种。
但是,另一方面,集团生活的西洋人反倒孕育出了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所谓「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的「个人主义」。而正因为从希腊城邦起始,西人即重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故必然留意乎权力(团体)与权利(个人)的关系,此种「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这驱使日后「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
与家庭生活相比,集团生活的维持以秩序为前提,「为维持秩序,就得用法律,不能讲人情」。
也正因此,于个人与团体双方,首要的是只求事实确定,关系厘清,理想生活与生活理想均自在其中。罗马法恰恰适应这一需要,特别是适应「我」觉醒之后「向前要求现世幸福」的「我」的人生要求,而以发达的私法形式推波助澜,营造「我」的「现世幸福」,一种「团体生活」中的「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又正属归「团体生活」中一个独立的份子。
因此,所谓民主制度,在梁漱溟看来,正是根植于西人这种「我」的生活与团体生活的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
凡此种种,共力形成并表达了西洋的别样的「人心」。 西洋的「人心」,曰「争」,曰「有对」,曰「我」之中心,曰「恶」的人性论,曰「理智」的工具理性。梁漱溟举叙英国宪政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无一不昭示一个「向外用力」的「争」字。
参政权乃「争讨而得」,个人自由是「反抗而得」,「若不是欧洲人力量往外用,遇着障碍就打倒的精神,这『民治』二字,直无法出现于人间。
他不但要如此精神乃得开辟,尤其要这个精神才得维持运用」。近世西方的宪政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个人权利与公民权概念的流布,将一切人际格局悉处理为具有平均值的「陌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往来的法律取向,其形成、维持与运作,就靠千千万万并非特别秉有「热心好义」的心肠,而是「各自爱护其自由,关心其切身利害」,「各人都向前要求他个人的权利,而不甘退让」的「孤立」个体的积极参与,设若没有这种「争」的人生态度,「则许多法律条文,俱空无效用」。
这里,梁漱溟认为「论敌」胡适以「不知足」概西人精神的一段话,与其「争」的论说恰可「互资参对」。正是这「不知足」的一个「争」字,使得包括法制在内的所有西洋制度,「一切植基于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契约观念」这一人类「有对性」之上,其情形正可借西人原话,以「钳制与均衡原则」(Principle of checks and balances)一言以蔽之。
这种处处防制的制度设置,以「斗争」为「法的永恒天职」的法律传统,从宗教哲学人性论看,实渊源于西方文化对于人性「恶」的基本预设,政治、法制悉以人性恶为根据,围绕着一个「恶」字做工夫。
一方面,梁漱溟认为,「恶」的人性论自有其深刻的理由,因为,其一,「人本是自家做不得十分主张的」,在立法上,西人并非有意以不肖之心待人,人实不可信赖故也,「与其委靠于人,不如从立法上造成一可靠之形势故也」;其二,除非绝对不要法律制度,要法制就是不凭信人。
法制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欲在凭信人之外,别求把柄,则此亦似不能独为西洋制度病,各社会各国族均欲托庇于此,只不过近世西人将此「把柄」运用到家罢了;其三,在他体会,西洋立法,似乎秉持一种「科学态度」,而科学讲的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平均数的,而不以少数的、特殊的为限。
既然法律本来就是为众人而设,其不信任人,只是说看人只能从平均数来看,我固然不能说你是坏人,亦不能说你是好人,所以当然只能以性恶立基了。
另一方面,这种基于「恶」的人性论,与鼓励「人类应时时将自家精神振作起来,提高起来」,而以「诚」、「信」、「敬」、「礼」相对待的中国固有精神,其「无对」的人生态度,实在大相刺谬。所以,当西洋式的制度性设置已然经由「革命」或「改良」而安置于中国社会,却「胶柱不灵」,甚或「适滋捣乱」,盖在中国根本就无此种人生与人心以为配合,这种制度在中国乃成为「没心没肺」的玩偶。
民国以后的中国徒袭有西洋制度的外形,而人生态度犹乎夙昔,扰攘不宁的表面原因似乎是人人群起而争,梁漱溟却慨言「这正为大家都太不爱争权夺利的缘故」,可谓道尽个中消息。
凡此种种,一句话,正所谓「民族精神」不同,欲在中国引植西方法理与法制,强拧中国人的人心以适应此一人生,冲突乃不可免了。
三 职是之故,欲将具有上述精神品格的西方法于仓促间移植中国,其可能与现实的结果会如何呢?梁漱溟曾先后举过四个例子予以说明,涉及法律与道德、个体与团体、社会与国家、公平与正义、价值取向与制度的功能运作等等诸对构建现代法制所必须处理的课题,关乎生活样法、人生态度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等诸方面。
若同样从「人生」与「人心」两端下手展开论述,则就人生来说,最说明问题的莫过于第四个例子中的地方自治及其选举。
该例典型地展示了固有的中国下层社会构造不敷新的上层结构的需要,以致欲经由「法制」联接上下的努力落空,下层饱受摧残,上层结构不立,而上下交相为害的尴尬。地方社会的自治,梁漱溟认为原意应在构造「团体组织」,使地方社会由散漫而入于组织,而在尊重地方利益与愿望,承认地方的自治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本身」成为一个「团体组织」,从而营造「地方团体生活」。
国家政权以强力来推行,无非求社会加速长进,但地方却不能因此而忘却地方团体本身,只着意于「上面的政令」与「官府的委托」,也不能将地方自治等同于「古代的所谓乡,党,州,里」或现代的「乡属于区,区属于县」这类「自上而下的『编制』」,否则,只有「他」而无「自」,哪来地方「自」治。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此种地方自治,一则需待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至一定阶段,而具备此实际需要与可能的「自然形势」,而不能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形如何,强迫为之;二则须诉诸中国固有的「人心」,而使外在的种种获得「情理」层面的价值源泉。
从前者来说,自来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样法不取「团体生活」的路子,特别是经济上不存在「不可解的连带关系」,从而不能产生「连带意识」,也就缺乏现代西洋意义上的那种「团体生活」的「政治习惯」,即「纪律习惯」与「组织能力」(梁漱溟有时将此表述为「物质经济」与「心理习惯」,或「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活动力」两端)。
物质经济条件的欠缺,表明中国的地方无「自」的存在,纵有所谓「县」「乡」之类的规划,却并不意味着社会本身的发育,从而不存在一个与政治权能相对的西方式的民间社会,毋宁是以「朝廷」直接面对亿万小自耕农、而以「官民」两极一言以蔽之的巨大的「天下格局」,以西方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立为预设的那套制度安插不上;心理习惯的阙如,即遵循团体生活的游戏规则及其习惯与能力的欠缺,说明短时间内「(自)治亦无从治起」。
在此情形下,以「秩序骚乱」、「产业雕残」、「地方疲惫」的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论,当局「只是颁布自治法规,督促实现,这好比对着干枯就萎的草木,要他开花一样」,岂独增加农民负担,实际上反倒助成土豪劣绅的权威,事与愿违地摧残原本就雕零的「地方」──乡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结果是乡民社会不待自治,已先自乱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氏所说的「地方自治」或「地方团体自治」,与当时流行的和当局策定的,毫无共同之处。
它实际上是指相对于政治国家的民间社会的发育(即其在论述宪政时所谓的下面诸「势」的形成),整个国族为应对新的生存环境所作的生活样法与人生态度的重大调整,而以组成现代的民族国家为指归。因而,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实际乃中华民族「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这一长程跋涉中的一个纽结,正如梁漱溟所说的:「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法律在其间与道德联手,扮演一个上下左右串联、衔接、润滑的角色。
所以梁漱溟才说:地方自治,「实是天下大事」。处甲午以降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中,梁漱溟比别人更为清醒地懂得,今后的中国必定是「团体生活」的样态──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蹒跚迈上了此一不归路了,而团体生活及其习惯也好,组织团体生活的能力也罢,「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人并不缺乏「组织」的能力,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在固有的中国人生与人心的基础上组织和达成这一生活,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包括法律移植在内的一切制度性重构所面临的真正困难之所在。
在此,梁漱溟提出的三点主张,实际是通过调和中西法律精神以连结社会的上下结构,形成新的治道与治式,从而调整中国人的身心,重组整个国族生活的框架性设想。其主要意旨包括: 第一,新的政制、法制的形成,必以新习惯、新能力(纪律习惯、组织能力)的养成为条件;而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
具体来说,欲在中国社会形成团体生活样法,则须以接续中国过去情义礼俗精神为条件,必从固有情义之精神以推演,不能以简单「移植西洋权利法律之治具于此邦」为已足。
有感于当时言地方自治者和中央政府之自治法令,「相率抄袭西洋之余唾,从权利出发使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均成为法律之关系;比之乡间,乡长之于乡众,或乡众之于乡长,均成为法律之关系」,「径行法律解决」,梁漱溟坦言,其于「西洋行之甚便,中国仿之,只受其毒害而已」,盖在其伤「情」害「义」,而「情义」二字乃中国乡民社会过去赖以组织的根本,也是将来的新习惯、新能力得以养成的起点和精神。
于此,梁漱溟提出,对于诸如「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样的舶来的西洋法律与法意,「吾人只可如其分际处师取其意,而不能毫无斟酌的径行其办法」,否则,简单灌输「四权」将使中国乡村「打架捣乱」,地方自治未成,倒先「自乱」了。
今日回头一看,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广大地区的基本结构还是以小自耕农为一极,而以「官府」为另一极的「官民」两分样态,阶级无由形成,也就是说不存在利益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从而无推出其利益代言人的迫切需求与实际可能,也没有为此而敷设的诸多技术性措置以为配合。
地方自治与选举,乃将中国组织成一国家的措置,社会与国家两分的尝试,代议制度的一环节一方面,在当时的中国虽又不得不做,实际上却确乎无从下手。
而将宪政等等大架子便搭设在这样一个直接以亿万小自耕农为基础的社会,能不危殆万分。这里,梁先生列举的案例,均道出了中国固有的「情义礼俗」与新的制度运作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国固有人生态度中「争」与「让」的游戏规则与新的制度设置的冲突。
案例一所陈述的,正是不敢、不愿甚或不屑「争」的固有人生态度在西化式的诉讼制度中的灭顶之灾。
本来,这一态度所导致的各自秉持礼俗,向内用力、反躬自省而各自诉诸自家情义这根心弦的这番内外交互印证的工夫,于攘让从违皆有心照不宣的绳矩,但新诉讼制度要两造拋却情义与情面,各自在「争」中赤裸裸主张权利,这一套游戏规则之伤情害义,于鸡犬之声相闻的乡民社会生活样法,恰不是解决问题,而适足以增加问题。
即在世纪末的今日中国都市,特别是商界,虽已多少倾向于经由诉讼解决纠纷,但也还是更多地以讨一个公正与「息事宁人」为诉讼预期,便是证明。
倘若诉讼结果较预料的成本还高,则其回避此径当然不可避免。所谓成本,自然包括彼此为「非」陌生人的两造间「情义」的损伤在内。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说所谓「法制精神」与「情义」乃水火不容,取此必须舍彼,则为了建成「法制」──中国人心中一百年来压倒性的优势价值──而舍却「情义」,则此成本总和于中国人生与人心是否太高而得不偿失,似犹有讨论余地。
我们固可以设想,在人生与人心中将法制与情义的各自领地划分清楚,情义的归情义,法律的归法律,但问题在于,一个没有情义层面支持的法律竟会是有效的法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尚未之见,则这种设想,其逻辑的说服力不敌其历史的逻辑性,正为梁漱溟所嘲讽的坐在办公室「写条文」类事。
而且,法律从业者所应时刻铭记的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法律、道德等等均为人类精神的自然流露,并服务于人类自身。如果采行某种法律制度就因为它是所谓「先进的」而全然罔顾其是否、能否造福于自家生活,这就恰与法律、道德的最高精神相悖。
所以,如果新制实行的结果是抽去了中国人人心中「情义」这个命根子,则无异于毁灭了中国人的人生,则采行这样的制度岂不是引火烧身?时至今日,1996年颁行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采行抗辩制,而执行效果不佳,新问题说出的还是这个老问题。
所以,以今证昔,梁漱溟的远虑实为近忧,而如何调和包括诉讼制度在内的西式法制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将是攸关今后中国将欲建成一种甚么样的法制及其成败的最根本因素。
第二,政治与经济应「天然」合一。这里,梁漱溟特别强调「天然」二字。在他看来,经济「进步」,则人无法闭门生活,在经济上必然发生连带关系,由连带关系而产生连带意识,则地方自治的基础即树立。
而此种连带关系的形成,梁漱溟认为不当经由「争」的路,而应循沿「合作」、「团结」的途径,以解决最为迫切、重大的生存问题。就当时的广大中国乡村社会而言,治安与生计这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逼着中国人非走「团结」的路不可。
特别是生计问题,必将逼迫着「没有三分钟的热度,没有三个人的团体」的中国人合作、自救、养成团体生活习惯与合作组织能力。梁漱溟悟然于「团体生活之培养,不从生计问题不亲切踏实」,乃有「乡村建设」的设想。
生计问题的核心是经济,从解决经济问题而引导中国人在生活各方面发生「欲分不得」的天然的连带关系,从而有「自治」,进而有「民治」,而且,国家越是民治的,地方越是自治的。
这样,便由经济问题引到政治问题,法律在此应是以「情义」为本的这种连带关系的表述。梁漱溟于此特别提出,这样一种政经一体的社会重组,先要造成事实,造成「形势所归,不得不尔」的事实,而此「事实确非骤然可以作到」,毋宁更为一远程的目标。
但既要有经济上的连带关系,又要保留「情义」,其间是否矛盾以及矛盾如何解决,梁漱溟却并无提示。这里实际上暴露了所有具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理路和价值取向的新儒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所要建成的那种现代工商社会经济运作的复杂性及其压倒一切的主宰性之缺乏心理与学术准备,而使得他们对于价值层面的解说,往往不免单薄。
第三,政教「天然要合一」。此处梁漱溟所说的「教」,如其所述,从严格意义说,特指「关乎人生思想行为之指点教训」,也可以说,「差不多就是道德问题」。
在此语境中,法律与道德也应当天然要合一。从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入手的国家与社会的重建,「非标明道德与法律合一不可」,其根源则在中国历来「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而为一」。
因此,案例二所述的法律冲突,其意义就不止于法律,毋宁更在于人生态度。在梁漱溟看来,西洋人看人生是欲望的人生,而人生天然有许多欲望,满足这许多欲望,人生之义就算尽了。
所谓尊重个人自由,就是尊重个人欲望。国家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个人欲望,另一方面并积极地为大家谋福利,帮助个人满足欲望。故西洋政治可谓「欲望政治」。但中国人自古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谋生存、满欲望更高、更深、更强的要求,即「义理」之要求,所以,欲引发中国人以真精神担当中国社会的重建,非以人生向上之义打动不可。
梁漱溟并举对于乡村不良份子的处置、革除缠足、消禁毒品等弊风陋俗为例,说明在当时的中国西方式法律的效能的有限性,说明较诸「完全靠法律统治,一刻都离不开」的西洋近代社会,「法律与道德分开,若用之于中国,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完全不行的」。
尽管如此,对于案例二,梁漱溟虽曾几度提起,意在说明中西法律背后的价值取向的差异与冲突,但对此案竟应如何处理,却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意见,这固然一方面如其夫子自道,于此外行,不愿多谈;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他很显然于新旧两种法律规定都不满意,而欲有一新的解决,这是他一生基于「于以往西洋法制中国礼俗之外,为人类文化的创新」而别觅途径这一深心大愿的必然诉求,也是绵延至今的中国人生与人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