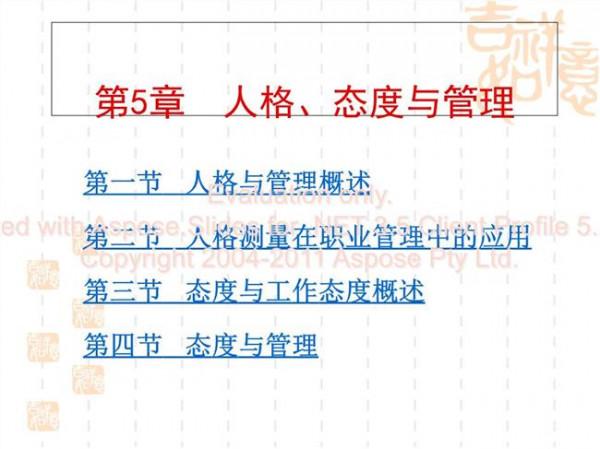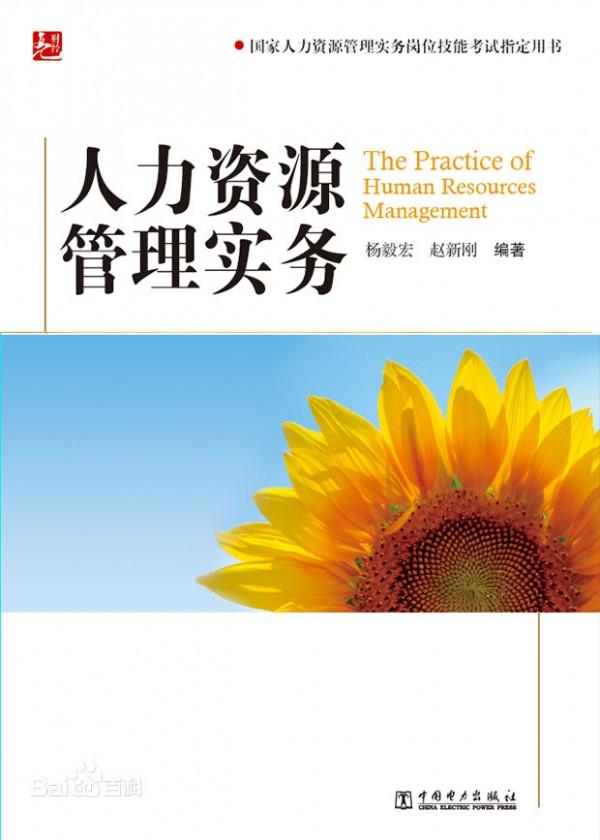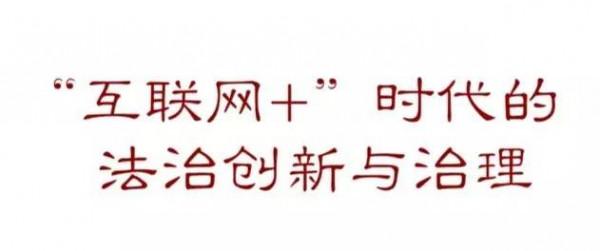许章润民主与法治 许章润:绩效、法治与政治认同
特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民生问题是无底洞,永远也解决不完。一个政府大包大揽要解决全部民生问题,这很危险。
政治文化五花八门
问:上次讲了向历史主流意志、向中国传统文化、向普遍人性的三个低头致意。(见2014年7月3日《南方周末》31版:《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循此三大路径前行,可否说包括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入宪,也是一个明证?
许章润:是的,“人权入宪”和“私产入宪”,都是在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也是在向中国文明和中国近代历史主流政治意志低头致意。说到底,“自由”概念若无具体行动权能表征,则太过抽象。财产是保障个人基本物质性生存的条件,也是个体自由的基础。174年的大势在此,相信没人真想逆着来。
说到革命和转型,概以欧美为样本,但若论现代秩序,不若近取华人文化圈说事,更具说明力。新加坡社群结构以华人为主,将西方市场经济和强人政治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相调配,有机结合,就一段时期来看,其效能与示范意义,不能低估。除了台湾、香港,包括韩国、越南,都属大中华文明圈。某种意义上,香港是一种程序合法性,新加坡是一种绩效合法性,台湾是一种政治合法性。
问:民主治理在台湾落地,前段时间的“马王之争”算制度问题还是其他?
许章润:在下以为,所谓“马王之争”,不惟党争,不惟私人恩怨,也不惟德位,而事关“政治文化”。马王之争,蓝绿之争,南北的分歧,说到底是民主落地之后的利益和理念之争,是在政治共同体框架内,为着分权及其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游戏,和平运作,依据法制和政制进行,而一统于政治,也应当有利于建设政治。此为民主政制下的常态。
话说回头,这种体制下的权力、权利和利益之争,有法可依,终归和平落幕,不用担心政权不稳,所涉只是政府的效能和德行,及政客们的操守和智商。其间拉锯进退,即便没有具体条文,也可通过法律解释解决,而于默会中各守底线。这便牵扯到“政治文化”,顶顶重要。综观世界民主国族,游戏规则都是民主,但政治文化不一样,因而,便五花八门了。
比如,在意大利,仿佛一定的腐败是政治运作的前提。迄至贝卢斯科尼上台,简直就是在拿国民开涮,也是在明目张胆地嘲弄民主,将金钱政治、私性政治乃至于流氓政治的民主负面,显山显水,暴露于光天化日。但是,老爷子还不照样纸醉金迷。在法国,总统搞个拉链门,有两个太太,国民未感惊诧,不觉得是个事。但是,如果此事发生在北美,清教传统,好家伙,不得了。
的确,相比而言,拉丁一系,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法国,都比较腐败。尤其是意大利,民主政治玩到贝卢斯科尼这个份上,简直成为福山笔下的“表亲专政”了。
它们说明,民主政体若无清洁机制和刹车装置,很容易自我腐蚀。
当年理学家们指陈读史之枢机,在窥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所以进退,便是格物”,以此观之,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秩序的大经大法,吾人尚需好生格一格呢,而最好的格物之法,不外乎下场操练。让国民成长为公民,公民经由选举兑现为选民,事关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实在是刻不容缓。
就政治文化而言,过往十来年,中国已悄然变迁,甚至于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举其要者,概如下列:
首先,社会大众在信息接受上的成熟,更多地自觉于自我判断和甄别,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和精神。
其次,不惟官学商精英,就是一般民众,多半都将权力的民主授受当作天经地义。就官员来看,心里多半认同人民出场式的赋权仪式之不可少,或者,之不可免,而对公共权力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再次,对“君师一体”,人们早已腻味,于享有良好私德信誉的独立人士,无论僧耶儒,更信任,这意味着某种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的发育成长。
最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识到并承认社会本有独立位格,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凡此种种,是数十年来“启蒙”的善果,接续的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它们作为政治文化,可以预期,一种最为深厚而蕴藉的民情与人心,必将于最近的将来与现实政制良性互动,于中国政治变革发生重大影响。
民生合法性的局限
问:说得是。不过,改革向前走,最大的动力或不是某种理想,而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只有迈向现代秩序的改革能给改革者带来最大利益时,改革才难以逆转。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呢?
许章润:政治总是充满着功利主义,虽不无理想,更不缺卑劣。刻下总体趋向虽说仍旧晦暗不明,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之不可阻遏,却也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湛蓝的天空。在此语境下,总体逻辑是在往世俗理性方向转,自然不能不和一己身家利益挂钩。而最大的利益是安全与发展,首先是身家性命和财产的安全。就此而言,就有利益交集的空间,而引发出政治透明、法治严明等话题了。
与乌托邦政治不同,此世的一切改革,均需获得“人民认同”。这听起来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刻下中国的语境,特别是与政治的总体氛围不太搭调,但究其实质,一点也不假。——君不见,上述三个“低头致意”,哪一项不是“人民认同”这一压力下的产物!而且,在我观察,这一进程依旧在持续,时紧时松,忽明忽暗,高高低低,则前景可期,不妨“谨慎乐观”也。
其实,刻下的“生存与发展”脉络,不脱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政治主流,而以中国历史汇入了世界历史,展现的是晚近这一波枢纽文明收束时段的中国景象。其间重要一端,就是把人从道德主体还原为肉身的世俗理性,家长里短过日子成为政治,而确保其安宁和接续,蔚为政治合法性。
现在的问题,也是先发起来的西人的教训所在,就是对肉身的照料和对德行的料理与自我料理,要并行不悖。否则,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难免集体堕落,汲汲耽溺于俗世欲望的结果是失去了满足它们的积极条件,也是欲望本身疲弱。地中海文明以还的这一波文明劲道渐显疲态,原因复杂,此为一端而已。
问:世俗理性是从哪里起源的?
许章润:此事说来话长,牵连晚近三五百年的世界史,及所谓的人性或者普遍人性。
大约而言,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主流思想是回归世俗理性,因为此前或因宗教太具垄断性压迫性了,所以人性的俗世一面似乎颇感压抑。这一脉思路,秉持地中海文明的强力,推展至全球,遂形成了解构神圣意义的所谓世俗化浪潮。
当然,何为神圣?世俗性在不同文明和国族如何展现自身?凡此种种,并无普适标准,恰需映照于具体时空,有以然哉。这里要挑明的一点,也是颇为吊诡的一脉是,晚近三百年的近代史上,革命和战争是主题,它们无一不是世俗化大潮的产物,却又秉持极度的乌托邦色彩和近乎神圣的理念。
比如,苏俄式的乌托邦,不仅自我神圣,而且,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主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社会安排的一个反拨,意欲超越,仿佛希冀站在更高的位置行使武器的批判的职责。由此一路狂飙突进,造成小部分人穷奢极欲,大部分人忍饥挨饿,而所有人均战战兢兢、觳觫立世的恐惧时代!
所谓“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抛弃此种思想路线和政治价值,而拥抱主流的现代文明。此于1860年以来的三波“改革开放”,并无不同,可谓心同理同。但是,问题在于,既有的这种现代性方案,积弊甚深,沉疴甚重。其间,一个基本倾向是向物质主义全面低头,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世俗欲望的满足,构成了现代政制获取人民支持的合法性的重要支撑点,这便导致人性猖獗嚣张,简直无法餍足,许多问题遂联袂而生。
问:“民生”牵扯到所谓的“民本”。传统中国不是讲民本吗?某种意义上,“仁政”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本呢?
许章润:本来,就建设“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这一整体性历史文化转型而言,需要解决的义项包括民生、民族与民权诸题,而不只是民生一端。概言之,“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基本道尽了“中国问题”的荦荦大端,内核则是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的“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之四位一体。
晚近百多年来的生聚教训,国共两党,一切的改良、革命与流血牺牲,所有的“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围绕于此而展开的。把它们悉数以“民生”笼统,是统不了的,也是兜不住的。
民生重在福祉,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而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条件,天经地义,也是一切政体首当尽心尽力的。但政体本身并不以解决民生为职志,毋宁,旨在提供政治秩序,让秩序建制化、程序化,从而,实现全体国民和公民在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和民生,由社会本身打理,政府行使治权,容忍经济和社会的自我发育,从旁协力同行就可以了。
盖因特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民生问题是无底洞,永远也解决不完。一个政府大包大揽要解决全部民生问题,这很危险。其危险不仅在于可能推导出人们对于全能政府的渴求,而且,暗含了极权政治的因子。
另一方面,长期把民生作为合法性基础,还可能会造成政治市侩主义,讨好民众、透支福利。美国长期这样做,也可以做,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将成本分摊,印钞票。可中国做不到,没法子。而且,很可能造成民粹主义。如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高度的行政极权导致人们对于极权的高度依赖,凡事都求助于政府;反过来,若果遭遇不幸,则直接归咎政府,甚至如托克维尔所述,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要怪到政府头上。
的确,一个集权的政府和政制,很容易造成“愤慨转移”,认为什么都是政府不好,都应由政府来大包大揽。——集权政制反而造成了国民的“政府依赖症”,也就是“公民懒惰症”,说来匪夷所思,却千真万确。
新加坡的政治参与问题
问:先前提到新加坡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治理认同难道也没个底吗?
许章润:作为一个小型城邦国家,新加坡将华人的经世之道发挥到了极致,也是将英国式的治理和牟利心机学得最入心坎的。其以高等华人自居,骨子里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势利与精明。历经数十年家父式管制,城邦调理首在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有向心力。
但是,即便如此,年轻一代要求政治发言权的势头,已然浮现。对年轻一辈,凡此福祉等于“与生俱来”,自无前后比勘而油然欣喜的可能与必要,他们要的是自家没有但“别人家有”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参与权。两年前大选换届之际的街头抗议,仿佛一夜间冒出来,出人意料,实则情理之中。而且,还将水涨船高,也是可以预言的。再者,既是“家父”式治理,则“家父”权威代际递减是铁律!
相比而言,刻下中国政制绩效不错,行政管制也还能对付。
问题在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平权与政治参与问题,必将浮现。就前者言,倏然显豁、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最大挑战,对此无策无方,则人心不服,根基不稳。就后者言,如何应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包括表达、结社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等,已刻不容缓。
再者,就意识形态和国家哲学而言,也得讲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话。在此,“讲好中国的故事”,同样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