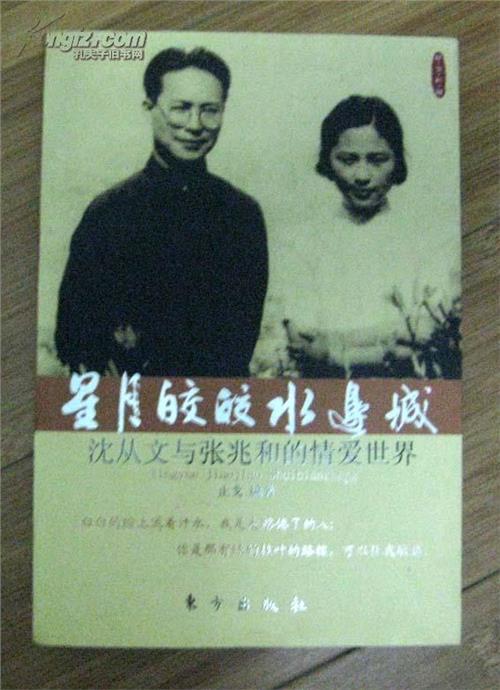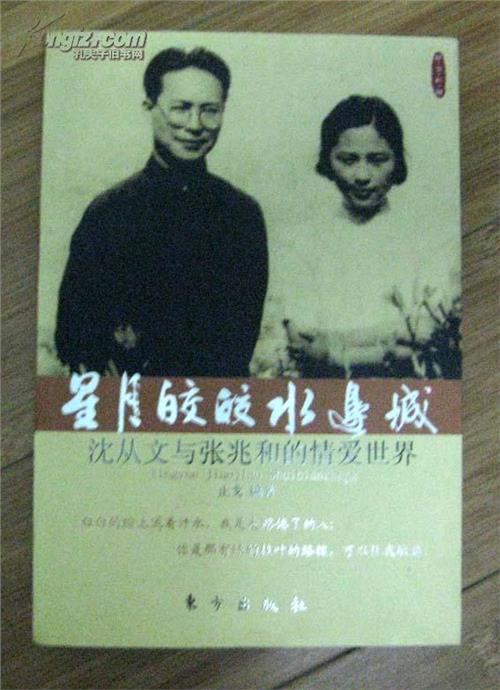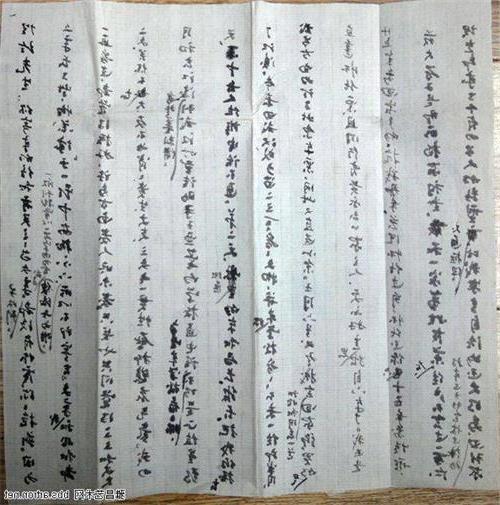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后代 沈从文后半生:不被时代裹挟的孤独行者
他的人生在1949年后被劈成两个部分。前半生传奇多彩,但记录众多;后半生一路压抑,却鲜为人知。沈从文的后半生始终如孤舟般远离潮流,但潮流过后,他的文字与研究反而越发凸显其价值。
1948年底,北平即将易主,澎湃的革命热情漫山遍野。
沈从文表面却异常“冷静”, 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的自由作家,沈从文始终警醒地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但是内心里他早是伤痕累累——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后,他就深陷“民族自杀悲剧”中不可自拔。这一年沈从文46岁,他的前半生可以用传奇来概括——一位来自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以70篇清新脱俗的文学作品名噪一方。
“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这样解读沈从文。
张新颖并非偶然走近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从他1992年偶然在《收获》上读到《湘行书简》时,他仿佛读到了沈从文一生的脉络——1934年,沈从文行走在湖南横石,看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100元争吵,他不禁感叹起人生的“意义”,多数人为生而生,而沈从文觉得应该像少数人那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然而当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后,又觉得历史不应该那么“宏伟”,那些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沈从文如是写道。
“沈从文笔下的船夫、船娘乃至石头,都是河流中不可缺少的生命。某种角度看,这又是一条‘人’的河流,我从这里明白了沈从文心底最关心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喜怒哀乐、劳作、创造以及智慧,这也可以解释后半生他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张新颖说。
从那时起,张新颖开始真正琢磨起沈从文,多年来,他陆续出版了《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然而张新颖更希望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沈从文的后半生世界——1949年沈从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两部分,前半生传奇多彩,但已记录众多,后半生一路压抑,却鲜为人知。
十年磨一剑,《沈从文的后半生》如期出版,张新颖说他并不想为沈从文“代言”,因为他想真实还原出沈从文在动荡年代里漫长的内心生活,但是这种丰富、复杂、长期的精神演变,并不能推测、想象、虚构而来,所以张新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资料中找出沈从文的“原话”。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概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张新颖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孤立
“我是来征服你的。”
多年后,沈从文仍然记得他到达北平前门车站时,放出的豪言壮语,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豁然敞开的古城大门,日后却将他深深囚牢。
尽管沈从文小心且痛苦地悬走在“政治”边缘,却还是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1948年,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历史的转点谈文学,自然没有那么“纯粹”,话题不久就引到了政治上,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喻成“红绿灯”,他表示文学虽然受制于政治,但是否有保有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对此,他同冯至、废明、汪曾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不久,沈从文就为自己为“红绿灯”话题发声而苦笑,因为他越来越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文学,要求他必须把政治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书信中写道:“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至少从此时沈从文的笔调看,他还是克制而平静的,沈从文已经预见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深知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代若干人的”,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沈从文决定“封笔”。
风暴还是很快袭来。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还全文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借此直指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时隔不久沈从文又收到了威胁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
精神重创与无力感蔓延,沈从文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他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渐渐沈从文感觉到这种“无力感”只有他一个人在苦撑,沈从文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的命运,却没有同代人陪伴。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我说的全无人明白。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与。金提、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 、不肯如此。”张新颖说。
在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张新颖后来翻阅这些资料发现一个细节,在后一篇的末页,沈从文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
“这里的解放,其实是解脱的意思。”张新颖说。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中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又割腕,最后还喝了汽油,所幸,张兆和的堂弟正好来此,发现房门反锁,于是破窗而入。此后沈从文被送到精神病院。
“沈从文不是现代舆论启蒙出来的、可以和过去断然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来自苗汉混居、偏僻山野的生长经验,这种野生淳朴的力量深根于他的内心,要在一夜之间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经验,绝无可能。”张新颖说。
在疯狂与谧静中挣扎“新生”
1949年4月6日,沈从文在精神病医院写了一上午日记,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似乎“平静”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 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沈从文决定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变成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及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沈从文用《红楼梦》隐喻了自己的无奈。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沈从文如是说。他甚至写信劝服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北上,并在信尾提到“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一样样做下去。”在张新颖看来,此时沈从文何尝不是在说服自己——接受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杀对于沈从文是‘因祸得福’,他为什么后面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还是幸免于难,就是因为前面已经死过一次了,等于在绝望当中重新诞生一次。1949年其实是沈从文一个重生的起点。”张新颖说。
而在沈从文看来,从事古代工艺史研究是“一件急得不能再急的事”,周围的朋友却认为此举是沈从文主动解救疯毁中的自己,他在给好友丁玲的信中坦诚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对于放弃写作,沈从文并不觉得惋惜,甚至有一丝”幸灾乐祸“——”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来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被安排在陈列组,主要负责清点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为观众做解说员。
弃文去研究“坛坛罐罐”,在很多读者看来,是沈从文逃避且无奈之举,但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后半辈子倾心古文物研究,实则是“主动而为”,“这个选择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沈从文一直乐于背负“历史”的重担——早年在湘西当兵时只有微薄的补贴,而他的包中却总是放着昂贵的《云魔碑》、《圣教序》、《兰亭序》等书,而据汪曾祺的回忆,他与沈从文谈文学的频率,远比不上谈论陶瓷、漆器、刺绣。沈从文可以对着一块少数民族的挑花布图案,和友人一起赞叹一个晚上。
然而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有多少研究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在历史博物馆的最初十年,他只是一个坐在过道的“临时工”,拿不到必须的办公材料,被嘲弄侮辱为“外行”,甚至他的儿子,也认为看不出父亲倒腾古董“有什么意思”。
沈从文却依然固我,他在1968年所做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中坦诚道:“我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我不是想做专家的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破除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性迷信。”
“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张新颖说。
与文学“初心”的博弈
1953年9月底,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理解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并不是完全否定,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做专业作家。
沈从文的内心何尝不想与文学再次相遇!与坛罐相伴的日子,沈从文几次提笔——50年代初在革大学习,一位朴实、寂寞的炊事员深深打动了他,沈从文写成了《老同志》,然而七易其稿后,只能搁笔作罢。而在1951年,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去四川参加土改运动时,深感“从早上极静中闻朱雀声音,而四十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这又让他燃起“创作的心”。
1958年“大跃进”,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做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的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对于父亲当时的创作,沈从文之子沈虎雏的评价是——他当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写的还顺溜。
“这其实是接受大跃进形势教育,用笔来歌颂新人新事。”张新颖说,这样的文章,写的怎么样,沈从文自己怎么能不知道呢?
而在张新颖看来,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作品虽然大多“谨小慎微且乏善可陈”,但是他一部很少被人提及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却是可圈可点,“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还能追寻到沈从文之前作品中特有的印记,你可以感觉到他写这部作品时的放松,这种状态只此一例。”张新颖说。
让沈从文的文学“初心”直接大受毁灭的是,开明书店通知他,以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书稿均已毁灭,于此同时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沈从文失望之极,他写信给大哥,希望能将家中他的作品也烧毁,以免误人子弟。“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经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沈从文对大哥说。
而接下来王瑶的“补刀”又让沈从文难以介怀——1954年,《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作者王瑶直指沈从文的作品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写底层人物“只有一个轮廓”,总之缺乏观察体验总是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奇多,但是空虚浮泛是难免的”。王瑶在自序中特别表示“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
这种阴影总是困扰沈从文以后的文学创作。1960年,他准备请一年长假,以其妻张兆和的堂弟张鼎被国民党伤害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然而身体的病痛加上心理上的顾及,让他“提不起笔。”而张兆和却认为沈从文总是为王瑶这样所谓的批评家嘀咕不完,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足。
虽然沈从文再也没真正跨进文坛,但他始终在“窥探”着里面的一切,他认为报纸上很多诗毫无“感兴”,“艺术和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而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经历,却在不可设想中一例销毁了。”
“沈从文年轻时的确有很大的野心,他觉得自己作品应该拿到世界上,但是这样一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他一辈子都不甘心,从此不断尝试,但他失败了,也只能失败。”张新颖说。
“他无法跟随时代变化的每一步,却比时代走得更久”
沈从文在坛坛罐罐绸绸缎缎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有人说他把文学梦寄情于历史,张新颖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他做的工作和文学的部分是相通的,历史研究有它的独立性。我提出过一个观点,如果学问做得够好,学问本身会反过来滋养你的生命,滋养你的身体和精神。沈从文就是这种。”
和文学创作一样,沈从文总是充当“打前战”的角色——此前对于绸缎的研究一片空白,因为它经常附着尸身,且污染严重,是文物中最娇贵且脆弱的,在很多人看来研究绸缎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而倾注沈从文下半生大部分心血的,是编纂《中国古代服饰资料》——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周恩来提出可以编纂一本关于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这个想法与沈从文“不谋而合”,从1960年初他就开始实施服装史研究,然而他全凭一己之力,艰难前行。
这本中国服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前后耗费多病缠身的沈从文8个月心血,它对中国历代服饰问题进行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然而就在即将印刷开印之际,因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批评意见,这本书的出版就此搁浅。“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文质文化史中服饰一脉,要讲的恰好是普通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历史”,张新颖表示。
“来不及”的焦虑贯穿了沈从文的下半生,他总有时不待我的感觉,他总想尽快做好服装史的资料,没有料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埋伏在前面。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根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沈从文不可避免被抄家,其中他的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都由历史博物馆”代为消毒。这让沈从文还原本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计划,连根拔除。
日后当记者和他聊起“文革”往事,沈从文说,那时他最大的功劳,就是打扫厕所很干净。来访的一位女子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谁也没想到,沈从文抱着这个女子的胳膊,嚎啕大哭,鼻涕眼泪一脸。沈虎雏说父亲就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但晚年时,沈从文中风了,手不能写,说话也不利索,只能吐露简单的字。所以眼泪代替了很多表达方式,这里面也有他一生的屈辱。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静静地离开世界,国内的媒体集体“失声”,直到5月13日,中新社电讯才惜字如金般地播发了这一消息,“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用什么规格报道”,好友巴金愤愤不平。
多年后,诺贝尔评委马悦然无不惋惜地透露:“如果1988年沈从文不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沈从文虽然有无法跟随变化的时代走的一面,却比时代走得更久。他曾经远离潮流,而潮流过去之后,沈从文的东西反而能保留下来。”张新颖对《小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