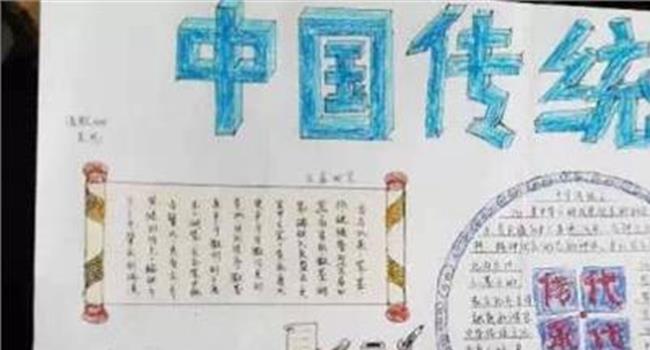张新民的书 张新民:守护文化 是生命力量的牵引
我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文史兼治,教中国古代史。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受父亲影响,我背诵过《论语》《大学》《中庸》等一类的课蒙读物,不知不觉,中国文化的血脉,就流淌在生命之中。古人常用“浃骨沦髓”来作比喻,说明个人的小生命是可以融入文化的大生命之中的。

因为“文革”,学校停课,下乡当了近4年知青,读了不少文史哲的书,深入了解了中国的乡村社会,影响到了我后来的人生选择。
乡村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人的意志品质,我把自己下乡的后寨湾,比作王阳明“百死千难”悟道的龙场。我的“龙场”生活教会我动心忍性的功夫,那是花任何学费也买不来的生命的学问。当然,“书荒”的年代也产生了知识饥渴的问题,于是四外访书、求书、读书也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有时候步行40多里路到县城,就仅仅是为了求人借一本书。

我后来治方志学读到的第一本志书,就是当时在县城找到的傅玉书撰作的《桑梓述闻》。这也是一种有趣的因缘,一本书竟会将人带入一个世界。
知青生涯刚一结束,恰好父亲被人抄走的藏书,有一部分得到了归还,满足了当时倍感饥渴又无书可读的年轻心灵。伴随我度过青春时光的,从此又多了一批中国古典名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就是那时候通读的。一部《资治通鉴》,一天读一卷,用了一年时间才读完。古典世界向我开启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珍藏在心中的价值与智慧。

如何读书,却总是受到生命力量的牵引。在读研究生之前,我就开始协助父亲撰写《史通笺注》,跑了全国好几个大图书馆查阅资料,很想将来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批评史。考上研究生后,恰好全国方志修纂工作刚刚恢复,因为吉林省编纂方志丛书约稿,我只好转入方志研究工作,撰写了一部《贵州地方志考稿》。

这部书稿我花了两年多时间,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通读了近300部贵州地方志,白天抄书做卡片,晚上整理作提要。书稿后来油印成厚厚5大册,分赠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当然也发挥了一点开风气的作用。
已故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说,他与修志同道带着油印稿跑遍了全省81个县,到一县即如数家珍介绍当地历代志书修纂的情况,我所做工作,通过他们也发挥了推动新志编纂的作用。
1985年我开始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受生命好奇探问力量的牵引,一度沉迷于考据,关注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依然想在考据的基础上撰写中国史学史书稿。由于考据文章写得过于老气,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托人打听,问我是不是已经70岁了,我也自嘲未老先衰,年未及40,即已成为学界的老先生了。
我多年读书治学,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中,痛感中国文化长期遭到人们的误读误解,遂将兴趣转移到了传统文化义理系统的梳理。但任何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都是需要载体的,于是我便调入贵州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目的是通过书院办学模式来坚守自己的人文理想,更重要的是向世人昭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我想每一个走进书院的人,都会感到中国文化活泼的精神,尤其是它与现代性融合后所展示出来的意义魅力和价值吸引力。
为思想文化注入新的生气
儒学研究是我长期从事的一个学术领域,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吸引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当然想有一个刊物来传达中国文化和平中正的广大精神,恰好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于是我便想到创办一个以陆王心学为符号标志的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
办刊物从组稿、编辑到出版,其中也包括经费的筹集,学者队伍的联系,都耗去了个人不少的时间精力,至于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更非局外人所能知晓。但毕竟我们在王阳明受到批判,传统心学学派打入冷宫的年代,创办了全国第一家阳明学研究的刊物,无疑推动了阳明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阳明学如何由冷变热,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当然更是点火助燃的推动者,但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缺乏扎实研究奠定的学术基础,任何用虚假语言堆砌起来的瑰丽大厦,最终都是要坍塌毁灭的,难忘的依然是自己寂寞耕耘的岁月。
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无论读书求学,或者潜研穷索,乃至教书讲学,其实就是自己心中时时升起的关怀和愿力,即使创办《阳阳学刊》,也是为了上溯先秦原始儒学,下联现代学术发展,寻找家国天下安身立命的发展新路径,是内心的人文关怀和愿力引导自己行走在不断求知探寻的人生道路上。
为地方文化研究拓展新领域
检读爬疏地方志是我从事地方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始,迄今为止已有了近40年的研究经历。从乡土社会认知或解释中国,我以为也应该是学者关注的一条学术道路。最近我们出版了80册的《赫章彝文古籍合集》,就是多年关注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的结果。
但是,就民间乡土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而言,耗费我时间精力最多的,仍是清水江流域民间契约文书的考释与整理。“清水江文书”数量之丰厚已超过了徽州文书,我根据自己4年的知青生活,本能地知道它的重要,与乡民的密契接触,也使我始终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出于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自觉职业判断,10多年来我一直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呼吁认真加以抢救和保护。
整理考释清水江文书,当然离不开田野调查,10多年来我跑遍了黔东南州的各个县,深感清水江文书是乡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始实录,每一份文书后面都站立着活生生的人,有着活生生的故事。活生生的人当然有他们的交往世界,活生生的故事也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实际,二者交织互动,正好构成了族群集体的共同记忆,当然也表征了清水江流域悠久文明的真实内容。系统及时地整理并出版发行,显然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我们整理的首批《清水江文书·天柱卷》共22册也已公开出版,以贵州本土学者为中心,已形成了一批全国性的研究队伍。以此为基础,贵州学者已先后拿到了2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或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已相当可观,清水江学已成为可与敦煌学、徽学鼎足并列的国际性显学。
这当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其中的参与者而已。严格地说,清水江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诱人。我自己只是为他人开山铺路的一块石子,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行走在更加宽广的学术大道上。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1950年3月生于贵阳。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兼职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区域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撰有《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等多种学术专著,整理点校《锦江禅灯》《黔志》《黔游记》等多种古籍,主编《黔灵丛书》《天柱文书》(22册),创办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