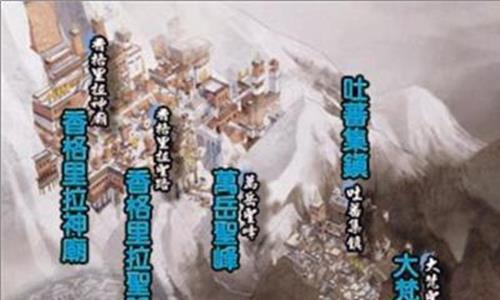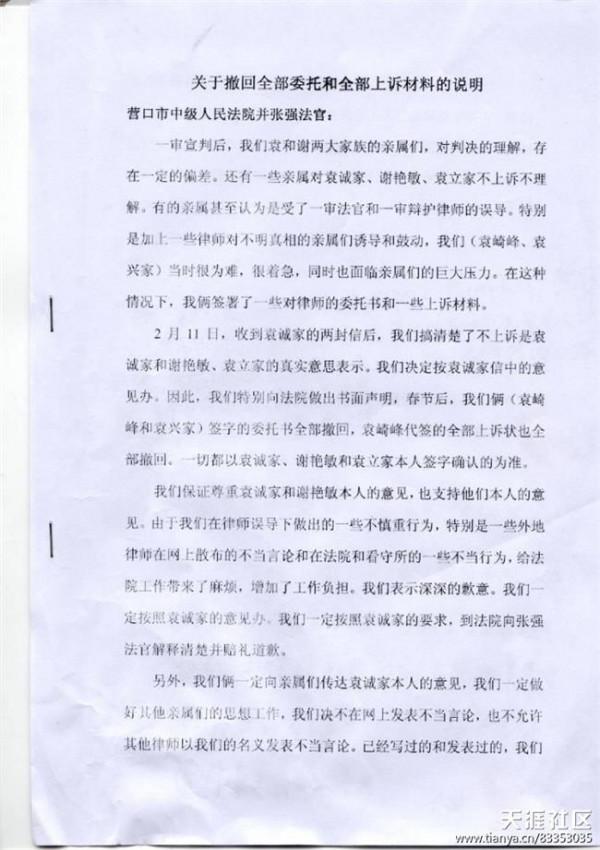中医火神派孙秉严医案 经方为主 用药简练——张存悌谈中医经典火神派
张存悌主任医师新作《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吴附子 吴佩衡》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京东、当当、亚马逊及全国各大书城有售,
欢迎广大中医师、中医院校师生及中医爱好者选购。
经方为主,用药简练

——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
十年前,编者刚开始研究火神派时,即将火神派分为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两类,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就现象来看,虽然同是火神派,同样擅用附子,但各家传人的选方用药理路却有明显不同,象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人的风格较为一致,大多数是选用经方,与郑钦安的风格相近;而象祝味菊、卢门等人就另有一套,如祝氏温潜法,卢门的桂枝法、附子法等,很少用经方,显然不同于吴佩衡、范中林等人,明眼人一看他们的医案就知道。

由此,出于研究的需要,就分了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两类。
随着研究的深入,回过头来看,这种分法确实显得必要,对于研究火神派,分清源流,是十分重要的。
广义上说,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乃至诸多火神派名家被冠以“吴附子”“祝附子”之类的雅号。所谓“擅用附子”,虽然体现在广用、重用、专用、早用四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广用,即广泛应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亦即广义火神派。由此才涌现了火神派传人各种不同的用药风格,也可以说,派内有派。

诚然,派内有派这种现象在各家学说中是常见的,例如温病薛、叶、吴、王四大家虽同属温病派,但各家是有各自侧重的。裘沛然教授说:“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理论是一定的,但治法用药却是“无一定”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关键是,作为开山宗师,郑钦安的用药有什么特点,研讨他的用药风格,有助于我们领悟较为正宗、纯粹的火神派风格。同时,作为火神派源头,通过比较看出后世传人的某些用药风格,与郑钦安有什么不同。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而是学习郑氏学说、明确选方用药的基本工夫,“遵得佛法便是佛,遵得圣道便是圣。”这就是分清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的意义所在。
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最重要者有两点:
一、选方以经方为主
郑钦安的学术根源于伤寒论,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他崇尚仲景,尊“仲景为医林之孔子”,“真是仙眼仙心,窥透乾坤之秘;立方立法,实为万世之师”;他熟谙六经,认为“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神奇;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绝妙”,他著有《伤寒恒论》,卢铸之先生称“郑师为仲景后第一人也”,他对伤寒研究之深之精,无需多议。
因此,从理论上他偏重经方,倡用经方。临床选方则以经方为主,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治阴虚则“人参白虎汤、三黄石膏汤,是灭火救阴法也;芍药甘草汤、黄连阿胶汤,是润燥扶阴法也;四苓滑石阿胶汤、六味地黄汤,是利水育阴法也。”看得出,无论阳虚还是阴虚症候,大多数选用经方,这一点没有疑义,“决不有差”。
郑钦安虽然有时亦称“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所引时方,出不得已,非其本怀”(《医法圆通·沈序》)。因为时方“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终究倡导的是经方。
试观其书中治病选方,随处可证:
如胀满一症,“予意此病治法,宜扶一元之真火,敛已散之阳光,俾一元气复,运化不乖,如术附汤、姜附汤、真武汤、桂苓术甘汤、附子理中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附子甘草汤之类。”(《医法圆通卷二》)。一口气举了7个方剂,其中5个系经方。
治“吐伤胃阳,胃阳欲亡”之证,法宜降逆、温中、回阳为主。“方用吴茱萸汤,或吴萸四逆汤,或理中汤加吴萸俱可”(《医理真传卷二》)。
健忘一症,“老年居多”。郑钦安强调,此症“以精神不足为主”,治疗“宜交通阴阳为主”,倡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切勿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与参、枣、茯神、远志、朱砂一派可也。”仍是经方居多。
虽然郑钦安没有留下专门的医案集,但从文献中散见的几个案例依稀可以看出他的用药风格,何绍奇称“如同浑金朴玉,阅之弥觉可珍”,爰选录几则,以证明其经方之用:
如治成都知府朱大人的夫人的吐血病,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用的是四逆汤原方。
“予尝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空,精神困倦,少气懒言,半载有余,予知为元气散漫也,即以大剂吴萸四逆汤治之,一、二剂而胀鼓顿失矣。”
“一人病患咳嗽,发呕欲吐,头眩腹胀,小便不利,余意膀胱气机不降而返上,以五苓散倍桂,一剂小便通,而诸证立失。”
“余每临症,常見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伤寒恒论·太阳上篇》)
“精滴不已:大凡好色之人与素秉不足之人,精常自出,此是元阳大耗,封锁不密,急宜大剂回阳,交通水火为主。予尝以白通汤治此病,百发百中。”
阴证发斑,“法宜回阳收纳为主,如封髓丹、潜阳丹、回阳饮之类。予曾经验多人,实有不测之妙。”
元气外浮牙痛,法宜回阳,方用白通汤、四逆汤,“若兼头项、腰、背痛,恶寒,于四逆汤内稍加麻、桂、细辛亦可”(《医理真传卷二》)。
看得出,各案基本上是伤寒原方,即使加味不过二三味,十分精确简练。
经典火神派必定是经方派,广义火神派一般不用或少用经方,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某些火神派名家自命伤寒派,不提火神派,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许是“究竟从伤寒入门者,自高出时手之上”(汪莲石言)这种意识使然?
或问,这样看来,经典火神派与伤寒派不是相同了吗?非也。火神派与伤寒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青出于兰,不同于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学派。简单点说,区别就在于对附子的广用和重用上,上文“医之能事,附子毕矣”已经陈述。当然,具有经方基础,再掌握火神派,那就若同锦上添花,如虎添翼。
二、用药简练
经方用药是简练的,113方仅用药93味,平均药味为4.18味,由3~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占82.3%。其药味加减也是十分严谨的。明代川医韩飞霞说:“处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简净。”“简净”二字说得何等传神。
郑钦安运用经方,谨遵仲景法度,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四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所谓“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法度简练。从他自创的几个方剂亦可看出,潜阳丹、姜附茯半汤均为4味,补坎益离丹5味,而姜桂汤、附子甘草汤则仅仅两味,确显经方用药特点。
综上所述,郑钦安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选药以经方为主,用药精纯不杂,每方多在五六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一二味、二三味,法度谨严。决不胡乱堆砌药物,更无所谓“广络原野”之芜杂,这就是郑钦安的用药风格,具有这一风格者,编者称之为“经典火神派”。
后世较为忠实的继承了郑氏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经典火神派风格者,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周连三、曾辅民、黎庇留、萧琢如先生……,堪称经典火神派的代表,观其医案具有鲜明的经方法度和郑氏风格。仔细考究,发现他们大多数医案用药不超过八味,虽非定例,究少例外。
经典火神派继承了经方药简方精的风格,即或不用经方,投药也是简练的,典型如郑氏研制的潜阳丹、补坎益离丹,每方仅用药4味,确是经方法度。如此简练的用药风格,应该说是一种纯正的境界,需要多年修炼,绝非一蹴而就。
为什么要堤倡用药简练呢?当然是治病求本的要求。治病求本,讲究用药专精,有的放矢,景岳指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
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用药不能“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范文甫云:“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
古人云:“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世医动辄以简为粗,以繁为精,衰多哉”——是说医生用药少者,其医术越精;用药多者,医术越粗陋。俗医动辄以用药少为粗疏,以用药繁多为精当,差得太远了。衡量一个医家医术如何,有个简单的方法,不用看他药开得好不好,只看他的方子开得大小,药味多少。
药味少者水平高,药味越多水平越低。一个方子若是开出二三十味来,肯定不足观。俗语说,“药过十二三,大夫必不沾。”意思是说开方若超过十二三味药,这个大夫肯定不靠谱。其意与“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相比较,前者更通俗,后者更典雅,二者异曲同工。
须知,随意多安药味,有时非但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作用,反而可能一加一小于二,原因就在于那些药物互相掣肘,影响主药发挥作用。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既或顾炎武也曾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谈及此事:“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术已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说明用药贵精不在多。
■广东弟子张某,其儿子2岁,因肺炎高烧入院,经治疗后烧退,咳减,大便日3-4行,带药出院调理。出院第一天,服用抗生素后便泻加剧,至次晨,日夜达20余次,皆为水状及不消化食物,时伴呕吐。中药用藿香正气汤、参苓白术散均未收效。
第二天下午见小儿神情疲惫,无汗,时有咳嗽,并闻及喉中痰鸣,背部可触及痰鸣振动,因思当是外寒内饮为患,拟小青龙汤原方:麻黄5g,桂枝10g,炙草10g,半夏30g,白芍10g,细辛5g,北五味3g,干姜5g。煎成60 ml,当晚8时服20 ml后,熟睡一夜,大便仅泻一次,次晨大便成形,咳嗽大减,喉中痰鸣消失。
按:该张某平时治咳常以小青龙汤加北杏、川贝、紫菀、白前等品,适逢此前一天与编者交流,谈及“经方运用当以原方为好,加减不宜太多”观点,并特别举了小青龙汤为例。受此启发,此次专用小青龙汤原方,不意效果反而比加味后要好。
仲景组方严谨,每加减一味药,都有加减的道理。某些研究伤寒的人,动曰“师其法不泥其方”,说是用经方,常在原方后加一大堆药,或者随意加减,恐怕失却经方原意,蒲辅周说过:“白虎汤中加上三黄解毒泻火,……就成了死白虎。
”顺便说一下,李可先生虽然常用经方,却作了较多“改造”,如改良乌头汤、变通大乌头汤、变通小青龙汤等,加入很多药味,与经方已有很大出入,倪海厦称其为“半个经方家”。当然编者很佩服李可先生,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只是这样对经方近乎普遍的改造,是否得当,值得推敲,试看曹颖甫、刘度舟、黄煌等伤寒名家的案例,那个简净劲儿,才真让人佩服。
仲景本来已有三承气汤,吴鞠通《温病条辨》中另外整出了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护胃承气汤等,试看今天谁还用这些杂七杂八的承气汤?而仲景三承气汤仍在为人所赏用,说明什么?说明经典是永恒的,不可替代的。试图改造经典是不明智的。
在强调上述两点的前提下,经典火神派还具有下面两个优势:
一、经典火神派是简单的。大道至简,经典的东西常常是简单的。郑钦安除使用自拟的几首温阳方和几首时方外,其余皆使用《伤寒论》原方,而且常用的仅十几个方、几十个味药而已。凡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建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
若是阴虚,在中焦用白虎加人参汤、三承气汤,在下焦用黄连阿胶汤,且其常用加减药物尚不及《伤寒论》所用的一半。真传一张纸,难怪敬云樵称郑氏:“认证只分阴阳,活人直在反掌,高而不高,使人有门可入。”
二、疗效可靠。郑钦安屡次称治病“百发百中”,“真有百发百中之妙”。敬云樵称其“只重一阳字,握要以图,立法周密,压倒当世诸家,何况庸手!”这个不是吹牛。经方疗效多数可以说,“一剂知,二剂已”,治病确实管用,本书所选医案即是明证。
编者以郑氏招法应世,疗效大幅提高,诚如郑氏所言,疗效差不多“百发百中”。常见病不用说,疑难杂症多能应手而愈,通常可以对患者说:“服药一周,慢性病两周,必须见效,否则另请高明。”
火神正道是钦安。水有源,树有根。郑钦安作为开山宗师,是以其著作和用药法度作为标志的。正本清源,欲掌握较为纯正的火神派理路,当从郑钦安原著和上述几家医案入手,这才是正宗源头。后世传承火神派者,充其量是流,不是源。
某些于经方之外另立一套体系者,可以归入广义火神派行列,但与经典火神派不可同日而语。如同研究伤寒,仲景《伤寒论》永远是源头,后世传承者即使再有“发展”,甚至“改造”,也代替不了经方原方。多么发展的东西也不可能取代经典,经典是永恒的,这应该是真理。
君子和而不同。最后讲一点,分广义火神派和经典火神派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没有褒贬之义,更没有轻视广义火神派的意思。实际上广义火神派开拓了用药思路,尤其是附子的运用,比如卢门的桂枝法、附子法,祝味菊的温潜法,用附子配以龙齿、磁石、枣仁、茯神;徐小圃治暑热症的温清兼施法;李可先生“破格救心汤”中四逆汤与山茱萸的合用;补晓岚先生的“补一大汤药”融温辛于一炉,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思路……,都有着一定影响,丰富了火神派的临床经验。
百花齐放,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