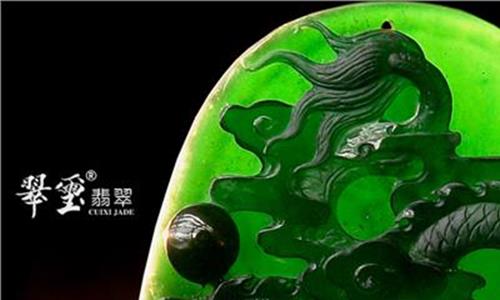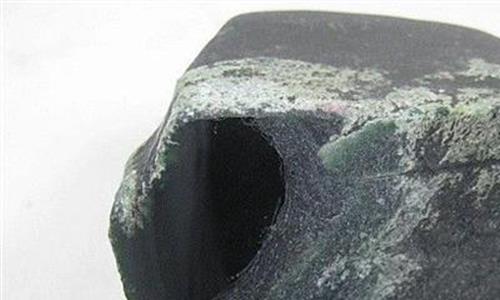曾子墨的母亲 曾子墨母亲帮我考大学
那时曾子墨也就几岁,她母亲赵遐秋老师天天背着她,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师范学院上班。大约1972年,赵老师从干校回北京,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尚未复校,所有人大的教师被分到其他高校工作,去北大的,北师大的,人大中文系很多教师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即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工作,包括赵老师。

赵遐秋老师在人大是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是她学问好,北大中文系毕业,古文功底极其深厚。二是她为人正派刚毅。为什么这么说?她在“文革”中是吃过大苦受过大难的人,是血水沸水里熬过来的女人。

据说赵老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官吏家庭。她的父亲1949年跑到台湾,她和母亲,好像还有个哥哥相依为命。她母亲是河南人,一口河南话,身体微胖,待人和蔼可亲,在人大西郊大院里,就是今天的人大校园,谁都喜欢这个老太太。赵老师本人极受尊敬,她对学生十分严格,一丝不苟,但平日对大家非常真诚热情,谁都知道她是个好人。就这样一位真诚负责的好人、好老师,“文革”时因不同派别间的争斗,让她吃尽苦头。

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我们这些“文革”中蹉跎10年的年轻人,以胜利大逃亡的心态疯狂投入高考。我们怀着破釜沉舟的信念,发誓赶上命运末班车,拼出自身的不凡与不甘,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遗憾的是,第一次高考我仅差三分未达录取线。我母亲焦虑地说,我请赵遐秋同志帮你补古汉语和作文吧。赵老师很忙,求她补课的人很多,但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并且当晚开课。我走进她家,当时天气正凉,赵老师刚下班,身上黑呢子大衣尚未脱下。从那时起,我开始向赵老师学习古汉语和作文,用现在的话说,赵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私人家教,一对一授课,不同之处是:分文不取。
从开始我就感到赵老师对我,应该说对我们这代人的深切关注。她的眉头微锁,认真回答我的提问,及时纠正每个错误,我被赵老师的紧迫神情渗浸着,深感时不我待,每分钟都可贵,我仿佛被她牵引着,跌跌撞撞去追赶失去的时光,急促的节奏和明确的方向令人兴奋,心中充满希冀。
有一次赵老师点评作文,我觉得自己写得很顺,一气呵成,肯定受夸奖。没想到她目光略带忧虑地问我,到底你想说什么?我连忙解释,是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那为何不直接说,非绕来绕去?我面红耳赤,心想你太不理解人了,难道真没看懂吗?赵老师接着说,写文章一定要想好说什么再动笔,写作的本质是思考。
就这一击,连同赵老师当时的表情,我再没忘记。这对后来我形成自己坦诚直白的文字风格很有影响。
还有古文。我们这代人的古文基础不是来自课堂,而是靠“文革”中读杂书获取的,非常凌乱,很不确定,这正是我第一次高考吃亏之处。赵老师当机立断,从《古文观止》中选出五六篇,我记得有 《曹刿论战》、《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等,给我讲解,并让我尽量背咏。
赵老师讲古文时令人陶醉,既游刃有余,又有音乐般的节奏感,谁说讲课不是艺术,谁说好老师不算艺术家,赵老师就是艺术家。落英缤纷怎么讲?她问。花落了,像雪花一样飘。嗯,可以这样理解,但还有一说你应知道,落,始也,落英指刚刚开放的花。刚刚开放?刚刚开放,知道就行,这问题应该不会考。古人云,举纲而目张。赵老师讲课就是个纲,把我东拼西凑的古文知识连接起来,形成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底蕴,让我终身受益。
19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和数学分都打了翻身仗。那时考上大学得意啊,狂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十年一剑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高兴得不知姓什么了。
在这种氛围下,人的心态也会异化。那天我远远看到赵老师拉着幼小的曾子墨,母亲一会儿看看女儿,女儿一会儿仰头看看母亲,她们向我走近,我想上前打招呼,说句谢谢老师的话,可不知为何竟躲开了!那时人大校园里有许多柏树墙,一人多高。
我躲到柏树墙的另一侧,望着她俩树影支离的身影从我身旁走过。我的脸通红,我相信我的脸一定是通红的,我的心咚咚跳,当时就觉得十分愧疚。30多年过去,现在想来仍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人怎能建功立业,难怪后来会漂泊一生呢!
我一直未能把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对上号。不久前有人说,知道吗,曾子墨是人大子弟,她母亲就是中文系的赵遐秋呀。我眼前哗地亮起来,涌出以上这些画面,微胖的身材,透明塑料眼镜,呢子大衣,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把头贴在母亲背后的小脸蛋,蹒跚走路的样子,母女的身影,这一切像《山楂树》的镜头,把那个时代空气中的味道、声音、服饰,最主要的是情感,潮水般冲进我的胸膛。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当年的小女孩儿如今已成为媒体明星,而我更刻骨铭心的是对她母亲以及那一代深厚宽广的知识分子的深深敬意,他们坚守了文明的根基,用肩膀托举出新时代的灿烂,他们的生命分量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谢谢您赵老师!请原谅我当年的浮躁。相信您从这些文字中能感到我的真诚和领悟以及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这不正是您对所有学生期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