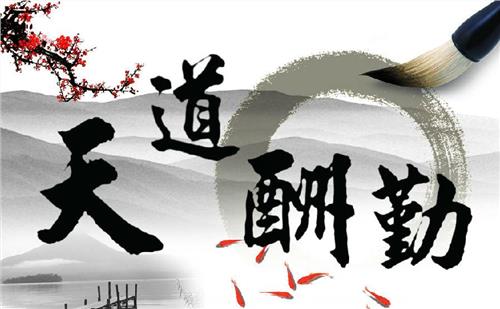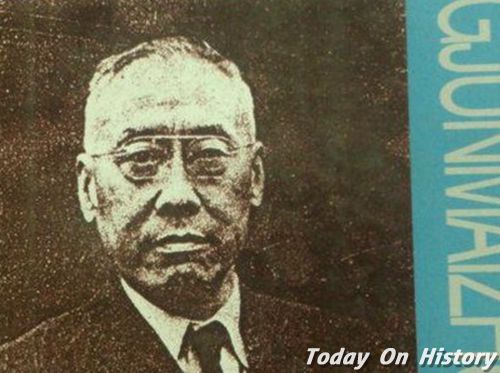张君劢人生观 张君劢:在“政治”与“学问”之间
张君劢(1887~1969),政治家、哲学家,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早年致力于政治运动,主张通过“改良立宪”的方式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民国政坛有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派势力”的代表人物。1923年3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由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末期“科玄论战”的序幕。

1930年代之后,他在投身民主宪政运动的同时也致力于学术研究。1949年之后,张君劢辗转海外讲学著述,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有《新儒家哲学发展史》、《中西印哲学论文集》等著作行世。

从欧战观察家到“治己”
1912年11月,沙皇俄国与外蒙古签订了《俄蒙协约》,规定“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蒙古在俄国的“协助”下建立“自治秩序”。消息一出,张君劢就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直斥袁世凯是造成外蒙危机的罪魁祸首。

文章一经刊出,随即被袁世凯查禁,张君劢本人也遭到了监禁。与此同时,张君劢所在的民主党内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处于内外交困中的张君劢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取道俄国赴德留学。

不过,张君劢此次留德其间的真正兴趣并不是他后来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甚至也不是他所修习的政治学,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张君劢对战争关注的痴迷甚至到了被房东老太太当作日本间谍向警方举报的程度。为了更好地观察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的影响,张君劢于1915年9月离开德国,启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欧战观察之旅。
张君劢回国之后即往来于于京、津、沪、宁之间,先后为对德宣战、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问题奔走斡旋,但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改良政治的宏愿,反而使自己陷入了一系列政治风波之中。
心灰意冷之际,他开始反思自己之前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在日记中写到:“问此一年来,所为何事,则茫然不知所以。盖自来救国者,未有不先治己。”本着这一“治国先治己”的原则,张君劢与蒋百里等人在北京组织了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的“松社”。同时,张君劢还为自己制定了具体的“治己”的方针:第一,学书写《圣教序》;第二,每日读《汉书》20页;第三,学习法文;第四,编写大学国际法讲义。
从“治国”转向“治己”,可以说是张君劢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治己”首先是儒家士人理想的反映,宋儒极力提倡的“修齐治平”对张君劢的影响至为深远,以至于他在现实政治追求受挫之际首先想到的便是求助于传统。
此时的张君劢虽然还没有作为“新儒家”登上学术舞台,但是儒家思想传统对他的影响已经显露。同时,张君劢所谓的“治己”在传统儒家的“修身”目标之外,还多了一个以树立现代主体为目的的启蒙目标。
在谈到组织“松社”的动机时,张君劢说到,“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存。唯有我思,故有是非。哲学之第一义谛如是,道德之第一义谛亦复如是。”或许此时张君劢对启蒙哲学与宋儒之间思想关系还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是他这一“治国先治己”的思想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作为新儒家的思想“起源”。
拜师奥依肯,重返“学问国”
1918年12月,张君劢跟随梁启超开始了第二次欧游之旅。巴黎和会结束之后,梁启超、张君劢一行带着极为痛苦的心情在欧洲游历,于1920年1月到达德国。当梁、张一行人到达慕尼黑之后,梁启超忽然想起来要去拜访当时德国哲学界执牛耳式的人物:奥依肯。
奥依肯曾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彼时为耶拿大学哲学教授。他的哲学秉承了从狄尔泰、席美尔以来的生命哲学传统,主张以人的生命或曰生活为中心,调和唯物与唯心、自然与理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奥依肯在耶拿会见了梁启超一行,张君劢在奥、梁二人之间担任翻译。奥依肯以诚恳的态度回答了梁启超的提问,并且在他们离开之后专门就物质与精神如何调和的问题写了长文寄给梁启超。
奥依肯的这种行为让张君劢大为感动,奥氏对待梁、张一行的态度与“外交家以权谋术数为唯一法门者”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由于受到他“人格之感召”,张君劢遂决定师从奥依肯攻读哲学,暂别“政治国”,专心建设“学问国”。在梁启超等人回国之后,张君劢遂返回耶拿跟随奥依肯攻读哲学。
师从奥依肯攻读哲学是张君劢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奥依肯的哲学一方面构成了张君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挑起科玄论战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儒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张君劢后来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以《人生观》为题目的演讲即是以奥依肯的《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一书为基础。
在“人生观”讲演中,张君劢秉承了狄尔泰、奥依肯等人将“自然的学问”(Naturwissenschaft)与“精神的学问”(Geistswissenschaft)相区别的观点,指出后者具有与前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支配精神科学。
张君劢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而发的。科学只能用来解决自然界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有关人的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靠“精神哲学”或者说“玄学”来解决。在张君劢看来,这种能够解决人生问题的“玄学”一是指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是指奥依肯、柏格森等西方思想家的生命哲学。
奥依肯以精神生活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与《中庸》中所讲的“尽性”有内在相通之处。二者都是要以精神生活来弥合现代科学所造成的主观(心)与客观(物)之间的分裂,实现主观(心)与客观(物)的统一。张君劢的“玄学”实际上是混合了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与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儒学新形态。
《新儒家思想史》:
儒学的“复兴梦”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君劢先后拒绝了国共双方的邀请,开始进行全球巡回讲学并计划写作《新儒家思想史》。《新儒家思想史》第一卷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随后他又很快完成并出版了第二卷。之所以要写这部著作,一是为了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偏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机蓬勃的有机生命体,而不是陈列在文化博物馆中的古董;二是为了阐明复兴儒家的思想依据,即通过“理性自主”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新生开辟道路。
《新儒家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自唐代开始,经由宋以迄于清末的思想趋向”。在张君劢眼中,宋儒强调的“格物致知”、心思体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区别等观念是古今思想的共同基础。因而,儒学的复兴主要就是宋明儒学的复兴。
“万物之有”与“致知之心”乃是新儒学的基本范畴,这两大范畴虽然“缺乏西方之严格方法”,但是却没有西方哲学割裂心物、偏执一端的弊病。张君劢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唯实的唯心主义”,正是为了彰显新儒学在调和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方面的独特优势。
其实仔细来看,所谓调和唯心与唯物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延续了张氏在1920年代对“人生观”问题所作的思考——所谓“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先前在生命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玄学”,如今以一种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收摄凝聚成了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儒学”。与前者相比,后者不仅是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同时也昭示了张君劢力图“打通”中西哲学重造民族文化的雄心。
未曾忘怀“政治”的“学术”
1958年元旦,张君劢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肯定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宋儒的重要意义,力图在沟通“心性之学”与西方现代启蒙哲学(康德、黑格尔)的基础上造就新的道德主体、认识主体和政治主体。
从这份《宣言》的文本来看,“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可以截然分离的——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在这里并不适用。虽然张君劢在晚年极力强调学术的“自主王国”,然而,仔细思考张君劢思想背后的深层动机,我们会发现,“学术”与“政治”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并且两者在相互缠绕和碰撞中共同塑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形态。
早在师从奥依肯攻读哲学期间,张君劢就一边观察欧洲的政法状况,一边在思考哲学问题。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国民缺乏一种互谅互让和衷共济的精神,故此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仍然不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制。
因此为了建构一种理想的政治,首先应该造就一种理想的国民精神和国民道德。此时的张君劢已经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学术与自己的生命结合在了一起:为了建立恃理不恃力的“理性政治”,必须要培养有智识有道德自由的个体公民,而以“修身”“尽性”为基础的新儒学恰好正可以作为这一政治目标的哲学基础。
张君劢曾说自己“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或许张君劢建设“学问国”的深层动力实际上正是来自于对理想的“政治国”的渴求。甚至在他晚年极力提倡“学术之独立王国”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强调本身所蕴含的某种“政治抵抗”的味道。
更何况,对于张君劢这样一位“立身则志在儒行,论政则期于民主”(唐君毅语)的学者而言,“政治关怀”本身就是其“学术价值”的一个维度,强行将“政治”从“学术”之中剥离反而容易造成对历史和学术的扭曲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