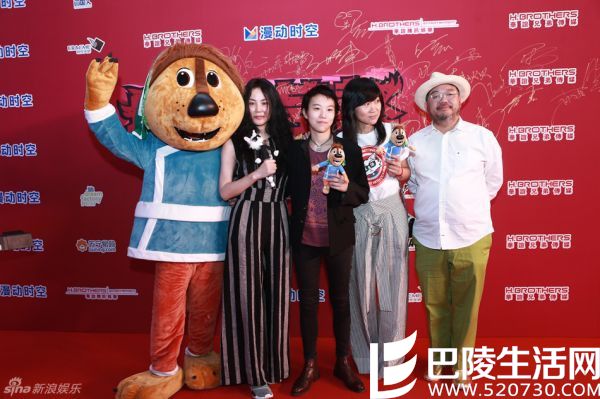姜昕打过王菲 姜昕:她们打听到 窦儿是和王菲一起出去的
经过那些变化,我和窦唯的感情似乎稳定起来,两个人好象都一下子长大了不少,懂得了谦让,也很少再会为小事闹得面红耳赤。因为H乐队演出越来越多,窦唯经常要离开北京,在一起的时间少了,相聚的日子就显得分外美好。每次他去外地,两个人多少都有点儿依依不舍,我总是嫌时间过得太慢,希望快点儿到他回来的日子;一到他要回来的那天,脸上不知怎麽的,总是忍不住的要微笑,那种思念,是甜蜜的。

我越来越爱那个“家”了,那虽然只是两间普通的平房,洗澡要去公共浴池,用水要到院子里,而且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空间也才只有六七平米,可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儿更温暖的地方吗?
我们谈到了结婚,可是我们还没到登记的年龄,于是,在一个小窗前洒满月光的晚上,他对我说:让那些世俗的狗屁规矩见鬼去吧!就让我们把此时当做我们的婚礼,有月亮为证,月光下他年轻的脸上一片虔诚,目光是那样的熠熠闪亮,“你愿意吗?”他轻轻的问,我一连串的点头,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一千个愿意,一万个愿意!

那个春天的夜晚,月光如水般顷洒,风从敞开的窗吹进来,轻轻撩动格子布窗帘,一切都美好得恍如梦境,而我们,就在那如梦如幻的星空下幻想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家,我们甚至给未来的孩子都想好了名字。
第二天,窦唯一本正经的把我们“天真”的“婚礼”告诉了他妈妈,她听了忍不住笑了,就半开玩笑的说:那先叫“妈”吧!可我怎麽也鼓不起勇气,叫不出来,可是,她却上心了,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真的开始留心起家俱什麽的了,还总是问我喜欢这样还是那样,弄得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这有什麽不好意思的?人这一辈子都得有这麽一回,早办了早踏实,我也算早了了一份儿心了!
”,“明年你们就够年龄了,我看,就干脆趁早儿办了吧!省得拖着让人说嫌话,这胡同儿里人多嘴杂的”,“咱们虽然是普通人家,可也得样样都给你们换成新的,不管好赖,是我这个当妈的一份儿心意,你可别计较,等将来你们自己有条件了,再换更好的,”,“听我的,早点儿做准备错不了!
”
于是,地板砖换了,沙发柜子也选好了式样,开始托人打做了,我也真的就把自己当成个小媳妇了;而昔日的那些梦想,似乎早已走远了。那时候我想,人生的满足,大概也不过如此吧,我还要奢望什麽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她。
其实他们早就认识,只是那时候,大家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情感,互不相干罢了。关于她,我只知道她早已离开北京,偶尔会飞回来看她的男友,在一些Party上也见过她几面,仅此而已。
黑豹乐队去了一次她在的地方演出,回来后听说她和她的男友分手了。但这当然和我没有什麽关系。
然后,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邮差送来一张包裹提取单,发件人处写的竟是王菲。这让我觉得多少有点儿意外,因为在这之前她和窦唯好象从来都没有过什麽联系。那一段儿我和窦唯一直很好,所以我也就没太多想。只是有点儿奇怪,她会有什麽东西要寄给他呢?等窦唯回来后,我把单子交给他,他去邮局取回了东西,是一箱CD唱片和一顶很漂亮的线帽,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信。
窦唯把信拆开来看了,然后很大方的顺手塞给了我:“没吃醋吧?”,他笑着探过头来观察了一下我的表情,发现我多少有点儿不太自然(是想表现得若无其事来着,可那麽一大箱原装CD,又从那麽远的地方寄来,大概要花不少钱吧。
普通朋友会那麽大方?我怎麽能完全做到视若无睹呢?),“别小心眼儿,噢?”窦唯把那顶线帽给我戴上:“这个给你还不行吗?去照照,好看死了!”,他吻了一下我的脸颊,又做了个他拿手的鬼脸儿,就兴致勃勃的跑去拆那些CD了。
我看了那封信,虽然他让我无话可说,可好奇心还是让我不能不看:那是两张淡蓝色的信笺(要是我,大概也会选择这样的颜色吧),字迹干净整洁,无非是写了一些最近心情不好的话,只是在最后,她说:你以后可不可以别再叫我小王?
日子一天天过了,街上又飘起了落叶,冬天眼看就要到了。她又来过几封信,依旧是淡蓝色的信笺,窦唯也依旧每次看完都塞给我,那些信,也依旧是说些最近在忙什麽,心情又怎样,窦唯有时候也回信,他总是写的很短,说不知道该说些什麽,自己也不太善于写信,总而言之,希望她快乐!那些信的开头,他依然称呼她:小王。而我,也就渐渐相信,那只是一份友谊。
那年冬天,窦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黑豹乐队。那实在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那时候黑豹乐队正如日天,出场费也越来越高,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也没有人能理解谁会在这种时候离开。大家都在劝他改变主意,我也一样,可我后来明白了,因为,他找到了新的方向——而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PeterMurphy的两张唱片:Bahaus和DeepOcean……
“这才是我想做的音乐!可我不想勉强别人,所以,只有离开!”,“我不想做什麽被歌迷捧得晕头转向的明星,到哪儿屁股后边儿都追着一帮傻尖傻尖的果儿,再说,那你还不掉醋缸里?”(尖是漂亮的意思,果儿是女孩儿,这是摇滚圈里的“行话”)他笑了笑,又严肃起来:“我需要冷静,你能理解吗?”这样的原因我当然能接受,可是,回头想来,才真正意识到当年的他能做到这一点真是可贵!
那次去海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黑豹乐队的演出,然后,他剪掉了长发,离开了。
新的乐队很快就组起来了,乐队成员有一个公同特点,就是都没有了长头发,可是他们的那些短发,却个个理得别出新裁,走在大街上,一样保准会有百分之二百的回头率——在当时,这可在摇滚圈儿这麽“前卫”的地方也都算新“形象”了。
他给它起了名字叫作梦,一切又开始从头做起,没有唱片公司的宣传操作,没有条件完备的排练场,没有演出收入,可是,我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对他们的音乐充满了信心。那一段儿他们真是“团结”,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泡在一起(以前在黑豹乐队的时候好象也没这麽“亲”过),所有人都憋着一骨劲儿:要让大家“惊讶”!
而每天一起床和队友通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在电话里互称起“Peter!”,“Murphy!”来。
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排练和“磨合”,作梦乐队渐渐确定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有了一些比较满意的作品。春天再来的时候,他们决定开始参加Party。清楚的记得那一天,那天晚上的那个Party是梦乐队自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开”亮相(在这之前他们的排练一直是“谢绝参观”的),虽然晚上到场的绝大部分仍将是圈内人,而且很多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加“战友”,可是对于一支“新”乐队来说,“第一次”无疑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刚吃过午饭,乐队的全体成员就“披挂整齐”的陆续到窦唯家集合了。那天的他们就象一支既将出征的年轻的球队,对于当晚的“首战”个个都显得十分兴奋,七嘴八舌的讨论着晚上的“战术”和“策略”。虽然是“新”乐队,可乐队成员却也几乎都算是在摇滚圈儿里摸爬滚打的“够资格”的“老”战士了,按说一次Party并不在话下,可是,要知道,那天晚上他们既将以“崭新”的形象登场,而且,既将带给大家更新的音乐:没有甩动的长发,没有“嘶吼”“奔跑”和狂野煽情的Solo,取而代之的是奇特的短发,更怪异的装束和“冷静的站立走动”。
他们甚至化了妆:黑色眼影和黑色唇彩。
这一切,大家会怎么看待呢?在男人留长发尚不被普遍接受的当时的中国,作梦乐队的这种种种种无疑既使是在“圈儿里”也绝对算是新鲜事儿了吧?——那种感觉大概既象是一次“冒险”又象是一场“挑战”,反正在我逐个的给他们化上他们要求的那种“恐怖妆”的时候,每个轮到的人都会在一瞬间忽然神情“郑重”起来(虽然在那之前或之后他们一直都在为彼此的“新形象”相互取笑逗闹)——“特异独行”大概永远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最想成为也最“敢”做到的,但是,重要的是,那绝对不是没有内容的为怪而怪,如果你看到了他们那时候的演出,你会明白,那些是混然一体的,那是他和他们那时候的心情,那是他们对生活的另一种“热爱”。
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他们就出发了(我至今无法想象那天的路人看到他们会是怎样的一幅表情)。临走的时候,窦唯还再三叮嘱我晚上一定要尽早赶到(因为晚上我自己也要演出),他说他会尽量把乐队的演出顺序往后调,争取等我到了再演,“你一定要看这场演出!”,“唉,对了,顺便儿帮我‘侦察’着点儿,看看有什么问题,大家又有什么反映。”
可是,那天晚上我没看到那场演出。
当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演完了,台上是别的乐队。对于Party来说那时候时间并不算晚,演出也只进行了一小半儿,怎么没等我呢,不是说好了的吗?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人很多,台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我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的寻找窦唯,可是,哪儿都没有他。
好不容易在吧台边儿找到了作梦乐队的另外几个成员,他们口径一致的转告我:他去外边儿“飞”点儿(吸大麻),一会儿就回来。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他“飞”(而且他跟我说过他挺反对这个的),我有点儿不信,也有点儿担心:“那你们怎么没去?(我不信要是这种活动他们会不在一起)他跟谁去的?带我去找他!
”,“你急什么呀?他一会儿就回来,真的!来,坐这儿,喝什么?”他们之中唯一一个坐在一张吧椅上的被另几个从椅子上拽下来(那几个本来正围绕着那把椅子在周围的吧台边儿靠着)。
“我不坐。带我去找他!”,“哎呀,你就踏踏实实等会儿呗,他又丢不了,不至于的吧?”,“那我自己去!他在哪儿?”,“还找什么呀?腿长在他身上,这会儿不定‘躲’哪儿去了呢!反正一会儿不就回来了吗?”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BB机,约好了的事情如果临时有变,他从来都会及时通知我的。
怎么出去也不打个招呼呢?吧台上就有电话,打电话留个言是很方便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也许演出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心情不好。
可是他们告诉我说:演得棒极了!从他们脸上的神情我看得出演出肯定没问题,可是我却隐约觉得那里边有隐情——因为他们看到我之后表现出的那股“热情周到”的劲儿有点儿“戏过”了——大家都那么熟了,谁还不知道谁呀?可从来没见他们那么“绅士”过,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有一种说不清的什么开始上漾,我知道那是那种叫做“预感”的东西,虽然我抓不住它,也不知道它到底预示着什么,可是就是觉得有事儿(而且肯定跟“飞”无关,但又不想让我知道)……很想赶快见到他,可是他们都一口咬定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大概就在附近吧!
”,“不会走远的!”;在关于跟谁出去的这一点上他们也含糊其词:“一帮人呢!
”,“没看清!”,“没注意!”(倒都挺够哥们儿的),我明白再问也没用(跟我比起来他们当然更属于“一个组织的”了),又没办法找他(窦唯的BB机在离开黑豹乐队的时候上交回公司了,其实可以不交的,但他说他有点开始讨厌那玩艺儿了,老是不分时间地点的叫),没办法,我也只能安下心来等(但愿他们说的是真的)。
一支乐队演完了,另一支乐队上去了,又有一支乐队上台了(我只看见了这些),还是不见他的人影儿。那大概是我参加过的最魂不守舍的一次Party,我站在喧闹的人群里,既没看进去演出,也没心思和别人“神侃”(更别说跳舞了)。
我只是不停的重复两个动作:四处张望和时不时的拿出BB机看一下(生怕错过任何一种“找到他”的可能性)。当一支乐队站到台上说:“我们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支乐队”时,我抬手看了看表,已经快夜里两点钟了,我沉不住气了:虽然对我们这些“夜猫子”来说夜里两点钟还在外面“折腾”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但是自己的男朋友到这钟点儿了还既不见人又没有任何消息(而且也没打招呼),这多少都有点儿不正常吧?我自然而然的开始想到那也许又是那类事情(否则又有什么事情需要这样“神神秘秘”的呢?),可是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这种预感(虽然它已经十分“强烈”了)。
怎么可能又那样呢?!我甚至都有点儿后悔了:晚上为什么不请假呢?!可是,那大概是跟我请不请假无关的吧?
再去找那几个家伙,早不知溜哪儿去了,跟我一起来的两个要好的女朋友帮我想了一个主意:由她们出面去问问其它的熟人——而且得是那种既便真有什么窦唯也不会去设防的人(不会想到你会去问的人),“至少应该会有人看见他是跟谁一起出去的。”,“你别去,在这儿等着。万一人家看见你觉得不好说呢?” 她们果真打听到了:他是和王菲一起出去的。她那天下午飞回了北京,而且来了Party。
说实话那个消息让我的思维在一瞬间"突停"了,一时间我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怎么会是她?她不是在香港吗?噢,对了,人是可以坐飞机的,想去哪儿都很容易也很快的,她是可以飞过来的。可为什么偏偏是今天呢?难道是专门为了看他新乐队的第一场演出?否则又为什么不看后边的演出而早早的就走了呢?那么,是他提前通知过她今天的演出喽?那也应该没什么了不起的呀,他下午走的时候不是还再三叮嘱过我晚上一定要早点儿赶到吗?可他为什么又和她一起离开了呢?又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而且明明知道我要来的,那些淡蓝色的信笺开始在我眼前飞来飞去,让我觉得有点儿晕眩,他不是说她只是他远方的一个朋友而已吗?那么和她出去又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难道,他在骗我?!可那又为什么要一直都给我看那些信呢?"怎么办?!","你倒赶紧想办法呀?发什么愣呀?!",两个"热心"的女朋友把我从那一连串的"?中拉了回来,后来的我慢慢学会了不再去干那种"完全出自生理反应"的冲动的"傻事儿",碰到类似的"事变"也已经尽可以表现得"不动声色",可那时候,我还没学过"冷静",我只觉得血往上涌,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那一刻里我只想到一个念头:找到他!
哪怕"翻遍"整个北京,我要见到他——就在今晚!
我要问他:为什么?可是,诺大个北京,从哪儿找起呢?说来奇怪,真不明白那一刻脑子里怎么就忽然"灵光一现"(让恋爱中的女人去破案肯定一破一个准儿),我几乎一下就想到了她在一封信中说过北京的酒店她最喜欢XXXX。她一定住那儿了!那么,他也许是跟她去那儿了?
冲到吧台边儿,打114查到了那家酒店的总机,然后把电话打到前台,居然真被我猜到了——她果真住在那儿!我放下电话,不管不顾的就往外冲,两个女朋友拽也拽不住:"干吗呀你?!","这样去不好吧?万一他要不在呢?!
","他肯定在!",直觉告诉我他在那儿(既使不在我也一定要去弄个明白),"那你也别就这么冲过去呀!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咱们再一块儿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好想的!我不管!我要去找他!","你们别管我!"拖拖拽拽的来到大街上,正好碰到一辆出租车,她们一把没拽住,我飞快的跑过去跳上了车。
我找到了他,而且是在她房间的洗手间里,他显然刚洗过澡,我注意到他的头发是湿的(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其实在那之前我到更宁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只是空跑了一趟而已),在"突然"看到对方(在不该看到的时间地点)所表现出的一瞬间的惊愕和不知所措之后,我们陷入了"漫长"的对视(当然那其实顶多只不过几分钟而已,那是记忆中的"错觉"),就那么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通过镜子直视着彼此的眼睛,我忽然间忘记了所有的疑问,而且一时间根本就无法开口说话(只是听见自己的心跳快得不得了,声音也清晰得有点儿夸张——我甚至怀疑他能听见);
而他也一言不发,就那么定定的看着我,他的目光让我觉得游离和冷,然后,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酒店保安也随后赶到了——这儿我得交待一下:那天我一进大堂的时候他们曾让我出示所去房间的钥匙牌儿(口气极其令人生厌),我没理他们(哪儿有功夫理他们呀!
)就径直上了电梯,没想到这些人对工作倒还挺"尽职"的——在他们和警察眼里,夜间"出没"的年轻女孩儿本来就没什么好东西,更何况半夜三更往酒店里跑——因为职责是抓坏人就怀疑所有人甚至总是一上来就用一种对待坏人的眼光和口气来对待人民这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存在的问题。
当然那天他们一进房间就发现那只是一桩"民事纠纷",是与他们的"职责"无关的。可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他们以"超过酒店来访时间"为由把我们带到保安部并且"要求"我们"交待"事情经过——三个人分别在三张桌子上,一一发了纸笔,而他们,则象兼考老师一样背着手,"神情严肃"的在其间走来走去——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心和藉以打发那漫长而难捱的夜班儿,她很快就被"批准"回房间了,而我和窦唯则一直到早上五点多钟才被允许离开并且是被"护送"到酒店大门口的。
天快亮了,路灯已经熄灭,街上灰蒙蒙的,大概是个阴天。我们一前一后的走着,相隔越来越远,从来没有过那样一个春天的早上,让我觉得如此惶惑,如此黯淡。我机械的向前走着,不管方向,不能思想,只知道跟着他的背影;他越走越快,后来,忽然就猛跑了起来,他跑得很快,眨眼间拐过一个街角,不见了,我停住了,无比茫然的愣在那儿,看着他消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