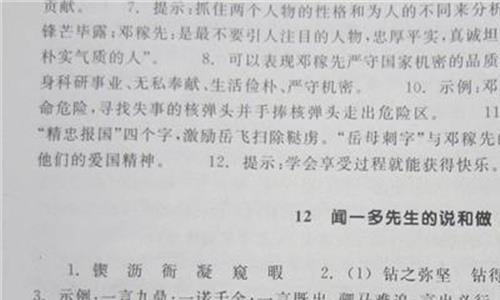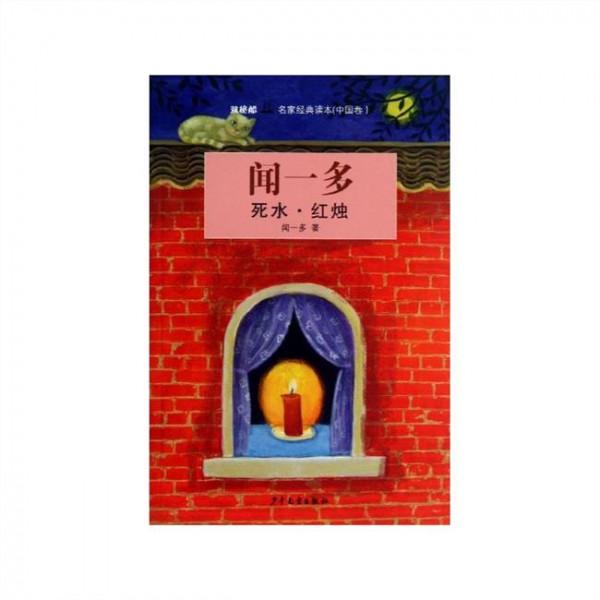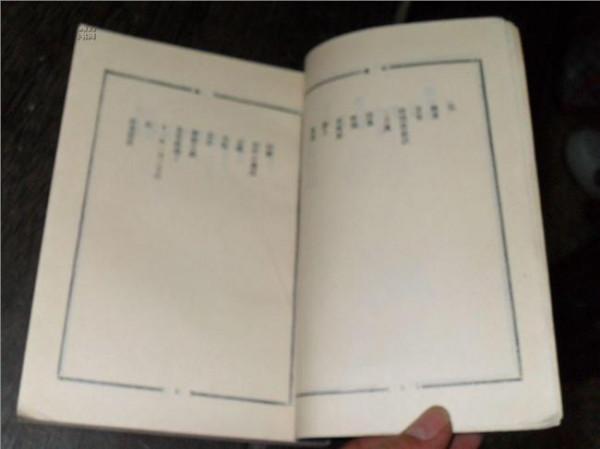闻一多诗集 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及其他
又在网络上找了一遍,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完整的考证著作,只有黄石先生上世纪60年代做过一部《端午礼俗史》,收在对岸一套民俗丛书之内,论证详切,而且有自己的看法。黄石在30年代就是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燕京社会学系”大旗下的重要一员。

读下来,闻一多先生与黄石先生都认为,把端午的源起派在祭屈大夫的头上,实在是一个民俗上的“误会”。闻先生戏称为一个“谎”,那谎的来源,最初是《世说新语》,但最“盛传”的是在南朝梁吴均的那一部《续齐谐记》里,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其实,端午之俗,却是远早于汨罗遗风,非由屈大夫而起也。其中龙舟竞渡与吃粽子两大节目,闻先生发现都与水神即所谓蛟龙有关系。龙舟之上有龙饰,而粽子之以楝叶塞、以五彩丝缚,虽那个“谎”里说是因为蛟龙所惮,但反过来却恰恰说明粽子与龙的渊源,原初应该是把粽子投入水中以娱蛟龙也。那么,这个风俗或最早起于以龙为图腾之族也。
闻先生联想到吴越人“断发文身”的话,因为《说苑》里面有“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的记载。那么,这个文身也便是刺以蛟龙之纹饰,吴越族应是以龙为图腾之族,端午之俗或起于吴越地,渐进而广及于他地。
而黄石先生认端午之俗起于驱瘟神,亦视后世转而以之祭屈子为绝大误会。他说,如果据上述那个续齐谐的“谎”里的说法,东汉时既已知楝叶与五彩丝为蛟龙所惮,那为何离东汉不远的晋,粽子并不如此模样,等过了几代,却反过来想起了东汉人白日见到屈子幽魂所听到的话,又遵行起来了呢?
而且,古来祭屈子的祠堂之类,并不多见,即使在相传屈子投江的汨罗之旁,亦未见古来的屈原庙,湘人亦不于端午祭屈原。黄石先生说,如果角黍确定是专为屈子而设的祭品,龙舟是特为他招魂而来竞渡,那么事物都具备了,何不就在江边祭他一番,或在龙舟上安设牌位致敬呢?但找遍载籍,旷观南北,都极罕见。
特备的角黍,大家只往自己肚子里送而已。只在大冶有送瘟的龙舟,设有三闾大夫像,杂于十数人物中,送到青龙堤焚化,这到底是把三闾大夫算作什么?是鬼是神,是招是逐,是敬是恶呢?主张吊屈原的人士,怎样强辩,也说不出个道理来。
黄石先生证以《夏小正》中“此日(仲夏月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又《礼记》中“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之文,认为“仲夏月的午日,毒气弥漫,宜乘水临风,以泽兰众药入清泉行洁礼,以辟恶去秽。这和后世于午日惶惶然走于郊野,什采百草众药,又争汲‘龙船水’为辟恶治病、解瘟消毒之俗,一线相承,自古至今,一致以五月为恶月,午日为特别可怕的凶日,适相吻合。
以此为端午的滥觞,虽不中不远矣。”由此,再来回看“屈原说”的两大支柱:角黍和竞渡,应该作如此解释:龙舟实际是法船,藉神明或巫师的法力,把五瘟鬼拘捕,划出大海后,一把火烧掉,把瘟鬼或远远放逐,或沉于海底,总之第一要义是送瘟禳灾,维护生命是最高目标。
至于角黍,早黍仲夏月便有收获,尝新荐寝庙,取为郊社之祭,是应时顺理之举。
祭毕散祚,用叶包裹更是方便,所以便有后世“裹粽”这样的方法。此外如以周处《风土记》为说,则是“取阴阳包裹未散之象……所以赞时也”,那在“应天顺时”这个古来礼俗的大原则上,更是完整了。
当然,端午起于辟病禳灾说,并非自黄石先生始。与黄石先生应是同辈、但在民俗学界的影响更大的江绍原先生,早在1926年便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三天发表了一篇长文《端午竞渡本意考》。这或是现代对于端午古俗进行“再思考”的开端之作里,最为人称道、影响也最为广远的一篇。
黄石先生礼俗史里的不少论断,应该也受到了江先生《本意考》的很多启发。江绍原先生在文中说,端午竞渡之事,吴以为与伍子胥有关,越以为起于勾践,楚又另捧出其地的忠臣屈原,其实此俗比这三个人都早,只是后来三地的人都想把这个风俗归到本地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而已。
从《古今图书集成》所引的《武陵竞渡略》中所谓“送标”的说法,可以知道竞渡的前身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于什么人的纪念,而是一种“禳灾”的仪式:“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
”江先生遍引遍述之后,概括起来下判断说:“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龙舟竞渡或者说整个端午礼俗的原意,必须离开了屈原、伍子胥、勾践等去求,才能求得也。
江绍原先生的论文与黄石先生的大著,都是“天才之笔”。用细密的理路、谨严的逻辑和灵动的联想,可以说是把一个自古相传的端午习俗的源头本意给“窥破”了。这种“窥破”本相的翻案文章,当然是让人佩服和惊叹,后世如此厚厚累积起来的密不透风的层层“包裹”,作者能够凭着耐心、细心和灵性,把它们再一层层地抽剥开来,露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始本相”,那一种欣喜和兴奋,不能说是不深切。
不过,正是因为过于欣喜和兴奋,也容易太过于把那个好不容易“露出头来”的原始本相视作“珍宝”,至于那些“剥剩下来”的满地的后世“包裹物”,却往往看不出它们的价值,甚至无意中看作“废弃物”而任其飞逝。
这一点,由我个人看来,像江先生和黄先生这样的大家,也有点不能免。
江先生在文中说:我们既然不都是楚人之后,为什么要特别来替屈原“捧场”?黄先生在书中也说,如果角黍真是吊屈原的祭品,那么拿来馈赠亲友,“岂不是把他们当水鬼一样看待?”这多少都有点说得太重太硬了。
同样是不信端午起于吊屈原的说法,我们回到闻一多先生这里,却发现他说得更温暖一点。他说这是一个“谎”,但这个“谎”里有“真”。下面一大段话,出自他的《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说得实在是好,必须抄录在这里:
吃粽子这风俗真古得很啊!它的起源恐怕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所以有那断发文身的风俗。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
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一切,表面上虽很热闹,骨子里却只是在一副战栗的心情下,吁求着生命的保障。所以从冷眼旁观者看来,实在是很悲的,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一二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不断的暗中摸索,人们稍稍学会些控制自然的有效方法,自己也渐渐有点自信心,……但是,莫忙乐观!刚刚对于克服自然有点把握,人又发现了第二个仇敌——他自己。以前人的困难是怎样求生,现在生大概不成问题,问题在怎样生得光荣。
光荣感是个良心问题,然而要晓得良心是随罪恶而生的。时代一入战国,人们造下的罪孽想是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担负不起,于是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于是屈原便投了汨罗!是呀,仅仅求生的时代早过去了,端午这节日也早失去了意义。从越国到今天,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
但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只要端午无限地延续下去,这个“真”就也会无限地“保真”下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