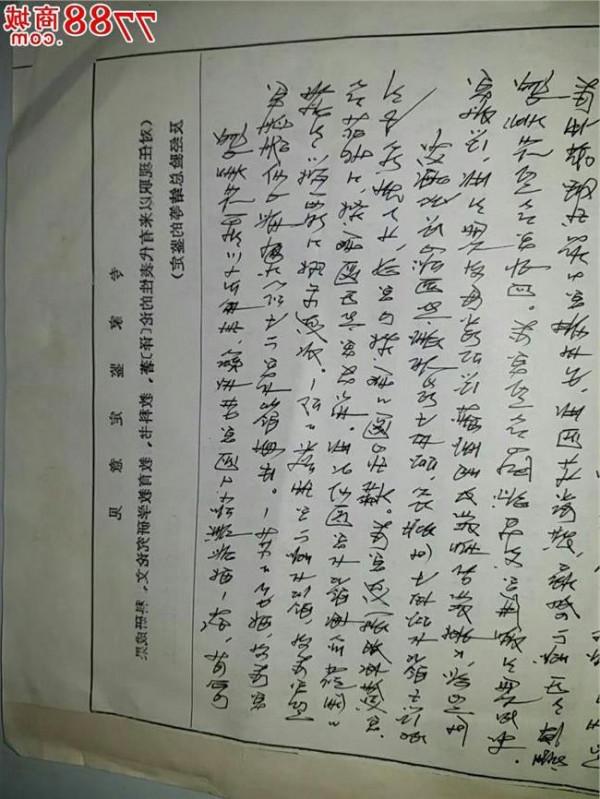周信芳前妻子女 周英华:我和父亲周信芳
围绕着周英华的话题太多了:他有一代名伶的父亲和出身富豪名媛的母亲,他的姐姐、好莱坞华裔明星周采芹,他的前妻、80年代世界顶级超模周天娜,他耀眼的艺术家朋友安迪·沃霍尔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个展览中呈现出来,或多或少。

周英华
回归画室的社交名流
有“纽约餐饮巨子、收藏家和社交名流”多重标签的周英华今年已经76岁了,但老先生依旧保持对时尚品位的绝对自信。上午从纽约飞来北京,下午便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他穿一件黄色休闲西装、旧牛仔裤,上面滴落斑驳颜料,很像是抽象表现大师波洛克的手笔。他说自己经常这个样子,从画室出来就一身颜料地去了社交场合。

看得出,他喜欢保留这些绘画的印迹。从2012年开始,周英华便尝试回归到另一个身份:画家。在放弃职业生涯50年后,他重新拿起画笔。2015年1月下旬,他在中国的第一次个人绘画和收藏展“麒派画家周英华”将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展览的名字表明了他另一个身份:麒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子。2015年1月14日是周信芳120周年诞辰,这个画展算是他对父亲的纪念。

将周英华重新带回绘画的人是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前馆长杰弗瑞·戴齐(Jeffrey Deitch)。2012年初,戴齐想和周英华合作一个有关他在建筑、设计、演艺及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的对谈,他上门拜访,结果在周家的厨房里,被一张尺幅不大的泼色画吸引了。当得知周英华学过绘画并曾是职业画家,作为经验极其丰富的策展人,戴齐开始鼓动他重返画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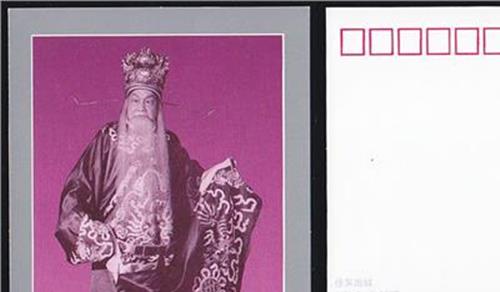
那时周英华已经73岁。他的创作将必须从他上世纪60年代在伦敦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是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他建了画室,但没有找助手,泼色、燃烧、撕扯、刮削、溶化、翻转、滴色,甚至爬楼梯、钉钉子,这些工作都是独力完成。他还像年轻时一样热爱西班牙艺术大师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那一代,他们使用各种物质材料绘画的方式在他眼里仍旧魄力惊人。
周英华画作:《四季(春)》(2013~2014)
经过首个系列的高强度创作之后,他将画面构图打开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结构方式和中国书法的优雅开始融入他的西画创作。“我也许没法跟那些老艺术家的创作抗衡,但我的绘画能达到这个展览里的大多数艺术家的水准,甚至超越他们。”在参观了洛杉矶MOCA一个当代艺术展后,周英华这样告诉戴齐。
在刚开始恢复创作的时候,很多朋友建议他画画用中文名,从而将他的绘画与他作为MR.CHOW的名人身份区分开来。但他作为餐厅主人、建筑设计师和富有远见的收藏家的成就反而促成了他在绘画方面的突破,而并非彼此冲突。和其他艺术家相比,周英华的绘画不仅表现了他强大的艺术直觉,同时也在画他难以复制的人生。
周信芳戏装签名照
献给父亲的绘画
父亲留存在周英华眼里的样子,每次他想起来都是同一个画面:父亲在舞台上踏着锣鼓点疾走圆场,突然立住,绕袖,亮相。那一站一亮,风采摄人,他虽只是一个小孩子也终不能忘。
在绘画中,周英华也想去捕捉这样一个亮相——“只有几秒钟,但蕴含了一切。”这大约就是他在展览英文名字中所期待企及的:The Voice For My Father(致我的父亲)。
周信芳和夫人裘丽琳育有四女二子,依次是周采藻、周采蕴、周采芹、周菊傲(艺名周少麟)、周英华和周采茨。他们一家人在20世纪离散聚合的命运,早已成为一部大时代背景下的家族传奇。
周英华和家人合影。左起:周少麟、周采藻、周英华、周信芳、周采芹、周采蕴
1947年,裘丽琳把大女儿周采藻送到美国留学,其余几个子女,除长子周少麟,也都在50年代初期相继被她送出大陆:二女儿采蕴和小女儿采茨去了香港,三女儿采芹和小儿子英华在英国伦敦。1961年,裘丽琳曾设法独自从香港出境到英国探望过几个孩子,这也是周英华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周英华和我们聊起来,他初到伦敦的记忆是充满失落和痛苦。1951年,他被母亲送到英国一所公立寄宿学校时只有12岁,比前面出去的几个姐姐都要小很多。寄人篱下,承受种族歧视,这是上海长乐路788号那幢洋房里一个富家幺儿从未想象过的生活,让他感到绝望和惊讶。
“一切熟悉和喜爱的事物都消失了。忽然间我非常空虚,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中学毕业后,他进艺术院校学了一年绘画,之后又读了两年建筑。自从离开中国,他就没收到过父母的只字家信,被彻底割裂在世界另一端,这样生活了10年。
周英华跟我描述当时的处境:“我奉为真理的两件事都不复存在:父亲的地位从巨星变成不为人知;我的祖国和文化处境更糟糕。周围的人都普遍认为我们是最最卑微的,来自某个早已没落的异域国度。这并不正确,也不公正。我为此十分心碎。”
但他并不向人表露这种痛苦,就像周采芹在自传《上海的女儿》中所记述的,弟弟英华“从来不让伤感外露”。直到1961年母亲来伦敦探望他们那一次,他在周采芹面前暴露了心碎。周采芹写到这个场景:他们姐弟开车去接母亲,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英华突然用手蒙着脸,喃喃地说:“妈妈,为什么非要让我那么小就离开你?”
那年他22岁,在伦敦画着画,靠在餐馆打工养活自己。周英华说,他始终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让年幼的子女一个个离开她。但周家最小的女儿、他的妹妹周采茨想明白了,她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因为姆妈一直觉得会有一场很大的浩劫等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家庭,她没有办法。她毕竟是纷繁复杂的旧社会里的过来人,人性她还是很清楚的。所以,无论如何,她作为一个母亲,考虑到子女的前途不能吃苦,做出了送我们出去的选择。”
他们的母亲,过去上海滩裘天宝银楼的三小姐、不惜以私奔来追求一代名伶的显赫名媛,确实不幸猜中了家庭的命运:1968年,裘丽琳在周信芳蒙冤入狱后去世;1975年,周信芳出狱后病逝。
周英华在1951年告别父亲后再未见过他。其实,即便是在上海度过的那12年,周英华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不多。以后每当有人和他谈论父亲,他总是一遍遍回忆离家前的最后两个星期,父亲带他去看戏、吃大餐,那是他和父亲朝夕相处的唯一记忆。
但周英华始终相信,他一生的创造力和执著心都来自父亲。周信芳7岁登台,15岁成名,30岁不到成麒派宗师,天才之外,都因不肯循旧。他喜欢时代的各种新鲜风气,所以将自己主持的剧团取名为“移风社”。20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先后和京剧改良派汪笑侬、欧阳予倩合作,排演了《黛玉葬花》、《王莽篡位》和《潘金莲》等新派大戏。
他创唱大嗓小生,在当时是悖逆于传统的方法,却因此而为戏迷倾心。周信芳还参与戏曲电影实验,1920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选中拍摄京剧《琵琶记》,在其中扮蔡伯喈。
同一时期,梅兰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的是《天女散花》和《春香闹学》。周信芳酷爱看电影,他曾告诉自己的女婿,在麒派代表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中,他为萧何见到韩信题诗的段落加了一段戏本里没有的肩背动作,就是从美国电影明星约翰·巴里摩亚那里学来的。因为性情的这种执著和热烈,周信芳的麒派表演艺术经常被人形容为“浓墨重彩”。
在周英华看来,美术、诗歌、音乐、绘画,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共通的,他父亲的麒派表演也是从这些艺术形式内部衍生出来的一种,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再从戏剧转化到绘画中去,“这也是我可以期许自己成为‘麒派画家’的一个原因”。
安迪·沃霍尔为周英华画的肖像(1984)
“Mr.Chow”:一席不散的艺术宴席
1968年2月,周英华在伦敦“骑士桥”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取名“Mr.Chow”,中文就是“周先生”的意思。名字看似简单,其实费了周英华很多心思。他说,这样一个名字,至少可以让每个人在谈论他的餐馆时都要首先尊称一句“先生”。
少年时代在伦敦的经历,总让他对种族歧视极其敏感又随时充满反抗意识。放弃绘画也有这个原因。60年代初在伦敦,作为职业画家的周英华也曾参加过一些标题诸如“三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或“知名潜力艺术家”的展览。“但那个时候,中国人想要努力在一个仍由欧美主导的艺术史和艺术界争取一席之地实在太艰难了,在西方几乎没有对中国艺术家的支持体系。
”在失望中,周英华觉得当时要想快速跨过东西方文化障碍,他能使用的仅有工具就是餐饮。“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餐厅做得尽善尽美的原因。我成功了,餐厅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把中国介绍给西方。”
那时候的周英华,正在和第一任妻子、60年代英国名模格蕾丝·科丁顿(Grace Coddington)的婚姻中,虽然这段关系只维持了一年,但日后成为Vogue美国版创意总监的格蕾丝无疑为他带来了和时尚圈、社交界千头万绪的关系。
周英华的第二任妻子,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红国际时装界的一代“Icon”周天娜(Tina Chow)。关于她惊人的美貌和前卫的生活方式都流传颇多,周英华在采访中并不愿意过多谈及。
总之,1972年他们在切尔西结婚时,周英华已经是成功商人和社交名流,伦敦时尚圈的人几乎悉数到贺。第二段婚姻在数年分居后正式终结于1989年,周天娜不久后就公开自己是艾滋患者并在两年后因此病去世,令人悲叹的结局加持了她的传奇色彩。1992年,周英华迎娶了现任妻子、韩裔设计师Eva Chow。
不过在1974年,周英华转到美国发展时,他和周天娜仍是璧人一对,并在美国上流社会也迅速成为新贵。周英华将第二家Mr.Chow开在了洛杉矶贝弗利山庄,好莱坞名人纷至沓来,餐馆成为当地时尚标签。1978年,第三家Mr.
Chow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开业,同样迅速复制了伦敦和洛杉矶的成功,成为纽约艺术家和明星们的聚会场所。“约翰·列侬(John Leon)遇刺前一天,在Mr.Chow吃了他最后一顿晚餐。”餐厅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诸如此类与明星相关的报道中。
那里的常客还包括:“波普之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街头涂鸦艺术家凯斯·哈林(Keith Haring),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以及80年代的先锋派画家、后来的著名电影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
这些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周英华绘画过肖像,这批收藏中的大多数画作这次也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
有一种说法,安迪·沃霍尔没出名时,用画作在周英华的餐厅里赊账,这很像是20世纪早期巴黎蒙帕纳斯那些波希米亚艺术家的故事的翻版。实际上,周英华说,那个时候的沃霍尔已经成名,那些画作都是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除了为人熟知的几张肖像,包括沃霍尔为他前妻周天娜创作的丝网画像之外,还有沃霍尔在餐厅即兴画的“汉堡”等作品。
周英华回忆:“我认识沃霍尔的时候,是在80年代早期,已经是他社交活动变得十分频繁之后。在经历枪击事件之前,他是个比较害羞内向的人,但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变得更好交际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来我的餐厅。
我和他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幽默感,比如他也喜欢戴假发,虽然看起来有点滑稽。”周英华说,2016年他的作品将会在纽约的安迪·沃霍尔博物馆展出,“到时候我们肯定会更多地谈论安迪·沃霍尔,整个事情就像一种循环,最终会在安迪·沃霍尔那里结束。”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为周英华画的肖像(1985)
在沃霍尔这个圈子里,周英华最亲近的人却是当时走红纽约艺术圈的年轻黑人涂鸦画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在我们采访中,周英华特地把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表示他与巴斯奎特的亲密程度。“一方面我们都对种族主义很敏感,另一方面我和他像是父子关系。
他觉得我在社交生活方面教会他很多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还一起去过香港,那段时光很快乐。我们也计划去其他地方,但没来得及实现。我很爱他,从朋友那里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很震惊也很惋惜,他的生命真如烟花般绚烂而短暂。
”周英华感叹,那个时期他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在嗑药,巴斯奎特就是因为吸食过量酿成悲剧,而周英华自己因为从小患有严重哮喘,没有沾染药物,得以逃离这股吞噬了无数明星人物的暗流。
“1968年在伦敦的时候,‘披头士’、‘滚石’他们都到我的餐厅聚会,那段时间太棒了;10年之后我到了纽约,类似的情形再度上演,又有安迪·沃霍尔这样一些艺术家来到我的餐厅。这两段时光都令人难忘。”周英华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目睹了社会的和艺术的两个20世纪。
周英华画作:《黑色绘画》(1959)
周英华画作:《无题》(1962)
专访周英华
三联生活周刊:你很早就开始收藏安迪·沃霍尔、巴斯奎特的作品,尽管只是自己的肖像。可以说你是比较偏爱波普和涂鸦艺术吗?
周英华:不是的,艺术就是艺术。20世纪有许多艺术运动,每一种都名噪一时,很难说某一种比另一种好。艺术通常可以反映社会,20世纪社会经历了巨变,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又承受了世界大战的疮痍,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而20世纪的艺术正反映了这一切。所以说,我并不会对某个艺术风格或者运动有偏爱。
三联生活周刊:1968年你和名模格蕾丝·科丁顿结婚的时候,英国报纸对你的描述是一个“留着长发、全伦敦有名的潮人”。你当时在画画吗?生活有多前卫?
周英华:其实那是假发。但我在1956年留过长发,那可是“披头士”他们出现之前的事情。当时我进了艺术院校,艺术生有这种成为另类的“特权”。那种发型很具有对抗性,它是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是我表达自由、反抗和创造的一种方式。
这种反抗和当时的心理状况有关。我小的时候有哮喘病,家里人很宠溺,我也很脆弱敏感。当我被送到伦敦的时候,基本可以说失去了一切,面临着极大的文化冲击,我完全迷失了,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扔到了水里,要么沉下去,要么挣扎着活下来。
在此之前,我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在他那个年代虽然很受欢迎,但社会地位并不高,我母亲有四分之三中国血统、四分之一苏格兰血统,所以我的成长背景本身就有一点离经叛道。当我被送到伦敦之后,所有和过往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重建和中国的联系,和我父亲的“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你到伦敦后,父亲给你写过信吗?
周英华:到国外以后就和父亲没有任何联系了,没有信件,没有听过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他去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母亲有一点点联系,那是因为她去过一次伦敦。
三联生活周刊:你总是回忆离开上海之前和父亲待在一起的两个星期十分宝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几个孩子平时和父亲也缺少亲密相处的时间?家中是严父慈母吗?
周英华:我想说,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不论男女都需要全身心投入,这就意味着你的伴侣和家庭都要排在第二位。在我父母的关系中,我母亲为家庭奉献了一切,而父亲则完全醉心于艺术。我继承了这份专注,在绘画上如此,一生做的每件事都是如此。我周围的人不得不承受这些,包括我的妻子、孩子,他们需要很包容。
作为孩子,我们过去也经历着和父亲的这种疏离,也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爱。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不是慈母,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我很高兴继承了她一部分社交和处理问题的技能。你说得对,我父亲在生活中并不积极,还要担心金钱和生活中的琐事,但一到舞台上他就成了一个超人,他完全自由了,对艺术有很高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有说过希望你们都成为什么样的人吗?做一个画家是他的期待吗?
周英华:小时候没有听他说过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知道他百分之百不想我成为演员,尤其是京剧演员,因为他觉得太苦了,太难了。
成为一个艺术家要经历两种极端,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你要很谦虚虔诚,因为绘画创作是很难的事情,面对这么艰难的事情自然会谦恭;另一方面,你要很自信,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那些说自己很普通的艺术家都只是在谦虚而已,他们心里并不那样想。这样两种极端形成的结果是,你内心里对艺术充满敬畏,但外在表现出来却是充满竞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