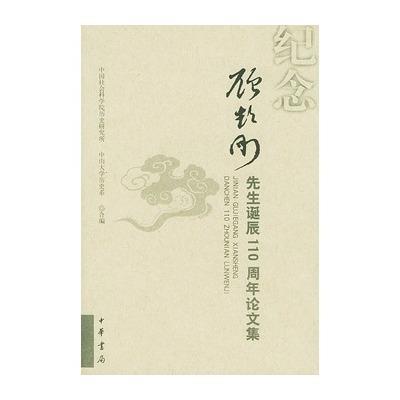顾颉刚是什么学派 论述顾颉刚与古史辨学派【2016年南开大学】
近现代史学虽然思想很新潮,但其方法往往又来自传统,古史辨便是这种思想新潮而方法传统的学派。古史辨运动是配合新史学和新文化运动而展开的学术活动。通过疑古思潮的掀起,颠覆上古的史学体系,通过层累构造古史过程的发现,层层剥离,还原上古历史的真相。正因为古史辨派迎合了新史学的需要,因此它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主流。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1893—1980年),江苏苏州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2年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1926年后,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1929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次年成立禹贡学会。1939年赴四川,在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历任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主编的《古史辨》为其代表作。

1923年5月,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公开信,从而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该信大胆立论、引经据典、观点激进,堪称“古史辨宣言”,引起了史学界众多学者的巨大反响。

钱玄同、胡适、魏建功、容庚、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纷纷表示赞同,而刘脄藜、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等人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卷入讨论的还有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和冯友兰等人。从1926年到1941年,在长达15年时间内,上述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考辨和争论文章被陆续编辑成集,这就是七大册的《古史辨》论丛。

从《古史辨》中收集的顾颉刚的论文可以看出其疑古学术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其一,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只知最古的人是禹,孔子所在的春秋时则增加了尧舜,到战国时又增加了黄帝和神农,到秦朝时更出现了三皇,三皇之上又有庖羲,到汉代时,竟将苗族神话中的盘古搬来作为开天辟地的始祖。
从战国到西汉,在尊古贱今和托古自重心理支配下,一步步地伪造出上古历史谱系,结果形成了历史学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的奇怪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其二,喊出了打破四个旧观念的口号,试图破除古史迷信。顾氏认为,为了恢复正确的中国上古史,必须打破自古以来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其三,提出了古史辨伪的方法。顾颉刚“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的原则,用理清事实和层层考辨方法研究上古史。先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考察某件史事在各个时代的传说情况;研究该件史事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的过程;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顾颉刚关于禹的考证,曾遭鲁迅等人嘲笑。其实,顾颉刚对“禹的演进史”的考证,是根据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综合考辨的结果。他指出,禹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一种有足的大虫,被铸刻在商周九鼎上,古人视为崇拜的神,类似于图腾,逐渐演变为“上帝派下来治水的神”,进而演变成“最古的人王”,到战国时成书的《禹贡》等文献中,终于变成了夏朝的开创者“夏后”,并被整合进了尧舜禹的序列之中。
无论结论是否正确,其方法还是值得重视的。
顾颉刚产生疑古思想原因很多,来源也比较复杂。但直接的原因与其师胡适启蒙有关。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开篇就用《诗经》作时代背景,“丢开唐虞夏商,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顾氏这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
于是便有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书信。同时,他也深受传统的辨伪学的影响,崔述和康有为的辨伪,对他的疑古思想影响最大。顾氏起初并未留意崔述的学术,日本那珂通世对崔述的研究触发了其对崔述的了解。
那珂通世将《崔东壁遗书》标点后印行,顾颉刚也于1921年开始标点《东壁遗书》。顾颉刚还通过钱玄同间接受到兰克学派日本传人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影响。除崔述外,顾颉刚受到常州学派和康有为辨伪思想的影响最大。
他曾标点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时常称赞此书。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也深受启发,自从读了此书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又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
[133]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实际上和康有为的诸子争相伪造更古老的史事来压服他人,时代愈后,所造的古史愈早;时代愈后,所造的人物形象愈加放大之说若相仿佛。
因此,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134]此外,顾颉刚也受到他一向重视的民俗学中故事构成原理的影响,“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135]。
古史辨运动在方法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古书辨常常替代了古史辨,对古史的甄别替换成为对古书的鉴定,而古书的鉴定标准又完全看其成书年代,一旦认定成书年代不符,就遽下结论断定其为伪书,既然是伪书,则所载必是伪史。
这种方法的可靠性仍令人怀疑。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张荫麟就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的历史认识理论,指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
此言一出,古史辨派学者竟无人回应。由于存在这样的缺陷,古史辨运动在40年代之后趋于衰落,顾颉刚也从疑古转为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