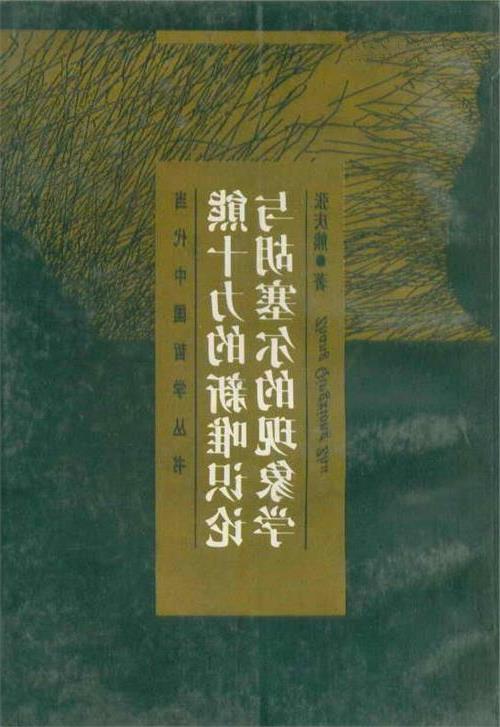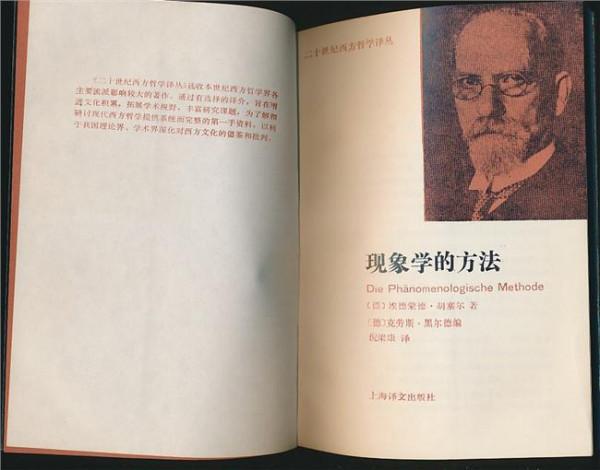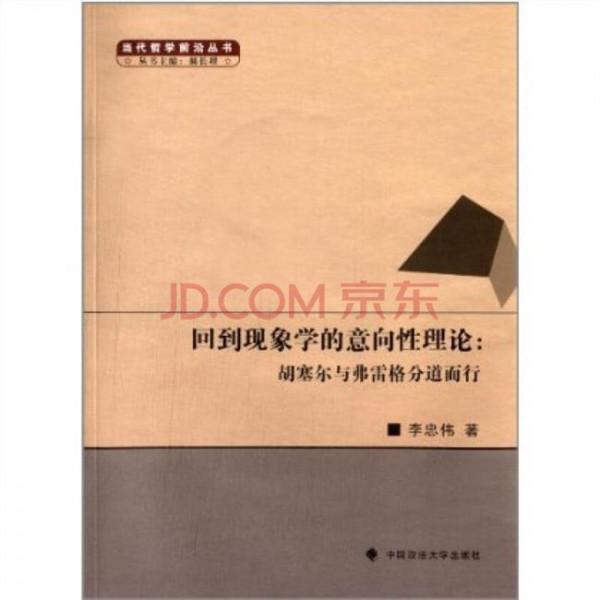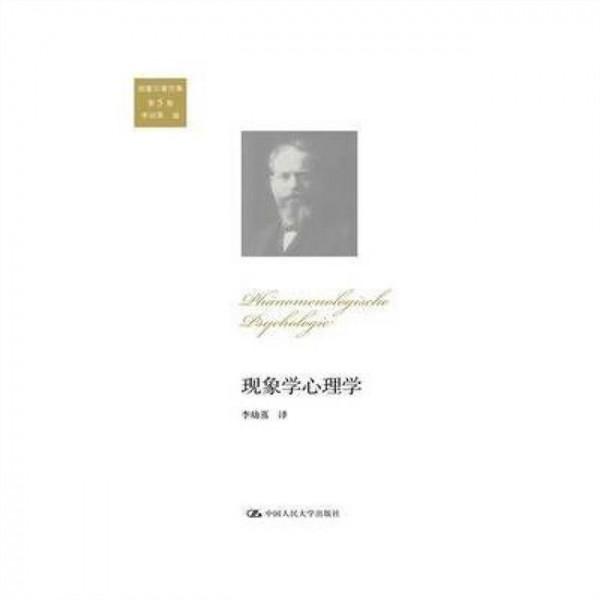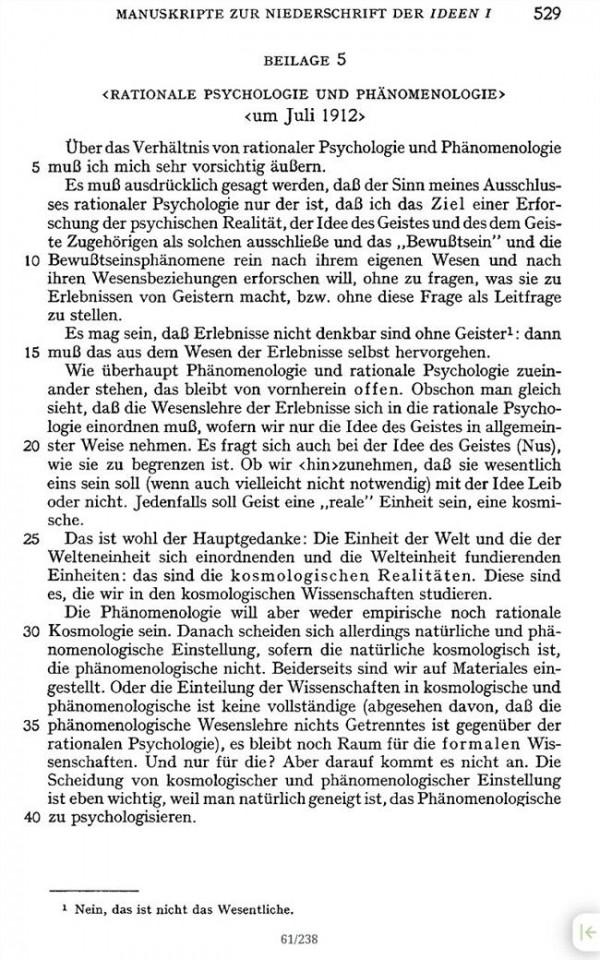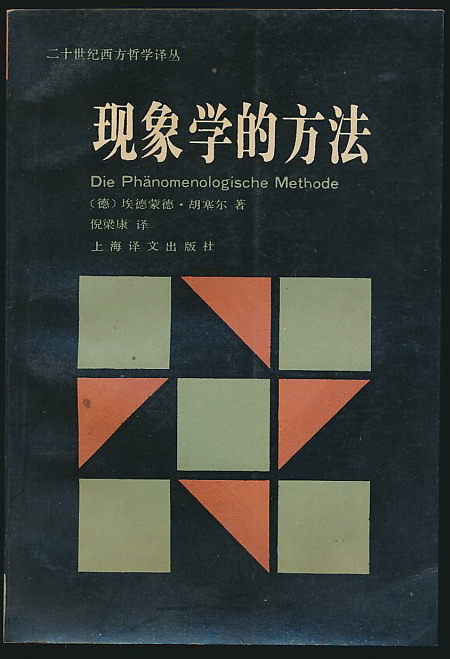胡塞尔的现象学 叶秀山: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对欧洲哲学发展的贡献(一)
本文为叶秀山先生遗稿。在先生去世后,清华大学哲学系宋继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齐研究员对此文作了后期整理。
由古代希腊奠基的“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到黑格尔似乎要画上句号。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现象学”,蕴含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似乎已是一个“大全”;以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如要发展推进,似乎只有把这个“大全”的“概念体系”“打碎一砸碎”,在这个“体系”之内似乎已“无路可走”。
“粉碎”这个“体系”的努力,无一日间断,如叔本华、尼采以及费尔巴哈等,也都卓然成家,影响巨大,而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在欧洲哲学现当代历史发展中持续保持着独特的影响,有其自身的理由。
表面上看,胡塞尔的哲学和黑格尔的体系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譬如都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冠以“现象学”的名称,都很重视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康德、费希特、谢林这样一种传承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努力保持这种历史发展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核心问题也都是自希腊以来的“自身-自己-自由-绝对”,都致力于“在理论上”使这个问题“明晰化”;然而,当我们反复阅读他们的著作时,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哲学”在“精神”甚至“面貌”上却是“各树一帜”、“自立门户”的。
若问他们“哲学”在“精神”上“相异”之点,我们大体上可以说:黑格尔重在“外在”、重在“客观”,而胡塞尔重在“内在”、重在“主观”;就“现象学”言,黑格尔“显现”“在”“外在-外化-客体”,胡塞尔“显现”“在”“内在-内化-主体”。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精神”如何“外化”为“现实历史”的问题,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是“现实历史”如何“内化”为“精神意识”的问题。
以下,我们想就此作一些阐述;不过我们预先要说的是:“外化”是一种“征服世界”的“精神”,黑格尔早年称赞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做的是“王者”的“工作”,用中国传统话语来说,是“内圣”“要-意愿-目的”“开出”“外王”来,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传统则又可以说是在“做”“神”的“工作”,“创造一开创”一个“世界”来;而胡塞尔的工作则是把“世界”“邀请一吸收”到“主体一意识”中来,做一番“超越一纯化”的“工夫”,“做”的是“人”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哲学尽管都叫“精神哲学”,但取向却各自不同,胡塞尔是“人文”,黑格尔则是“神学”,或者叫没有“神”的“神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应归于胡塞尔。只有胡塞尔把“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设定”为“哲学”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人”不是“拥有”“自由”,“人”就“是”“自由”;“人”如果把“自由”当作“外在”“东西”来“拥有”,则就会像黑格尔那样,只能“在”“必然的现实中”“保持一显现”“自由”,而“自由”又受到“限制”,“人”于是只得“在”“客观现实”的“必然”之“流”中“忍受一化解”这个“矛盾”,仍然要“在”“哲学”“思辨概念”中“获得”对“绝对”的“认识一知识”。
“自由-绝对-精神”之“外化”乃是“异化”,“人”“异化”为“物”,“自由”“异化”为“必然”。“马背上的拿破仑”“必须”“付出”“人异化为物”的“代价”。
胡塞尔的哲学工作努力揭示这一“异化”在哲学“超越”上的“不彻底性”,批判一切“向”“自然-客体-必然”“倒退”、“回归”的“自如趋向”,“坚守”着“意识心理-思想-内在”的“自由”之“纯粹性”,为欧洲哲学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
一、胡塞尔与欧洲哲学的历史关系
黑格尔为了讲课,由学生整理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出版。胡塞尔没有那种专门的哲学史著作,但在他的论著中,很多都联系到他自己的学说与历史上各家学说的关系。人们将发现,他和黑格尔各有一部完全“不同”的“欧洲哲学史”,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不仅要参考黑格尔的论述,也要重视胡塞尔的阐述和评介。
扩充开来说,每一个大哲学家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哲学史”。
欧洲的哲学家对于古代希腊哲学的重视,大体是一致的,但重视的角度和内容却可以保持各自的特点。
胡塞尔曾以柏拉图的直接继承者自居,倡导“超越”的“理念”,探讨“自己”的“意义”,而又不断批评这个“现成”的“历史传统”,“超越”“不够”。
然则,“理念”为世间“万物”“自身”,为“万物”之“本原-原本”,一切“事物”皆以“自己”的“本原”为“范本”,皆是各自“原本”之“模本”,这样的“超越”,何言“不够”?
原来胡塞尔心目中之“超越”不是从种种“客观对象”那里“超越”出来,而是一种“无对象-无客体”(雅斯贝尔斯语)的“超越”,不仅“超越”一般的“物理”,而且“超越”一般的“心理”,不仅是“原-物理学”,而且是“原-心理学”——如果把“心理学”作“物理一心理”那种“经验-自然科学”来处理的话。
胡塞尔的“哲学”,不是我们译为“形而上学”的那种“meta-physics ",也不是通常“实验心理学”意义的“psychology”。或许,如果套用“原-物理学”,我们可以把这种“超越”“物理一心理”态度的“内在现象学”,叫作“metapsychology";而胡塞尔专门利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哲学”来阐述他的“先验-内在——主体现象学”。
胡塞尔自认为他这种德国精神固有的“彻底性”“弘扬了”古希腊“理念论”的真正意义。这意味着,在胡塞尔看来,“哲学”不仅要“超越”“关于自然”的“物理学”,而且要“超越”“关于自然”的“心理学”;亦即,胡塞尔的“哲学”要“超越”一切“设定”“自然”为“客观对象”“前提”的“态度”,使“意识-认识”成为完全“独立”的“内在自由”“领域”——一个没有“自然客体”的“域”。
从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由”的“内在”之“域”出发,胡塞尔不仅重视欧洲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外在-客观超越性”的努力,而且重视这个哲学传统中一切“感觉主义”的努力,认为他们在使“意识一认识”“内在化”方面功不可没,只是在“还不够超越”方面存有缺点而已。
于是,与黑格尔相反,胡塞尔给予了近代英国经验主义一感觉主义诸家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把“意识一认识”问题“规定”于“内在”的“感觉印象”,对于保持“主体性”“自由”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的不足之处乃在于:对于“内在”的“心理”仍以“物理”-“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之,使得“客体自然”仍成为“主体意识”的“前提条件”,尽管他们一再宣称,这个“前提条件”是“不言自明”的、“无可怀疑”的。
这就是说,“认识论”以“存在论”为“前提条件”,而在胡塞尔看来,这个从“自然一朴素”的态度“设定”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恰恰是“可疑”的,需要“存疑”的。
从这个意思出发,胡塞尔高度评价由洛克奠定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这个传统把一切“客观超越”的“存在”“归结为”“内在”的“主观”的“意识-感觉、知觉、印象等”,以“感觉-知觉-意识”作为“存在”的“基础”,就欧洲哲学的发展来说,已经把“传统”的“存在论”“转向”了“知识论”,以“感觉经验主义”的“知识论”作为“客观超越”的“存在论”的“基础”。
也就是说,包括“神之本体论证明”在内的“巍峨-高大上”的“存在论-本体论”“大厦”,竟然是“建筑”“在”“感觉经验”种种复杂的“心理”“因素”的“基础”之上的。胡塞尔深刻地“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惊世骇俗”的巨大历史作用,并给予了充分的阐述。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最极端、也是最彻底的意思,在年轻的巴克莱主教的一句“存在即是被感知”中表达了出来。这句备受谴责的话,当有其哲学上的意义,而不可以像狄德罗那样简单地以“发疯”加以“打倒”。
巴克莱的感觉主义,当然具有很明显的“朴素”性,是以一种“朴素”的“知识论”企图代替同样“朴素”的“存在论”。在“哲学”意义上,所谓“朴素”乃是让“哲学”“依靠”“另外”的“条件”,让“哲学”的“工作”也处在一个无尽的“因果”系列之中,而“哲学”原本是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学问”。
古代“存在论”要在“诸因果”系列中“寻求”“第一原因”,找出“众多”的“始基-始祖”来,近代“感觉主义”“知识论”,因“感觉”“需要”“外界”的“刺激”,“感而后动”,找来找去,找到“神之一击”。
于是,“哲学”不以“无限一自由”为“目标-课题-主题”,“哲学”“自己”“消解”“自己”,成为“理念”的“分有者”,而不是“理念”“自身”;“哲学”“跻身”于“诸学科”之中,“越姐代疤”,“哲学”作为“学科”,常常“游移”于“诸学科”之间,乃在于它自身的“不成熟”和“自身”的“朴素性”;而按胡塞尔,正是古代希腊人为欧洲“增加”了一门“学科”—一门“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学科”,只是这门“学科”由“朴素”到“成熟”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胡塞尔自认为他的哲学找到了“成熟”之“路”,他的工作就是为“建立”这门“独立”的“学科”所作出的努力。
英国感觉主义把“意识一认识”问题“收回”到“主体”“自身”来,为“认识论-意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意味着“主体”不仅是“客体”“模本”,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将“认识论”从“本体论-存在论”“统摄”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提出“本体论-存在论”原本应是“建立”在“认识论-知识论-意识论”“基础”之上的,“存在”乃是“知识一理智”的“构成物”。
从这个思路出发,感觉主义-经验主义原本可以超出“‘物理’是‘心理’的‘构成物”’这样一个结论的,但英国的哲学家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结论”,反倒是又“退回”到“朴素”的“物理主义”的道路上来,按照“物理学”的“自然一客观”的“模式”来“建构”刚刚被他们“剥离”出来的“心理学”,仍使“心理学”“附属”于“物理学”的“自然一朴素”的“思路”之中。
由于英国感觉主义这条经验教训,胡塞尔经常提醒哲学家要防止“回归一退回”到“自然一朴素”这种“倾向”。胡塞尔的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他后来提出“欧洲科学的危机”这样的高度上;这个“危机”正是表现在将“心理”“归结一回归”为“自然一物理”这样一种欧洲哲学的“习惯”“倾向”上。
对于这种“倒退”倾向,胡塞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以此审视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批判从任何角度在“科学”上“回归”“自然一客观”的态度,就连被他称誉的欧洲近代哲学“开创者”笛卡尔哲学也不例外。
我们看到,胡塞尔对法国笛卡尔哲学情有独钟,他“追随”笛卡尔作出自己的“沉思”系列演讲,并汇编成为阐述他自己哲学的重要著作;在备赞“我思故我在”这个伟大命题的同时,仍然指出它在“超越”的道路上却步不前,“停止”在不该停止的地方,从而仍然按欧洲哲学的“习惯”,“退回”到“自然一客观”的立场上,是这个“思”“止于”“证明”的“工具”,“证明”“我”之“存在性”,从而使“我”的“意义”被“存在-自然-客体一身体”所“覆盖一笼罩”,从而使笛卡尔整个哲学“陷入”了“身一心”“二元论”。
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原本为克服“怀疑”的“我思故我在”,由于未曾“固守”那个“思”而落入“存在-自然-客体”的“案臼”,也就重新落入这个“可疑的”“自然一客体”之“流”。
我们也许可以体会和发挥胡塞尔的意思说,“思”不仅仅是“我一在”的“证明”、“工具”或“标识”,似乎“我思故我在”仅仅说出了一个“思”的“承担者”,胡塞尔想说的应是进一步的意思:“我”不仅“有一拥有”“思”,不仅仅比起其他“动物一自然”来是多了一种“功能”,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而且要认识到,“我”就是“思”。
“我思故我在”“意味着”“我”“在”“思”中,“我思”,就是“我在”,推演开来说,也就是说“在”“在”“思”中。
就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看来,“思”“使”“在”“在”,“主体”使“自然一客体”“存在”,也就是巴克莱说的“存在即是被感知”,这里的“感知”不是由“客体一对象”“刺激一引起”的“感觉”,“感知”就是“思”,就是“意识一认识”。
按这个思路,胡塞尔之所以没有成为“发疯的钢琴”,乃是因为他只是把“自然一客体”的“科学”“悬搁”起来,而将“哲学”-“科学”的“目标”和“宗旨”转向了“主体”,亦即将“物理学”“视角”“转向”了“心理学”;而这个“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也同样“悬搁”了一切“内在”的“自然一物理”的“问题”“不问”,只“追问”“纯粹一绝对”的“心理”问题。
于是,在胡塞尔看来,经过这样一种“转换”,“可疑的”只是“物理-自然-客体”的“问题”,真正“纯粹”“心理”的“课题”,则是“绝对无疑”的。
二、“怀疑主义”与“悬搁”
胡塞尔哲学之所以不是“发疯的钢琴”,乃是因为他的“怀疑”不是“终极目标”,“先验现象学”的“目标”是“绝对无疑”,而他的“悬搁”也就是把“怀疑”“悬搁”起来,“悬搁”不是“经验上”的“否认”,而是“置而不论”,“终止判断”。
为什么要“悬搁”?“悬搁”被用来“对付”“经验主义”,乃是因为“经验感觉主义”永远是“可疑”的,“感觉经验”里的“世界”是一条“永动”的“流”,只有“截流”,“认识-意识”才有可能把握一个相对“稳定”的“对象”。
“悬搁”是“感觉经验主义”“自身”“必定”要“产生”出来的“认知态度”,是“古已有之”的思路。“悬搁”这个词来自古代希腊,被胡塞尔发扬光大,成为哲学的一种“批判”的武器,把一切“自然”的、“客观”的“科学”“成果”都“悬搁”起来,“括了出去”,“存而不论”,也就是说,对一切“客观-自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都“终止判断”。
于是,“悬搁”并不否定“经验”的“自然科学”“成果”,只是“现象学”“哲学”对这些“成果”不“下判断”,因为它们自己是“未完成”的;现象学哲学有自己的“任务”和“课题”。更进一步说,现象学哲学不仅不“否定”“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而且“欢迎”并且“邀请”这些“未完成”的“成果”作为“意识一思想一知识”的“材料一质料”“进入”“哲学”的“殿堂”,成为这个“思想体系”的“部分”和“内容”。
现象学哲学通过“悬搁”将“物理”的“世界”“邀”进“心理”的“世界”来,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使”一个“变动不居”、“无家可归”的“物理现象”,“在”“心理”的“世界”“存在”。“纯粹”“心理学”“使”“经验物理学(以及由此超越的元物理学)”“存在”。
这样,在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心理”就不可能是一种与“物理”同一层面的“另一类”“物理”,“心理”不允许在“自然-客观-物理”意义上来理解。“自然-客观-物理”的态度,要“经过”“批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悬搁”。
在胡塞尔看来,一切“自然-客观-物理”的学问都设定了一个“外在”的“条件”,都是“有前提”的,而正是这个“前提条件”使得一切“自然科学-客观科学-物理科学”的“成果”都有“可怀疑性”。因为这个“外在”的“目标”只能“渐进一接近”,而没有“达到”的可能性。“自然-客观-物理”的“科学(知识)”永远不得“安身”,它们“永远”“在”“存在”-“不存在”之“间”。
体会胡塞尔的意思,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种“自然科学一客观科学一物理科学”已经是一种“悬搁”的“产物”,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族类”,“原始”并无“科学”可言,“人族”“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中,或许有些“适应一改造”这个“世界”的“技巧”,但并无“科学”可言。
对于这种情形,也许可以说,只有“实践”,而无“理论”;对于“世界”的“理论”态度,当是对于“实践”态度作出“悬搁”的“成果”。胡塞尔把这种原始的“生活世界”叫作“朴素”的“生活世界”,须得经过“悬搁”,以求对“世界”有一个“理论”的“概念式”的“科学”态度。这个态度的建立,是古代希腊人对世界的贡献。
“人族”采取的对于“朴素生活世界”“第一次”—我们姑妄名之—“悬搁”,使我们“拥有”了一种“科学性”-“理论性”-“概念性”的“世界”,亦即一种“思想方式”,从此“有可能-能够(暂时)”“摆脱”“当下实际”的“利害关系”,“从事”一个单纯“理论式”的“观察一思考-研究”。
这种“思想方式”具有“朴素生活态度”所缺少的“普遍性”,“科学理论”应是“不受时空限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从“紧迫”的“当下实际需要”中“解脱”出来,尽管是暂时的,但虽一时“无用”,长远来看,却有“大用”。
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人族”这个“第一次”“悬搁”,也是“第一次”“解放”,“第一次”“自由”。
然而,这个“第一次”“解放一自由”在胡塞尔看来仍是“不彻底”的,这种从“朴素生活世界”“脱颖而出”的“科学”态度,仍然带有“原始的”“朴素性”,是一种“自然一客观一物理”的“科学”态度。这个“科学态度”是“有前提一有条件”的,即这种态度首先“设定”了一个“独立”“外在”的“对象一客体”,“科学”的工作只是有可能“无限”地“接近”这个“预设”的“对象”,而“科学”“自身”永远得不到“确定性”,也就是说,“科学”是永远要“被质疑”的,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拒绝”“怀疑论”的“袭击”。
“科学”的“进步”“依靠”着一种“怀疑”的精神。
为求得“科学”“自身”的“确定”的“信心”,人类的理性除了像笛卡尔那样以“无限性”“概念”“请出-邀请”一个“神”来“平息-弥平”“怀疑”,而胡塞尔提出对这个“自然-朴素-客观-物理”的态度“再一次”地“悬搁”,来一个“二次革命”,通过这次“悬搁-革命”,“剩下”的就是真正意义上“无可怀疑”的“哲学”,而这个工作是古代希腊哲人们“想做”而没有“做好-做成”的。
胡塞尔认为“二次革命(悬搁)”是他提出的“先验现象学”完成的,他的工作使“哲学”由“元一物理学”发展成为“元-心理学”,也就是说,“哲学”的“革命”第一次发生在“物理学”方面,“超越物理学”、“超越自然科学”,使“哲学”成为“理性-理念-思想-精神-主体”的问题。
但逐渐地,尤其在欧洲近代,这个“主体-思想-理性-精神”又以“自然-物理科学”的“模式”来进行工作,使“心理学”习惯性地“退回”到“自然-物理-客体”科学的道路上,使得在洛克-笛卡尔哲学刚刚“露头”的“变革”又“回到”“自然一客观”科学的道路上,使这个“变革-革命”“半途而废”。
胡塞尔的工作是要继续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弘扬他自己说的“德国精神”的“彻底性”,使“心理学”“纯净化”,不仅从“朴素”的“自然生活”中“超越”出来,而且要从“自然-物理-客体”“科学”中“超越”出来,这样“彻底”“超越”的“先验现象学”,才是真正“独立”的“哲学”的工作。
由于胡塞尔“建立”的这样一种“哲学”工作的“独特性”,使他的“先验现象学”从通常所谓“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脱颖而出”,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脱离”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传统一样。
三、胡塞尔与康德
胡塞尔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里较少提到黑格尔,但对康德却给予了很高的崇敬和评价,并认真地阐述了“批判哲学”的不足之处。这可能意味着,胡塞尔认为他的哲学“直接”康德,而与黑格尔哲学“名同”而“实异”,尽管我们后人仍然觉得他们的哲学存有紧密的关联。
然则,康德哲学的确有“资格”作为种种“新”哲学的“起点”。不仅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这条思路,而且有“新康德主义”这条“文化哲学”的思路,而胡塞尔的思路则更影响至欧洲当代。
就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来看,我们可以说,康德的贡献在于对人类“意识-思想-认识”划出了两层界限,亦即对于胡塞尔的两层“悬搁”都“规定”了各自的“疆域”:“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不同“原则-原理”的“超越性”。
在“理论理性”“领域”,康德“建构”了“(经验)科学知识”的“先验原则”,确立了被休谟否定了的“因果”范畴的合理性,确立了“必然的经验科学”的“可能性”,而不“停留在”“习惯性”的“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中,“科学知识”从这个“朴素的世界”“超越”出来,以“先天的”“直观”和“概念一范畴”的“必然性”“形式”使这种“知识”成为“可能”。
在这种“经验科学知识”领域,康德“悬搁”了休谟的“怀疑论”的“问题”,树立了对于“科学知识”的“确信”。但是在这个领域,“理性”对“自然-朴素的世界”固然“拥有”“立法权”,但却只对“科学知识”“拥有”“建构权”,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有理由指出,康德这种“科学知识”仍然是“有前提一有条件”的,这种“知识”“预设”了一个“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一客观”“世界”,因而对于要求“建立”一个“绝对确信”、“无任何预设条件”或“无任何不言而喻条件”、“自身独立”的“(哲学)知识”来说,尚未达到“无条件确信”的“彻底性”。
康德已经意识到这个“不彻底性”而“预设”了一个“物自体”的“存在”,但正由于这种“不彻底性”,康德宣布这个“物自体”——这个“本源性-原始性-朴素自然”的“世界”对于“科学知识”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是“理性”“立法”“不可及”的领域。
康德“建构”的这种“有前提一有条件”的“经验科学知识”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带有一种“逻辑”的、“形式”的“必然性”,因为它的“先天性-a priori”无论“感性直观”还是“概念范畴”都是“形式”的,“形式”“保障”了“内容”的“必然性”。“必然性”乃是“被”“规定”“一定”如此,是“逻辑”“推论”出来的。
康德的“知识”“需要”由“外部”的“感性世界”通过“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时间-空间)”为“知性概念-范畴”“提供”一个“内容”,“知识”受这个“供应”的“制约”,它“建构”的“概念-范畴体系”是“必然”的,是“被规定”的。
“知性”为“自然”“立法”,这个“法”是“必然”的“法”,对于“知性”来说,也是“被规定”的,“知性”不“可能”“为”“感性世界”“本身”(“物自身”)“立法”。在这个意义上,“知性”是为了“建立”一个“科学知识体系”而“为”“知性”“自己”“立法”,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知性”的“号令-法”不出“现象界”,“知性”只可能为自己的“知性王国-知识王国-科学王国”“立法”。
“知性”的“立法”“领域”“受到限制”,康德哲学之“批判一批审”工作,正是要“防止”“知性”之“僧越”。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第一次”的“悬搁”,是从一个“充满偶然不确定性”的“朴素生活世界”,“提升为”一个“确定的-无可怀疑的”“必然世界”;而当这个“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要“回到-运用到”那个人们“生活”的“世界”里时,仍然会“遇到”种种“不确定性”。
如果把这个人们“原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理解为康德的“事物自身-世界自身-物自身”,则“必然”会“出现”他所谓的“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揭示了“科学知识-知性”的“僭越”,为避免这种“矛盾”,“知性-知识”必须严格“限制自己”,“限制”在“自己”“设定”的“必然王国”之中。
康德非常清楚这个“王国”的“局限性”,他的哲思已经“进入”更高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探讨”需要“再一次”“悬搁”,即从一个“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王国”中“超越”出来,这就是康德的“道德王国-自由王国”。
康德的“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来说,也是一次“悬搁”:把“知识论”的问题“置而不论”,“回到”“理性”“自身”,不受“理性”之外的任何因素的“制约”,“理性”“自身-自由”得到“阐明”;“理性”“自由地”“证明”“自己”之“存在”,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地”“证明”“自己”的“存在”,“无待”也“无需”“利用”“感性世界”的任何因素来“证实”“自己”。
康德“提示”的这个“第二次”“悬搁”当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在胡塞尔看来也具有初创时期的某些“片面性”和“不彻底性”。正如后来经常被提到的,康德的“自由意志”虽然很“高尚-纯洁”,但却是“软弱”的。在这个意义上,就“力量”的“实际”作用看,康德的“德性”并无“力量”,它缺乏本应具备的“实在性”,而只是一种“概念”,“纯粹理性”也就是“纯粹概念”;康德的两次“悬搁”都没有“超出”“概念”的范围,“悬搁”“方向”“向着”越来越“纯粹”的“概念”,从而他的“批判-批审”的工作,也就越来越“概念”化。
胡塞尔的工作,不但要有“概念”的“悬搁”,而且更要有“直观”的“悬搁”,这样,“悬搁”的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彻底性”。
当然,严格来说,康德的“批判-批审”工作针对的正是“概念”的“疆域-范围”,他的“自然”和“自由”都是“概念”,亦即“理性-概念”的“立法”“权限”:“知性概念”的“立法权”只限于“可直观”的“感性领域”,对于“思想”的“本质”即“自由”——即“自由”只可“思维”并无“直观”——来说,“知性立法”“无权”过问。
这就意味着,“自由”对于“知性”的“管辖区域”-“经验自然科学”来说,只是“空洞”的“概念”,而无“相应”的“直观”;“自由”而又“不可知”——“不成为知识”,认为“真正”“确定无疑”的竟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这样一种“悬搁”是一种“架空”,从而不是为“终止一拒绝”“一切可疑因素”的“悬搁一终止判断”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所在。
以“架空”“替代”“悬搁”依然“留下”一个“可疑”的“知识王国”,这个“王国”只有在“形式”上具有“确定性”,在“实质”上仍然充满了“偶然性”:“经验科学知识”有自身具有的“相对性”,那个“规定”“可直观”的“感觉经验材料”的“时间一空间”,也是“相对的”。
我们并无权要求康德具有后来的“相对论”思想,他的“时空观”来自于牛顿,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康德把“无限一绝对”的问题,“划在-排斥于”“科学知识”之外,对“经验自然科学”是一种“保护-防护”,但对于“哲学知识”来说,则有“消极”的“排斥”意义。
“哲学”是一门“异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既不是从“自然科学-经验科学”“超越”出来的“只剩下”“概念”的“元-物理学”,也不是从“经验伦理善恶”“超越”出来的“至善-自由”“空洞概念”。
应该说,康德自己已经“意识”到这样一种“分裂”出来的“概念”之“空洞性”问题,在两个《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之后,还有一个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判断力批判》力求把两个“分裂”的“领域”“沟通一结合”起来,在这个“区域”(不是“领域”,不是从“理性”那里“领”到什么“立法权力”),“自由”的“概念”也有了“直观”的“内容”,不再是“空洞”的了。
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这个“区域”“覆盖面”“涵盖”了“知识”和“道德”“两个”“领域”,但却并无“理性”的“立法权”,因而并无自己的“领地-王国”,虽具有“感性直观”,但“无权”在“感性直观”的“世界”“建构”“什么”;虽具有“自由”的“概念”,却“无权”“发布”“绝对命令”。
这个被康德称作“情感-审美”的“区域”,实际上就是后来包括胡塞尔在内的“现象学”所称的“生活世界”;但它不是“情感-审美”的,而是“知识”的,是“哲学知识”的“根基”,因而也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根基”。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就是那“自然-朴素-经验”的“生活世界”,而康德却把它看作“沟通”“科学知识”与“意志自由”的一个“环节”,“理性”对这个“环节”没有“立法权”,而只有“管理-规整”的“作用-功能”。
康德在“哲学”“领域”“实行”的这种“批判-审批精神”,可以被看作“三权分立”的一个“折射”:“理论理性”的“立法权”,“实践理性”的“审判权”,“判断力批判”的“行政权”;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理解方式,20世纪末法国的德勒兹业已开始。
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胡塞尔又回到“三权统一”,即“一切权利”归“理性”的“哲学”“传统”,以“理性知识”把这三个被分立的部分“统一”起来。“理性”无分“知-情-意”,被认为是“情感”的部分乃是一个“基础性”的“朴素-自然”的“生活世界”,它之所以是“基础性”的,是因为“任何”的“超越-悬搁”都要“在不同层次”上“回到”这个“生活世界”来。
“经验科学”的“超越-悬搁”,即使是“理论科学”之“搁置”“生活利害关系”也是“暂时”的,最终总要“改变”那种“朴素一自然”的“生活世界”,使这个世界更加“科学化一合理化”;同样,“先验现象学”-“哲学”对“经验科学-自然科学-客观科学”的“悬搁-超越”也是要“回到”那个被“自然科学”所“改造-浸润”过了的“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中来。
当“理性”实行“第二次(姑且名之)”“悬搁-超越”之时,也就是那个“朴素一自然一客观”的“生活世界”“提升”之日。这个“悬搁”之后作为“现象学”的“剩余者”的“生活世界”,可以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找到“对照物”,因而也是“理解”这个“剩余者”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