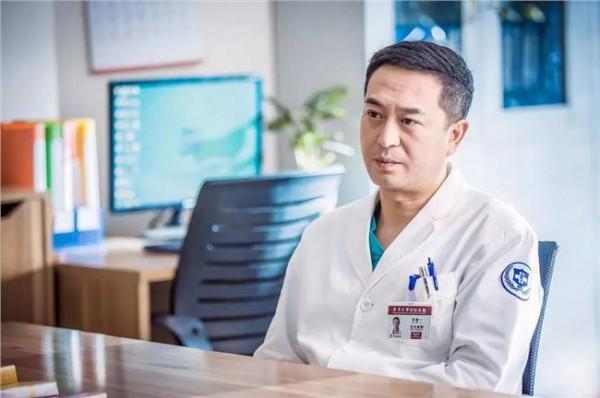郑晓龙影视作品 郑晓龙:三十年经典剧作的幕后推手
近日,北京晨报记者就“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视剧60年”对郑晓龙进行了专访。他回忆起了当年的入行经历,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他在电台已经是一名记者,薪资待遇、社会地位都不错,但是不安分的内心还是让他走进了高考考场,于是迈进了北大的校门;必然的是,他一直都从事着和媒体、文字有关的工作,从部队的宣传工作、电台的新闻记者、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再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最初从编剧、策划到全盘掌舵中心的项目……郑晓龙在电视圈中的地位确立和不断巩固靠的正是这么多年来一部部的精品力作。

1982年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后,郑晓龙就写了《空中小姐》和《迈克父子》两个剧本并主导了拍摄工作。由于当时的艺术作品几乎都是以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为主人公,因此这两部描写普通人情感生活的作品算是“另类”,引发了不少的质疑和争议,但播出后又反响很好,这无疑增强了郑晓龙接下来各种尝试的信心。

1990年《渴望》播出时更是火到降低了全国的犯罪率,公安部为此表彰了整个剧组;播出期间武汉某个区停电后因为老百姓无法收看《渴望》,市委的热线一度被打爆……此情此景不复再现。
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开创了电视系列剧的先河,属于能反复观看咂摸的经典。不过,这部剧的播出并不顺利,差点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对生活不严肃”等理由被搁置,险象环生终于播出后,老年观众对王朔式的语言幽默不接受,“哪里有个编辑部的样子,整天就知道瞎贫”,但年轻人非常喜欢剧中的调侃、幽默、戏谑,最终把这个片子的热度带了起来。

再去回看《编辑部的故事》,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拓展了国产剧的审美范畴。
《北京人在纽约》1994年在央视播出,当年的轰动不仅是视觉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不仅是行业内的,还有在社会层面的。明年,郑晓龙将投拍新剧《北京人与纽约客》,两部剧没有直接的联系,角色不同、演员不同、故事也没有延续;但也不是全无关系,因为两部剧都反映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别,二十五年前是《北京人在纽约》,二十五年后是《北京人与纽约客》。

从2005年到2015年间的十年间,《幸福像花儿一样》《金婚》《甄嬛传》《芈月传》……每一部都是荧屏佳作,郑晓龙通过数部经典作品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多年来在电视剧圈头把交椅的地位。从业36年来,郑晓龙目睹了行业环境、创作心态、数量质量、题材风向等各种流变,但他拍戏一贯坚持的是从不随波逐流,始终有着自己明确的想法和方向。
谈到入行以来始终保持高水平创作水准的秘籍,郑导笑言:“不浮躁、有耐心、不着急,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的好奇心。”
郑晓龙的经典作品有太多的幕后故事值得挖掘,这些作品像是这个行业的一面镜子,单独看,就是当年的那人、那事,带着明显的时代特色却又有着永不过时的共性;放在一起看,就能折射出行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应该改变什么?应该坚守什么?郑晓龙通过作品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
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北大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时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的郑晓龙和同事一起去海南采访了一个月,在当地跑了十几个县,回京后写了十几篇报道,都是关于海南农村的,还出了本类似游记的小册子。正是因为这次采访,郑晓龙错过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
难道采访比高考还重要吗?对很多人来说,肯定会选择高考。高考自然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儿,这意味着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但对郑晓龙来说则不是,他半开玩笑说,“我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此言不差,毕竟在电台做记者也算一份不错的工作。
“当时才25岁,如果我就那么混着也没问题。但我想给自己点压力,原来上大学之前就看过好多书,在部队的图书馆有大量的各种文学名著,《荷马史诗》《奥德赛》,还有莎士比亚的、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书都是在那会儿看的。”郑晓龙笑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里,男人都是以谁看过的书多为荣,看谁能出口成章,能说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靠才华混社会、跟姑娘逗贫,不是靠颜值。
因为有文笔、有文化,所以高考对郑晓龙来说不算难事儿,但最终他只考上了北大分校。“我没上北大,因为我数学没分,我也没去考,我完全不会。考大学我就想检验检验我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其他的四门功课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总共考了330多分,就靠这四门的总分也够分数线了,于是就被北大分校的中文系录取了。
”当时父亲也不太理解郑晓龙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考大学,郑晓龙说就觉得那会儿年轻人戴着校徽去上大学也是件非常牛的事儿。
“而且我还是带着工资上学,我有八年的工龄。我不到16岁就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来去了二炮,总共当了五年兵;部队转业后进了电台,当了三年记者。我也是老革命了,我一个月有40多块钱,经常请同学们吃饭。”
1982年,分配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大学毕业那年,郑晓龙29岁,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重回电台。孰料,四年后的电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广播电视局,里面增加了一个电视台,还增加了一个电视艺术中心,“当时的台长就问我愿意去哪儿,我想去电视台,电视台算新闻单位。
不过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期间还发表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于是,我就想电视艺术中心是搞电视剧的,搞文艺创作的,至少它和我的专业接的比较紧,于是我就在1982年底的时候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最早叫北京电视制片厂,和电影制片厂相对的意思,但后来有人说“厂”都是企业,还是叫艺术中心吧,毕竟是事业单位,于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名字就固定了下来。虽然是抱着十足的好奇和满腔的热情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电视剧到底是什么,郑晓龙坦言,那会儿真的没有很明确的概念。
在郑晓龙去之前,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只拍过《矿长》《头发的故事》。“更多的业内人认为电视剧接近于电视电影,而且那会儿中心的工作人员像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等都是来自长影、西影以及从各个电影厂调来的人,他们都有拍电影的能力,想回到北京,但北影厂又进不去,就都集中到了我们这儿。
”所以,电视剧到底是什么,大家都是一个有点迷茫又在不断学习的状态,并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是凭感觉去摸索。
因为是大学生,在校期间还发表过小说、电影剧本,郑晓龙很快成为艺术中心编辑部的主任,还写了《空中小姐》和《迈克父子》两个剧本。虽然播出后在业内还算有点影响力,但其实尚未播出时也受到很大的质疑和争议。因为以往的影视作品都是表现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而《空中爱情》是一个讲述爱情故事的作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这种作品的意义在哪里?另一种是,歌颂人类最美好的情感难道不是意义吗?最终,年轻人的声音和争论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空中小姐》和《迈克父子》得以顺利播出。
1991年,《编辑部的故事》遭遇阻力终播出
如果说讲述普通人生活情感的、中国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开篇之作《渴望》在1990年12月播出时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同样被奉为经典的《编辑部的故事》就在筹备期间和播出时均遭遇过相当大的阻力,“当时这部剧主要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插科打诨实在对生活不严肃,还设置了‘马列主义老太太’牛大姐,老实巴交但有点抠门小气的刘书有,还有本质不坏但唯利是图的余德利,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有点小毛病,这些人怎么能成为艺术作品的主要人物呢?”
郑晓龙先请思想比较开放的,当时北京广电总局的老局长张永经做艺术顾问,有人劝张永经,“不要拍,别晚节不保”,但张永经力排众议,《编辑部的故事》才得以立项开拍,“张永经主要觉得这作品首先是无害,其次是讲了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在笑声当中讽刺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郑晓龙回忆说。
能拍是第一关,能不能播又是接下来的一道坎。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他透露说,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跟他说很好,很有意思。于是,《编辑部的故事》得以顺利地在全国播出,不仅拿下大大小小的奖项,还成为了国产剧历史上的又一部经典。据说,姜文后来和郑晓龙合作《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因为看了《编辑部的故事》,他没想到电视剧能拍得这么有意思。
《编辑部的故事》开了不少先河,不仅是国内第一部系列剧,还是国产剧植入广告的鼻祖。在第五集的开头,余德利神神秘秘地抱进来一个东西,并给牛大姐介绍这是矿泉壶,专门做矿泉水的。厂家要在刊物上做广告,先给一个样品试用,广告植入的理由非常自然、合情合理,毫无遮掩地陈述了产品特性,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这玩意少喝,喝多了打嗝”。
郑晓龙说,那会儿对“金主”还有剧情都要负责,“我们不光编台词、还编情节,还要看起来合情合理,又让对方满意。
”当时,百龙的矿泉壶产品推出不久,几乎谈不上什么知名度。郑晓龙回忆说:“《编辑部的故事》拍摄时,那个老板来的时候带了好几个人,六七个人从一辆黄色小面包里下来,等他回来感谢我们的时候是坐着大奔来的。”后来有评价说,国产剧的这个首次植入可以作为行业范例,不像现在大多植入广告太不走心,只满足“金主”了,完全不顾及观众。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克服困难引轰动
现在剧组出国取景拍戏已经十分常见,少则十天半月,多则占到拍摄的近半时间,但全程在国外取景的剧组仍不多见。一是人员成本、制作成本问题,二是相关剧情其实和国外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文化氛围关系不大,“国外取景”更多的是一个宣传卖点而已。
但是,15年前在美国拍摄的《北京人在纽约》不仅是一部实打实的全程海外取景,而且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热潮”以及中西文化的矛盾。“因为要拍《北京人在纽约》,所以我认为必须去美国拍。不在纽约拍,在国内弄个假的,我觉得这个不可能,而且从去美国体验生活、采访,回来搞剧本,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外景上的不一样,内景也很不一样,你在中国哪找Supermarket,(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还没超市呢,街上还都是打酱油的小铺呢,是拿大木勺舀的那种……”
“第一是没有钱,第二对国外的了解特别少,但就是胆特别大。我们那个剧组40多个人,21集的戏整个在美国拍了差不多一百天吧。”郑晓龙回忆说,在拍《北京人在纽约》之前,他在1985年的时候去过一次香港,完全没有出去的经验。
“当时出国是一个社会风潮,多少人都想出国,因为那会儿不像现在,那会儿国外的物质条件和国内差距太大了,车辆、街道和人的富裕程度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郑晓龙第一次去体验生活,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十几天的时间里对美国概况有了大致的了解;第二次就是去纽约开公司了,一家录像带租售的公司,我在那儿当总经理呆了三个月,回国后就开始弄《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
“原来小说里面就没有王起明和郭燕离婚,也没有David这个人,重新做剧本时加了David,延伸出了郭燕跟David结婚,王起明和阿春这两条线。”至于为什么要加入David,郑晓龙有着题材和专业上的考虑,“我现在总结这个剧,表面上是商战加爱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讲不同的文化,东西文化的撞击。
我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故事放在美国的华人当中,所以加了David这个人,在他的身上能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以他对待郭燕的态度为例,David就会公开赞美她,他认为喜欢一个人就要给她更好的生活,这在当时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后来很多在国外拍的电视剧都没有这么深入的思考,也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就是一帮华人在国外,把他们的故事放在国内也同样成立。如果纯粹为了取景其实完全没必要。”
David并不是纯虚构的一个人物,他的真实原型是郑晓龙当时所在美国公司的一个美籍菲律宾的华人,一个非常西方化的华人。所以,郑晓龙最初想让陈道明来演这个David,但陈道明不会说英文,最后才改成了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人,“这个角色在戏里面必须是中文、英文都会,那会儿去找一个能说中文的外国人,简直太难了。
我最后找的这个David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秘书。他工作了几年离开使馆后,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中文。没想到他那口蹩脚的中文观众还特别认可,应该是很符合观众的想象吧。”
现在回看这部剧,无疑是对当时社会潮流的折射和反思,“当时大家特别想出国,我们就反映了当时大家想出国的心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会儿大家就觉得国外特别好,但是曹桂林的小说写出来之后我一看,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国外满地是黄金,他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
中国人一般有这么几种文化心理吧,比如穷家富路、报喜不报忧,还有衣锦还乡,等等,剧中对于这些文化心理以及中国人文化当中的其他劣根性都有反映。”
2018年,《北京人与纽约客》再度聚焦中西文化
《编辑部的故事》遇到的问题是剧本审查和能否播出,《北京人在纽约》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没有钱。“我们没钱啊,也没有所谓的金主爸爸,还是找银行贷的款。”前一段行业中流传着“互联网资本的弊端,以及怀念煤老板投资的年代”等文章,郑晓龙笑言,“最早是找餐馆老板、然后去找做服装生意的、后来才是找煤老板。”
“我们穷到什么地步?《北京人在纽约》就是通过我父亲跑到三九胃泰的药厂,人家赞助了五十万的启动费。我们去跟纽约负责这块的办公室报备了一下,说我们要在这儿拍片子,取得了整个的拍摄许可的一个证,那个不花钱的。事实上,他们要求你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再提前报备,他要派警察来给你维持秩序,还要给人家小费,这个小费我们都不乐意给,因为没钱。美国也觉得我们没钱吧,所以他们也不会较劲。现在肯定不会这样了。”
整个剧组人员的生活条件也是紧紧张张。拍摄期间剧组在五矿租了一个别墅,一个别墅住了三十多人,还剩下十几个人住在山下的一个小旅馆里。“美国法律有规定,每一栋房子里面住不能超过多少人,但当时我们自己做饭,还有其他的垃圾,所以每天扔掉的垃圾特别多,很容易招乌鸦……这就难免引起别人注意。后来我们还被告了。”
幕后的艰辛鲜为人知,但台前的风光却是有目共睹。“《北京人在纽约》剧组在央视春晚上站在纽约街头给大家祝福,你想想那会儿出国拍一个片子是多么大的影响,多么重大的事情,现在谁会把这当回事。”郑晓龙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郑晓龙的新作《北京人与纽约客》正在筹备中。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续集,而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这回是两地吧,前半部分是中国人去美国,在美国的奋斗;后半部分是美国人又到中国来……相比二十五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新剧有很多地方的变化:我们现在看美国就不像那个时候我们看美国,是仰视,在仰视的同时我们带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怀,我跟姜文那会儿在美国就感觉说这种爱国情最容易产生是在国外。
但是现在就变得比那会儿平和很多,是平视,大家会比较平等地来看这件事。就是变得没那么激愤,变得幽默了,变得敢于开玩笑了。同样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但故事的讲述明显会和那时候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实的反映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