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门自然拳 自然门始祖徐矮师
我在第一篇短文中,已略述杜师出榜访师,因四川友人之介,又因同他屡试功夫,都沾不到其边际,不得不从他学,心实未甘也。亦非有意暗算其师,因实明打打不着,只好暗打,而又因每一次打,则必更进一步的传授,所以也就越打越起劲。

这个情况,一是该时武器尚少枪支子弹,以武术技能来立身立业,重在实用,故专致力于‘打’;一是矮子本领高强,有心培育门徒,所以门徒越打他,他就越高兴,看透门徒是打不住着他的,假设换另一个师傅,则师生之谊早绝,杜师之行为,讲为人所不齿矣。

一年冬天,两人同食时,(杜师素于徐师同食共饮)这天小白炉上,炖了一满罐的羊肉汤,炉下托一支盘。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杜师在桌上,石钵石杵捣椒粉,请徐将炉和罐移入室内,室前原挂有一绵帘,徐诺之,两手托炉,漫步进室,刚抵室门,则换一手托炉,一手掀帘;一脚迈进,一脚尚在门槛外,就在这一刹那间,杜师看是好机会,相隔不及三步之遥,杜师双手举起捣椒粉的石钵,连石杵在内,猛向徐后脑打下,这在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不仅炉碎汤覆,人要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是毫无疑义的。

不图徐师爷不慌不忙,立换左手,托炉塞向室内,平方桌上,头向右一侧,用右手三指,捏住钵边,钵底恰好置在左肩上,有如碰上硬象皮的钳子,夹住石钵,分毫未动,汤未溅出点滴。
回首视杜师笑曰:“朗个啰!(四川口语,怎么了)!汤打泼了大家都吃不成了吗?”若无事然,伏案大嚼。象这样的一场闹剧,竟在两人对视,默默无声中结束了。他为什么只有三指?他的右手食指和无名指没有,似斫断者,问其故,不答。

终日小铜烟管不离手,也算是他的武器了。因为他不多言,不解释,不生气,所以杜师常用暗算方法求艺,暗中闹撇扭,总不会闹出意见,更不致引起仇怨,无异把他当作靶子来练习,遇有机会就给他几下而已。杜师常对我说:“似他这样功夫,除了遇到剑侠外,谁能斫去他二指?”
又一次,清晨练完功夫,徐立阶下洗脸,台阶有三四尺高,徐站在阶下,正临面盆架。杜师练的是七尺五的竿子,一见此状,认为又是大好机会;杜师在他背后,他是面向前方,根本没有注意。杜师挥动手上的椆木竿子,双手用力从徐后脑勺劈下,而徐却一腾身跳上石阶,在室中已转过身来,一手持巾,面对杜师时,洗脸盆已被棍子打的粉碎。徐笑曰:“朗个啰!把盆子打碎了,洗不成脸了吗!”杜师与其面面相观,作声不得,就此作罢。
杜师平日练七尺五的竿子(即棍子),竿子为硬木所作,因为南方不产白蜡竿子,多以椆木制成。置二石,如石锁者,中洞孔如杯,各重二十余斤。竿端撂在两石之间,左右一摆。把两手打得振振作响。再穿一石上起,翻过头来,摔在对边。
这一手练成,则竿端一落人之胯间,左右一摆,人之两踝关节即碎矣。如更一挑在裆间,即可将人挑起,摔他一个筋斗。于是杜师请矮师比长兵器,指架上刀枪谓徐曰:“由你挑。”徐曰:“你可随意挑选,我只此一短烟管足矣。
”师遂操七尺五竿子于他对垒,当头一竿劈下,徐轻快闪过一旁;接着横腰一竿,则从竿上跃过;即穿竿其裆间,向下一放,竿落踝部;左右一摆,这一袭击,在任何武术家,都不容易躲过而有击碎两踝之虞,但徐则左右一摇晃,竿端刚好在左右相差分许之际,却未打在骨上。
跟着穿进,一挑而起。徐本矮小,师原高大,一挑即至竿端,徐已骑上竿头;正相收竿时,徐已胯竿而下,与师面相对,以小铜烟斗敲师傅大拇指第一关节,痛彻心腑,豁然而坠。
正在抱指忍痛,气愤不伸之候,徐曰:“你这竿子,岂非替我拿的么?”说完话若无事然,微嘻点首,漫步回室,坐椅打盹,既不言其然,更不言其所以然。因此,更感抑郁,总想打着他一下,以出这口恶气。这种场面,诚古今中外功夫的人对于师道所仅见的。
杜师家住湖南慈利县之某村,那时练武术者是很普遍的。各村庄之比较富裕者,多延聘教师练武功以自卫。近村有一家聘请一位北方武术家前来教练。其人身材魁梧,功夫过硬。杜师原是武术界中为乡人所敬仰者,闻其聘一矮子为师,见这莫不窃笑;尤其这位北方教师爷,更为轻视,曾对乡人说:“他日如遇矮子,当教他从我胯下钻过,看他有多大本领。
”此事已风闻杜师耳中。时值春节,市后空场,设有剧台,乡人醵资演戏。剧场至正街,须通过一条窄小胡同,刚容二人摩肩而过;当日,杜师等亦往观焉。
剧终人散,杜师与矮师爷路径此巷进街,适北方武术家偕其徒众出街,相遇于小胡同中。其徒众即指徐向北方武术家曰:“前面的矮子,即徐某,后随者即杜某也!”北方武术家大笑,抢前一步,指徐曰:“矮子呀!
今天我可遇着你了,听说你很了得,今天你想过此胡同吗?”说着,即张大两脚,指裆下告徐曰:“可从此中钻过。”随行者皆停步不前,看矮子如何处理。矮子手提烟包和烟管,相隔约二三丈之遥,徐将烟管插入腰际,拽起长衫,笑对北方武术家说:“大个子!
你不要吹,你要小心!我说:‘我要过去了’!北方武术家正在凝神看他时,他已一跃穿过头上,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北方武术家的两额,提起向后一摔,竟如提一只小猫似的,抛出两丈多远,跃下不能兴,而矮子已飞步扬长而去矣。杜师回顾北方武术家,细察其两额深陷半寸许,昏不知人。徒众抬回,医治年余,始束装踉跄回里,从此不再言武而轻天下士矣。
旧时代,有榨房,为轧油用的榨油厂,恒用千余斤重的牯水牛,拽此巨轮榨油。邻村有一农人,畜有榨油的牯牛一支,比一般水牛硕壮一半;性烈,惟饲养它的农民可近,不然,则触之以角,献之以蹄。
某年夏天,晚餐后,杜师于徐师散步至此村头,此牯牛正系在大树之下,农人固亦擅武术者,笑谓徐曰:“闻你功夫很高,似我这头牛,你敢近它否?”徐曰:“此亦何难。只是,我如近它,它死了,或残废了,将如何?”农人曰:“可以打赌,我牛坏了,不要你赔偿;你如死了或伤了,又该如何?徐曰:“我有徒弟在此,他为我负责,不烦你分心。
”此时,围观者甚众,均鼓掌欢迎。矮子才将烟管插起,长衫拽起,牛正怒目相向,后腿上踢作势时,矮子已一跃走至牛后,顺步蹬下,双手握其后足两蹄胫处。
牛大怒,两蹄力掀,颠播摇撼,竟将前两蹄刨地下成一巨坑。只见矮子惟两手上下挫动,左右摇了几下,视牛已精竭力疲,再也不能动,徐两手一扬,牛即倾倒。矮子大笑,扬长而去。诸人往视牛时,两胫已碎,牛虽未死,不能用矣,农人无言,乃屠而货其肉,事闻一乡,皆为惊骇。
杜师常走镖云贵间,徐师爷同行。有一次,值盛暑,人们担货疲惫,憩于山麓。此山峻拔,上下可二十里,循石级而上,山麓距石级约数百步。杜师慨然叹曰:“人们传说,有飞檐走壁之能,我却从未见过。这座高山,在此暑日,要过去却是耗力;倘能飞行,不须片刻,岂不一跃而过。
”徐曰:“此有何难。”那时徐尚留发,(辛亥革命,才剪发辫),梳一小辫,辫绺,共长二尺许,平日盘在头上,此时散其辫,令师取孔币一枚,系于端,(孔币为当时通用之铜币,即有孔铜钱)。
脱去长衫,放下烟管,赤手空拳,短衣短裤。他说:“你看吧!”话甫毕,拔腿向山上直驰,望之,不见其两脚之动,惟见人似风车一般,瞬息已至山腰,还间发辫飘立,似棍如竿,再一转瞬,已达山颠,倏一返身,势如奔虎,惊顾间,已到面前,摔辫取下钱,交给杜师,目斜视,若不屑然。
气不上浮,面不改色,怡然自若,不言不语。杜师虽觉奇异,但终不心服,总认为他的行动,有如儿戏,有似幻术,并不感其神奇了得。
过山后,宿于农家,休息一日。农家畜鸡甚多,放在田野,间,杜师商诸农民,欲买一头,农民首肯。命子女数人围捉,鸡四处飞走,捉之不得。杜师自前抓之,亦不应手。徐嘻曰:“可笑练功夫,连一个鸡都捉不住!”师恚(hui)曰:“你既会捉,曷不动手。
”徐萧然曰:“欲捉哪一支?”曰:“前面具芦花色者是!”徐即向前,鸡竟不飞,一卡其项,甫将鼓翼,已被擒矣。农人曰:“好一个捕鸡能手,我正欲捉对过之红色雄鸡,烦亦我捕之。
”徐诺,如法擒获,似其夙畜,驯甚,不费气力,竟如拾芥,亦未见其用何奇妙手法。杜师明知有异,又故讽之曰:“你小人,动作比我们快一些,鸡见你不注意,故为你擒;倘是飞鸟,恐怕就是捉不着了。”徐曰:“我捉鸟么?也同捉鸡一样。
”师曰:“请一试”。适地有麻雀八九只。徐曰:“即捉麻雀吧!”师曰:“可!”问捉哪一支?师指远处一支,徐即一扑而上,如捉鸡然,雀正鼓翼时,徐的三指已落雀项上矣。余雀惊飞,稍定,又捉之。如此连捉数个,亦似其所畜者然,亦无从探其神奇之处,杜师无奈之何,只好忍气,默然无言而已。
遂起行,经山间之铁索桥,不似大波河之宽;上边一根铁索稍小,下边一根铁索粗些,过桥者须手扶上面索,下覆粗索而过。稍一失足,下临绝壑(he),坠下即成齑粉矣。徐先行,正在伸脚欲踏下索,手犹未握上索之际,杜师一看,好机会,走拢一腿,向徐腰部踢去;这一腿,即使躲过,也必坠入崖下。
不图矮子一转身跳到崖边,顺手掠着杜师的辫髦,如捉鸡然,望向崖下曰:“你这回之冒失,幸而对着我,不然,任何人都必为你葬送了,你今还有何说?我如一松手,你碎尸无地矣!”师大惊求饶曰:“今知吾师的功夫了,今后再不敢造次矣。”徐扬手一撂,抛出丈外,跌在崖岸,半晌始起,向徐叩谢,言知罪矣。
师常言神箭李广,有百步穿杨之能;神弹子李五,有野马奔槽之技,惜今人少能知者。徐闻之,即自小包袱中出一铁背弹弓,是两块钢片折叠而成,撑之则为一。又出小铁丸,如箭矢之用,曰:“行踪不定,小弹弓易携,试弹你看。”说着弓向空中弹去,侔弹丸下落到中途,复发一弹,把正在下坠之弹横空击落,如此三弹,均无虚发。
又在走镖时,只囊如小指头大之石子一掬。问有何用?曰:“防贼盗足矣。”请试其技,适前有兔鼠,取小石子投之,随掷即毙。趋前视之,已洞其脑,有如被火枪之铁沙子击中者然。并云:‘岂特石子,即黄豆、绿豆、甚至纸团,均可为用也。’
杜师又常在徐前侈言武松如何魁伟、如何力大,在景阳冈上打虎,如何英雄等等,徐微嘻云:“我呀打过老虎的!”当时并未信其言,后游艺江湖,所向未逢敌手,寻思矮师所言,殆成有之。似他这样功夫,岂特‘伏虎’已哉,当亦可‘屠龙’矣。
一日,嘱师作好套腿,乃以四层棉布为之,与徐试技。徐曰:“你不信我功夫,你要小心!”师尽力进出,徐不躲避,随起一跕碰在师之左迎门骨上,当即跌倒,不能起立,视之,无伤痕,亦未折断,只其脚尖跕处,有如钱大硬块,以药敷之,烂去死肉,其见深骨,医治三月始愈,师与从学八年,一日,对师曰:“你功有成,我欲行矣。
”问何之?曰:“行云野鹤,莫卜所止,尔后有缘,其於峨眉相见。”又云:“尔日后亦修大道之士,须读王船山所注‘庄子’一书,于尔当有裨益!
”言讫,遂行。不图悠闲岁月,竟无此机缘得循前约,益悔平日对徐之侮慢,良用疚心。只有一次,卧病河北保定时,将死,家人已备棺术矣。在昏瞀中,似见窗外飞进黑絮一团,窜至榻侧作声曰:“练到今日,气还没有下去吗!
”旋觉有掌抚摸胸腹,掌热如电,触处纷解,顿觉松快,霍然而起,即须大解,倾泻遂愈。细释其警欬,极似徐师。其即矮师爷成道,知其高足命不该绝而有意再临人间,予一援手乎?噫!‘言教不如身教’,矮师爷其亦斯人之俦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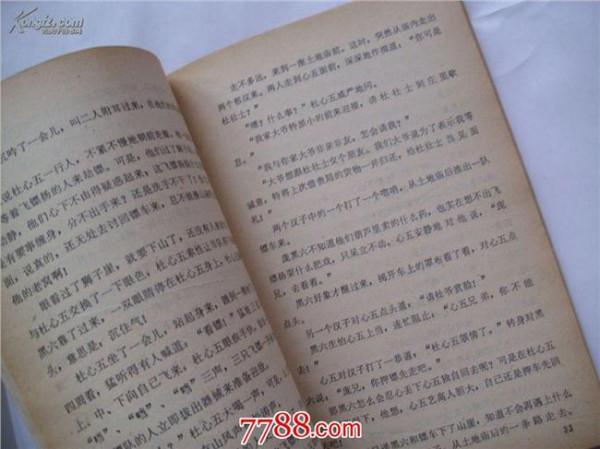

![>万籁声自然门应用拳 万慕通 林荫生《万籁声嫡传自然门内功技击》 [复印件]](https://pic.bilezu.com/upload/2/b4/2b46ce09e86e8da03209db43c948a8c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