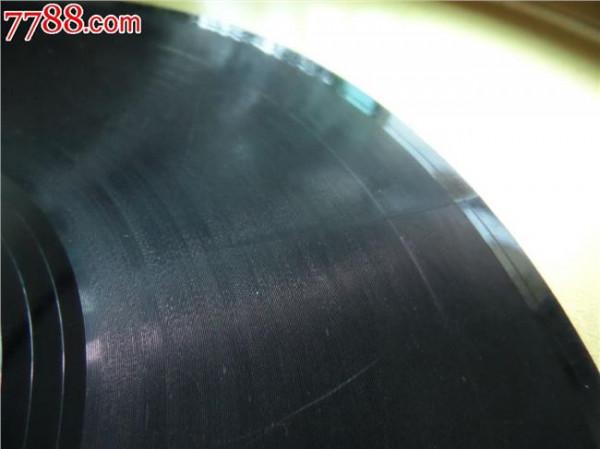殷承宗女儿 专访 京剧钢琴大师殷承宗——七十年风雨历程
夏末的中山音乐堂,迎来了七十二岁的钢琴家殷承宗,以及他为纪念三十年前卡耐基音乐厅首演的音乐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殷承宗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成为了中国交响乐的代表作之一。1983年移居美国后,他不遗余力的将中国古曲推上世界舞台,巧手之下,“洋”钢琴也说起了中国话。

上海寻梦:走了五天五夜
许戈辉:您把您这七十年的钢琴路总结为“七十年的中国钢琴梦”, 三岁与钢琴结缘,无师自通,能否跟我们聊聊您这场梦的开始?
殷承宗:当时我的姑父去了新加坡,他就把他家的钢琴放到了我们家。我们家有九个兄弟姐妹,姐姐们弹,我就坐在琴下听。他们会弹些简单的曲子,他们弹完,我就上去自己摸,就可以把曲子弹出来。那时候吃完饭要找不到我,我一定是在钢琴底下睡着了。因为兄弟姐妹多,所以父母也没钱培养我学钢琴。我就帮大妈妈摆鞋,她给我两块钱美金,一块美金我找了个老师,上了四堂课,学认谱。另外一块美金我舍不得上课,就买了一些谱子开始练习。

许戈辉:顺着您的履历看,您有三次离别故土的经历,对您日后的钢琴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是十二岁独自去上海求学,我很好奇那么小的年纪就独自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求学,从来没有像别的小孩一样,因为条件太苦想要放弃吗?

殷承宗:没有,我太喜欢钢琴了。当时福建的公路、铁路、飞机、船什么都没有,只能靠走。我和我同学两个人,身上揣着厦门音协给我的二十五块钱,拖了一个小箱子就上路了,走了五天才到上海。到了上海,阴错阳差的拿到份大学的招生简章,我就按着考大学的要求训练的自己,结果考了附中的第一名。

那时苏联正好派了专家过来,所以我在上海音乐附中的六年都是跟着苏联专家在北京、上海等各地跑。这一次远行让我真正的踏上了正规学习音乐的道路。
1958年,16岁的殷承宗第一次出国参加罗马尼亚埃乃斯库比赛,由于准备不足,名落孙山。1959年,17岁的殷承宗以十位评委全部给予满分的成绩,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冠军。此后殷承宗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
许戈辉:剩下两次分别是留学苏联,和取道香港远赴美国。这两次出国的经历分别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成长?
殷承宗:刚到苏联,音乐厅和歌剧院,是我每个晚上必去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像饿了很久的狼,什么都想吃。我不单学自己的科目,还学了室内乐、伴奏、作曲、指挥、声乐,每个我都想要多学一点。所以那三年是我快速汲取养分的三年。而到美国,则是开启了我职业演奏家的生涯。
“文革”十年:让钢琴说中国话
在苏联留学期间,殷承宗参加了莫斯科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殷承宗的名次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殷承宗说,其实这不亏,因为第一名现在也是世界很有名的钢琴家。
许戈辉:如果说那三年留学生活为你续集了能量,那么1963年回国,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想要释放能量,大干一场?
殷承宗:对。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之后,我在苏联演奏了六十场音乐会。刚开始回国的时候,毛主席还接见了我,鼓励我多搞民族的东西。后来下乡到农村,我创作了很多和农民生活有关的音乐,在农村很受欢迎。总理听了,也鼓励我们多创作这种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曲子,我也觉得要让钢琴说中国话。但后来发展的就有些不一样了,“文革”开始,这些就都不能弹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些不理解,我觉得怎么中国人就不要钢琴了,那么好一个乐器。
许戈辉:毕竟钢琴是西洋乐器,在批判封、资、修的潮流下,你有没有受到波及?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海归青年,在艺术被冲击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应对的?
殷承宗:有一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钢琴不能动,要动,就只能弹奏《东方红》和《国际歌》。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就只能变奏,因为你的手要动,不然就会僵掉。之后到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五周年,大家都组织宣传队上街跳舞,我就想,把钢琴抬到天安门去。
第一天,大家要听京剧,这和钢琴离着十万八千里啊,我就硬着头凭记忆弹了两段《沙家浜》。第二天我找了一个团里的演员,去天安门演沙奶奶,我伴奏,围观的人就已经上千了。第三天人就更多了。之后很多人支持我们,给我们写信。那时候工农兵说了算啊,有了这个支持腰杆就硬了,我就可以写信给中央,说我要搞创作,钢琴是中国老一辈人需要的。
受天安门为《沙家浜》钢琴伴奏的启发,1968年,殷承宗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公演。日后,该戏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1969年,殷承宗与多位音乐家合作,借用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主旋律改编创作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大获成功。
许戈辉:我知道您为了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使钢琴和京剧更好的融合,还特意去学了京剧,甚至在剧院听京剧,一听就是一个月。是否也有一些人质疑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做这样“洋为中用”的音乐,是政治上的投机?
殷承宗:不能说是投机,我做《黄河》和《红灯记》完全是自发的,不是上级布置的任务。我那个时候脑子里很清楚,想要钢琴重回舞台,一定要有它在中国该有的步骤。第一要借助京剧,采用合奏伴奏的形式。第二步,要有乐队,有协奏曲。钢琴协奏曲是很气派的,用它来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是非常合适的。第三步,要想钢琴单独出来,就得有独奏曲。我们搞了很多古曲,《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之类的。
远赴美国:“司机问我,你在哪个餐馆打工?我说我是弹钢琴的。”
“文革”结束后,殷承宗被当作“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政治审查。
许戈辉:钢琴伴唱《红灯记》、《黄河》让您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用钢琴来抒发对艺术的理解和感受。它让您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是后来也给您带来了长达四年的政治审查。那段没有钢琴陪伴的岁月,您是怎么过来的?
殷承宗:对。当时划地为劳嘛,其中有十个月我被隔离在琴房,不能摸琴。之前体委给了我一个举重用的皮带,我就把皮带放在钢琴里面,那样钢琴就没有声音了,我就偷偷练。那段时间很苦闷,好像自己做的一切都错了,是个没用的人。我记得当时在哪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内参,看到一篇外国人对《黄河》的评论,觉得这个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甚至说中国又出了一个贝多芬。那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许戈辉:1983年,对您的政治审查结束后,您恢复了演出,并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为什么还要带着五岁的女儿离开中国,远走美国?
殷承宗: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去完成我的钢琴梦,我是学西洋音乐的,但已经和外国隔离了二十年,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法国学派我没有接触到,德国后期这些浪漫派我也没有学到,所以我要去学。那个年代不管怎样,中国的运动还是很多的,在中国弹琴还是会有很多干扰。
许戈辉:做为一个刚从中国“文革”走出来的音乐家,刚到美国的发展是怎样的?您1983年3月到达美国,9月就在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而且当时《纽约时报》对您的评价非常高。这样的发展速度其实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殷承宗:其实在1973年,费城交响团访问中国时,有个经纪人看到了我弹奏《黄河》,他当时想请我去美国,我没去,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批的。所以我到美国后又找到了这个经纪人。这样很快就促成了第一次卡耐基音乐厅的演出。当时观众是非常少的,大家都不知道你。我打车,司机问我,你在哪个餐馆打工?我说我是弹钢琴的。他说,你在哪个餐馆弹钢琴?就是总离不开餐馆。我说我要在卡耐基演出了,他就是不信。
《纽约时报》评论:“对于我们这些常以孤立来形容中国历史的人,殷承宗使我们惊讶。四十二岁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星期三在卡耐基音乐厅举行他在纽约的首演,展现的不仅是他对乐器的卓越控制,还有他对乐曲的正确理解。”许多优秀的青少年钢琴家跟殷承宗学过琴,著名钢琴家郎朗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选择钢琴”
许戈辉:我很荣幸看到了您卡耐基音乐厅首演三十周年音乐会。您现在回望这七十年的钢琴路,您觉得艺术生涯里还有没有什么遗憾?人生还有没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
殷承宗:历史不能重复,人生也后悔不来。选择钢琴,我是很幸福的,如果有下辈子我还选择钢琴。
许戈辉:近些年,有“文革”的回潮,也有“文革”的悔潮,以您自己的经历看,您觉得政治和艺术分的开吗?
殷承宗:我还是一直坚持政治和艺术要分开。我记得那时候让我写检查,问我每天做什么事情?我说很简单,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几千几万个音符,还哪有时间去搞别的事情。这些东西虽然写在那个年代,但现在对艺术还是有价值的,无论有什么痕迹在里头。我从小在教会上学,唱的是赞美诗,中国音乐一点都不懂,要是没有那个年代,我也不会去更深入的了解中国音乐,这为我的人生开启了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