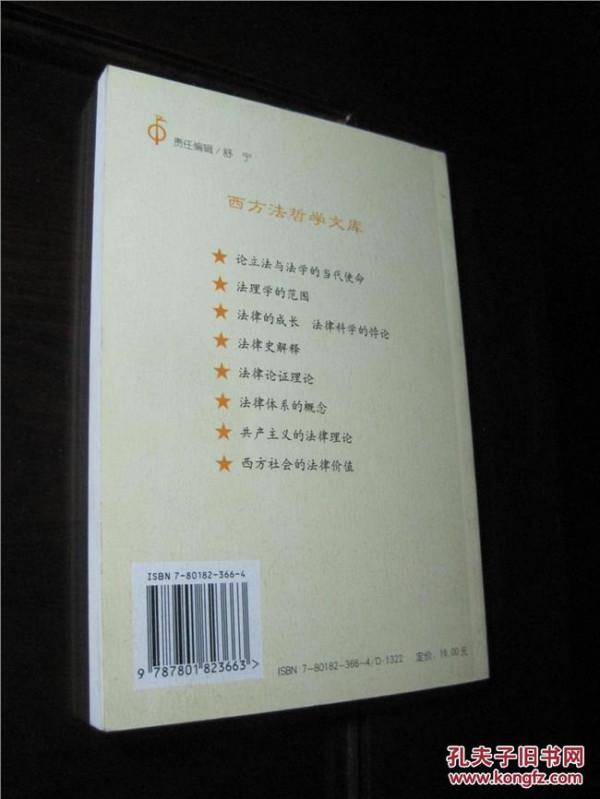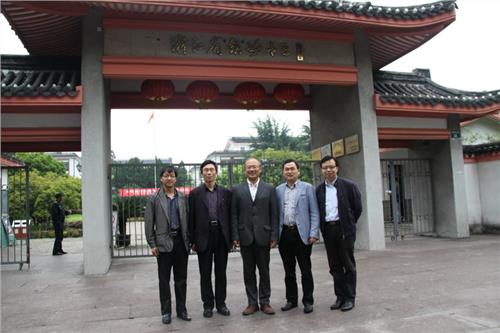法学高鸿钧 高鸿钧:法学研究的大视野——社会理论之法
在西方,社会理论(1)的发展已有数百年之久,其中一些流派对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把从社会理论视域对法律的观察和分析称为“社会理论之法”。为了推动我国在社会理论之法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我们搜集了汉语世界晚近研究和解读社会理论之法的重要文论,并将其选编成集,分为马克思篇、涂尔干篇、韦伯篇、哈贝马斯篇和综合篇。
下面拟结合本集所选文论的内容略论社会理论之法的几个基本特征。——高鸿钧:《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导言
法学研究的大视野——社会理论之法
在西方,社会理论(1)的发展已有数百年之久,其中一些流派对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把从社会理论视域对法律的观察和分析称为“社会理论之法”。为了推动我国在社会理论之法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我们搜集了汉语世界晚近研究和解读社会理论之法的重要文论,并将其选编成集,分为马克思篇、涂尔干篇、韦伯篇、哈贝马斯篇和综合篇。
下面拟结合本集所选文论的内容略论社会理论之法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关联思考与整体视域中的法律
一般说来,法律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视角,即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前者着眼于有效的实在法,研究法律体系的结构和层次,探究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目的,分析法律规则的语义和逻辑,阐释法律程序的形式和功效。在现代社会,不但法律实务者采取这种视角,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立场的学者也采取这种视角。
他们如同大家闺秀,虽然偶尔窥望窗外,但活动的范围基本囿于“法律闺房”。他们担心,一旦打开“法律的窗门”,道德、伦理、宗教以及政策等法外“杂质”就会乘机侵入,法律的“贞洁”就自然难保,法律自治的“城堡”就会失守,法律与非法律的界限就会模糊,法律的确定性就不复存在,由此法治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导言:法学研究的大视野另一种视角是外部视角。社会理论视域中的法律就是一种外部视角。通常认为,“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世界的作用的相对系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反思”(2)。“社会理论之法”是从社会整体的视域研究法律,法律只是作为社会现象或要素之一。
研究者从法律之外观察、思考和分析法律,将法律置于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观察法律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分析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互动,追问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探求法律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其终极命运。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或法官,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职业角色,遂放弃了法学而从事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然后从多角度观察和分析法律。在他看来,把眼光仅仅局限于法律本身,无法探明法律背后的社会力量,无法理清法律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复杂关系,无法揭示法律所表达的真实意志,从而无法把握法律的真正本质。
于是,他把法律置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之中,考察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联。
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了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法律所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是普遍的社会公意;法律决定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而不是相反。今天看来,其中的个别观点或结论虽然有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之嫌,但是这种研究法律的进路仍值得借鉴。
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视角,把法律同社会分工关联起来,指出了社会分工如何影响了法律价值取向的重大变化,分析了法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他还探索了犯罪与群体意识的关系,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一种行为并非因为是犯罪而震撼了群体意识,而是因为震撼了群体意识而被认定为犯罪。
(3)涂尔干是一位职业社会学家,没有受过法律专业的训练,但他从外部视角对法律的观察和分析颇有创见,其方法和结论对于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受过系统和完整的法律教育和训练,并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这种专业背景使他能够对法律从内部视角进行研究,像一个法律职业者那样熟练地阐释法律分类、法律命题和法律思维,具体地比较分析罗马法、英国法和欧陆法的基本特征。
但是,像马克思一样,韦伯的视野远远超出了法律,他的兴趣涉及经济、宗教、政治、社会以及音乐等诸多领域。在有关法律的观察中,他明确区分了法律职业者内部视角的教条法律观与社会学家的经验性法律观,并始终坚持后一种立场。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从他的“理想类型”出发,把法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的法律、实质非理性的法律、实质理性的法律和形式理性的法律。显然,这种划分潜在地关照了法律演进的历史脉络。简言之,“形式”是指使用“法内标准”,“实质”是指使用“法外标准”,如诉诸道德、宗教或伦理的裁决,“理性”是指裁决案件的依据明确可察,合理可喻,“非理性”则与之相反,例如诉诸灵魅、情感或未经反思的传统的裁决就是非理性的。
相比之下,其他几种法律类型或者采取的是“法外标准”,或者裁决案件的依据变化莫测,因而裁决结果往往是随意的或高度不确定的,只有形式理性的法律采取的是“法内标准”,且裁决依据由法律明确限定,因而同类案件的裁决结果具有确定性和一致性。
韦伯认为,在现代的理性化社会,只有这种法律才与目的理性行为相契合,才能为目的理性支配下的个人提供精确的计算尺度,才能最有效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因为此他才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形式理性的法律不可避免地会取代其他类型的法律而占据主导地位(4)。
十分有趣的是,韦伯从外部视角研究法律,即关注法律的历史变化、法律与经济和宗教的关联以及社会行为类型与法律类型的内在关联,但最终结论却转向了内部视角。在他看来,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社会行为趋于理性化,非理性的行为被理性的行为所取代,非理性的法律也被理性的法律所取代。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过程颠覆了上帝的一统权威,导致了“诸神之争”,由此任何终极性的统一价值都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正当性不得不求诸于自身的形式。
结果,形式理性的法律不得不从社会中独立出来,同道德或宗教等实体价值剥离开来,筑成形式自治的“城堡”(5)。正因为这种结论,韦伯的法学理论在结论上似乎与法律实证主义殊途同归,并因此而受到了批评。实际上,韦伯对自己的这种结论也深感无奈和不安。
当代学者哈贝马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对哲学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之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最后,他开始把目光集中在法律问题上,在法学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自成一家。
由于上述学术背景和研究路径,从社会整体的视域和关联互动的角度研究法律,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他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溯了古代的法律及其合法性(6)基础;回顾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发展的四个阶段,并从整体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划分为两种基本范式;把社会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界面,然后分别探究了法律生成的合法性源泉;从言语行为出发论证了交往理性行为应有的主导性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重构了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
所有这些表明,哈贝马斯是把法律置于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中来思考,从法律与道德、伦理、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关联互动中探索法律的地位、功能以及合法性根基。(7)
由上可见,社会理论之法不同于其他进路的法律研究。第一,它从法律之外观察法律的现象和特性,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和要素的关联互动中分析法律的地位和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探索法律的产生和命运。与内部视角相比,这种外部视角以广阔的视野,更充分地展示了法律现象的复杂性,更真实地揭示了影响法律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更深刻地指出了法律的性质、功能以及局限。
第二,社会理论之法的外部视角不同于自然法学派的外部视角,它拒斥“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之类虚拟的历史或模糊的观念,坚持从实际的历史过程出发,把握法律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从实在的社会现象或事实出发,探索法律与社会之间关联互动的奥秘。
第三,社会理论把法律视为社会现象和要素之一,将这种现象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避免了内部视角“见木不见林”的褊狭。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整体视域的法律研究往往存有“见林不见木”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涂尔干关于法律发展的解释表现得较为明显。
他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简单分工与复杂分工两大阶段,与简单分工相对应的是机械团结,反映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是压制性法律;与复杂分工相对应的是有机团结,彰显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是恢复性法律。
(8)这种概括虽然颇富洞见,发人深思,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整合机制及其法律的不同特性,但毕竟过于宏观和笼统,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社会演进的复杂性。
毋庸讳言,韦伯的“理想类型”和马克思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以及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概括,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以西欧封建制为原型而概括出来的“封建社会”模型,就不适于解释古代印度的村社制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社会。
他本人在晚年也发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但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系统研究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架构。最后,从方法论上讲,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法学研究各存利弊,整体视域与具体视域的法律分析互有短长,实际上两种研究进路和方法可以实现互补。
在我国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法学研究曾偏重外部视角和整体视域,忽视了法律本体的理念与原则、具体的制度与规则和内在的思维与程序。近年来,法学研究开始关注法律本体的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这种转变无疑值得肯定,但如果以为这是法学研究的惟一正路,并由此拒斥外部视角的法律研究,那就未免偏颇了。
二、现代性、法律与社会整合
现代社会最先出现于西方,后来扩展到世界各地。在西方,现代性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其重要标志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开始萌发,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科学业已产生。但是,古希腊人的理性之光仍然笼罩着神灵的阴影,其科学之魂也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而随风飘散。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曙光,那也只是灵光一现。实际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始于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实现了个人主义价值的暗渡陈仓,于启蒙运动时期完成了思想和价值的彻底转换,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现了体制变革,最终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的宪政政治中得到了制度落实。
如果从简单的进化论出发,人们会认为社会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为之欢呼雀跃。当然,持这种乐观姿态者自然不乏其人,经济学家斯密就为“经济人”时代的到来而高唱赞歌,而社会学家斯宾塞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拍手称快。
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现代社会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和尘世的天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新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上帝死亡了,人们高奏理性的凯歌而告别了信仰的时代,转而却发现自己失去了精神家园和终极权威,不得不诉诸权力意志的冷酷博弈;传统的家庭、行会、教会和庄园解体了,人们从过去血缘或身份性组织解放出来,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迎接梦寐以求的自由女神,转而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新的经济压迫和政治权力的枷锁之中;传统社会的等级特权消除了,人们为平等时代的到来而大声欢呼,转而却发现法律的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实际的不平等。
诸如此类的现代悖论隐含的是现代性的二元冲突:凡俗与神圣、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个人与社会、民众与政府、权力与服从、身份与契约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人们进行了种种思考。起源于现代早期的社会理论针对现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个体的社会化、知识的理性化以及权力的合法化构成了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它们集中体现了西方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和反思。这里我们不关心现代性的一般性问题,只感兴趣社会理论大师对于法现代性问题所做出的独特回应。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9)取代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与此相应,“法学世界观”代替“神学世界观”以及统一而明确的法典取代分散而模糊的习惯法,也都是重大的历史进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远远优于封建社会的特权、束缚、专制和人治。
他甚至认为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但他同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仍然存在对立的阶级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其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都有历史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自由和民主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