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讲课好无聊 邓晓芒:我已经就是哲学 哲学就是我
去年11月,69岁的哲学家邓晓芒出版了新书《哲学起步》。从字面上看,这是一本向大众通俗解释现有哲学知识的书。然而在邓晓芒看来,这不单纯是一本普及读物,因为书里一些主要观点是他独创的,是对已知哲学观点的刷新。

邓晓芒说:“我已经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我。没有哲学思考,我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日前,长江日报记者走近邓晓芒的哲学世界,对他作了专访。
60岁以后要建立的自己的哲学体系
1948年,邓晓芒出生于东北,一年后随父母南下长沙。1964年,初中毕业的邓晓芒从长沙下放到湖南江永县插队。在10年的知青生涯中,他辗转湖南多个县。也是在这期间,他开始读起了哲学。1974年,邓晓芒回长沙当临时工、搬运工。期间有调到销售岗位摆脱体力劳动的机会,被他拒绝,他说喜欢干完活后有大片读书时间的搬运工岗位。

1979年,邓晓芒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主攻德国古典哲学,直至2009年离开武大,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至今。近40年的学术生涯,邓晓芒在康德哲学研究上成果颇丰,还多次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在学界内外享有盛誉。

新作《哲学起步》,是邓晓芒给华中科技大学法律系等非哲学专业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的录音整理。在邓晓芒看来,多年来他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经典的解读、阐发,除了把自己的一些哲学思考顺便带出来,以及偶尔几篇纯哲学的文章发表外,很少有机会展开他自己的哲学思考。出版于1995年的《灵之舞》几乎是唯一例外,那时他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以一种体系化的方式进行一番哲学的清理。
由于长期从事一种“注经”的工作,有年轻朋友曾问邓晓芒何时把自己的哲学“正式”建立起来。他答,起码要六十岁以后,要看的书太多了,他还在经典的“围城”中艰难突围。康德“三大批判”的“句读”花了他10年,接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句读”用了5年。能把自己哲学体系的导论部分完成也算不错,邓晓芒于是把这门给本科生上的课当作创作自己哲学的一桩重要工作来做。
从“认识你自己”开始哲学起步
许多人觉得哲学高深、难懂,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邓晓芒认为哲学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难,哲学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只是许多哲学问题与我们谋生不太相关,平时就放过去了。
学习哲学如何起步呢?邓晓芒认为,不仅仅是学习一些哲学基础知识,而是凭借已有的常识,运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生活中的经验,来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来触及人类世世代代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当今人类关注的问题。他说,当我们静下来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当小孩第一次学会用“我”来说自己,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它时,在他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这道光就是智慧,西方人称之为“理性之光”,意味着智慧开悟了,这是最早的哲学智慧,这已经是哲学起步了。
邓晓芒说,古希腊太阳神的德尔菲神庙上有一个神谕,叫“认识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我自己”,这就是最早的哲学素养。怎么认识自己呢?就要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入手。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的本质问题”、“自我意识的本质问题”、“自由的本质问题”。由此延伸出一系列哲学命题,如探讨人的本质问题,就要讨论“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人的精神”三个问题。
心灵鸡汤是听了很舒坦“快感哲学”
为什么近些年“心灵鸡汤”流行?邓晓芒说,“心灵鸡汤”是指那些含有哲理的通俗话题,或者说哲学快餐,这种东西在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和禅宗中历来都是拿手好戏,如我给你讲个故事,编出来的,或者打个“禅语”,就足以让你“受用终身”。儒家也有,但儒家板脸说教的成份更多些。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让你听了以后心里面特别舒坦,可以满足一些“乐感意识”。
西方哲学不同,它往往导致人们对自身的严肃拷问,让你不得轻松,有种“罪感意识”。西方哲学难以做成“哲学快餐”,老是有种沉重的话题,这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关。我们平时讲的“自我意识”、“真正的自由”、“做自己”等,都是从西方哲学中拿来的。
邓晓芒说,年轻人今天想要了解这些问题,可以多看些西方哲学方面的书,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和文化也要关心,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么博学多闻,而是真正用来思考人生问题,建立起自己丰富的个体人格结构。这往往是一个痛苦和孤独的过程,不像心灵鸡汤那么享受,但应该作为年轻人“成人”的必修功课。
(访谈)
西方现代哲学对中国当代思想无异于一剂毒药
记者万建辉
我也出版面向“文青”的书
读 :感觉您过去多出版哲学专著,这次为何出一本面向大众的书?
邓晓芒: 我历来有两种文字,一种是纯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像《思辨的张力》、《康德哲学诸问题》,和各种哲学经典的逐句解读(句读)等等;另一种是普及性、通俗性的,这主要是一些讲演录,如《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康德哲学讲演录》、《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等等,以及一些随笔集,如《徜佯在思想的密林里》、《人论三题》、《新批判主义》、《启蒙的进化》等等,还有就是非常风行的、20多年来已多家出版社接力棒式地出到了第四版的“文学与文化三论”套书,即《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都是面向各个不同层次上的大众、特别是“文青”的。
现在这本《哲学起步》是根据给大一非哲学专业的本科生上的一门“哲学导论”课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当然要考虑到通俗性了,但又不单纯是一本“普及通俗哲学知识”的书。也就是说,不是向大众通俗地解释现有哲学知识的书。
读 :出版《哲学起步》这本书,您的初衷是什么?
邓晓芒:《哲学起步》是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地道的哲学书,虽然形式比较通俗。我以为哲学书不必写得那么晦涩难懂,但内容一定要有哲学深度。我的初衷就是借助于给本科生上“哲学导论”课的机会,为自己正在构思中的“自否定哲学”做一个引导,当然同时也把青年学生引进哲学的大门。
书里提出的一些主要的哲学观点都不是已知的,而是包含有我独出机杼的见解,或者是对已知哲学观点的刷新,它可以看作我将要建立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导论”。
读 :为何您说周围朋友当年的雄心勃勃现在少多了,而您是苦命,也是乐观主义者,干活要干到底?
邓晓芒:我说的所谓“苦命”当然是说笑话了。我丝毫没有觉得苦,就是当知青和搬运工时也没有觉得,因为我有件事情乐在其中。我在69岁出版了《哲学起步》,应该说目标有了初步的实现,今后要建构的是一个纯粹哲学体系。但在此之前,还要把手头一些事做完,比如现在正在努力赶工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的整理。
更愿意通过写书或讲座进入公共视野
读 :哲学家周国平出版的许多书,在解答当下人们的现实困惑和焦虑。哲学家陈嘉映去年接受网络视频节目“十三邀”访谈。你怎么看他们两人?
邓晓芒:周国平和陈嘉映都是我所敬重的很有成就的学者,当然各人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尽相同。
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上电视和视频,曾婉拒过《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邀请。我觉得哲学这种东西只能是小众文化,而普及性达到媒体的程度,我的口才又不够,我更愿意通过写书或讲座,让有心人进入我所思考的问题中。
读 :感觉近几年您通过媒体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少了,这是为什么?
邓晓芒:我对社会公共话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我一开始就不是把目标定在批评社会现象上,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学者。我的发言通常都着眼于人们在公共话题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我要对这种思维方式中被遮蔽了的东西加以揭示,进行一些个案分析,一方面为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提供现实的例证,另方面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推广。
前些年,我对一些中国人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作了不少批评。近些年我的发声相对较少,甚至有媒体约我发声也被我谢绝。我的理由是“该说的已经说过了”,我不愿意老是重复。
读 :您鼓励今天有哲学爱好的小镇青年、农民工子弟继续自学哲学吗?
邓晓芒:我当年在农村当知青,经历过十多年的底层生活,是生活本身的磨砺使我产生了想要学哲学的强烈欲望,不是想要当哲学家,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只是想把人生的问题想清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今天民间或底层也有不少的人喜欢哲学,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抱着我当年那种心态在看哲学书,如果仅仅是当作一种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我想那恐怕不能持久,也许最终会失望。
我鼓励他们为提高自己的素质、看清人生的真相而学习,但不要太功利,那只是一种个人兴趣而已,也许会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助,但也许没有。
西方现代哲学渗透进了大量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读 :您提出制造使用工具,特别是携带工具,是人的本质定义和人区别于猿的关键,为何您特别强调携带工具这一点?
邓晓芒:我提出“携带工具”是人猿之别的关键,这是我这本书从哲学人类学角度所提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观点,它将对当今国际上由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所统治的人类学界产生重要的理论冲击作用,同时又成为我从中引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一个基点。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一个能够将以往零散的有关人的哲学命题全部贯通起来的总纲,例如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类的关系、语言符号的产生、历史的本质、自我意识的结构、理性和精神的发生、自由的起源和谱系等等,都要从这一基点才能得到透彻系统的解释。
读 :流派众多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在康德、黑格尔哲学基础上,是否是哲学这门学科的进步?
邓晓芒:我主攻德国古典哲学是经过选择的,本来也可以选择别的,但我通过对各种哲学的对比而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最能够代表西方文化整体精神的哲学,而且它具备这种自觉,而同时代的英国经验派则缺乏这种自觉,他们更偏向于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
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则受到两种倾向的冲击,一种是语言分析的技术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国靠科技竞争而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时代潮流之下大面积地挤占以往人文哲学的地盘,使当代哲学的总体思维水平大大下降;另一种是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导致人文哲学领域里面鱼龙混杂,渗透进了大量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解构因素,使所谓的“后现代”哲学走向哲学本身的消亡。
读 为什么您说西方现代哲学还没有成体系,中国急需学西方一两百年前的古典哲学?
邓晓芒:如果说西方文化由于其深厚的哲学传统还能够对这种时代的逆流有某种抗衡能力的话,那么这一潮流对于缺乏这一传统的中国当代思想无异于一剂毒药。所以我对康德、黑格尔的研究和解读不单纯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启蒙的事业,它能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今天真正所缺乏和所需要的思想营养在哪里,从而建立起全民族的自我反省精神。
没有这种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可能在当今时代的残酷竞争中真正得到新生。
读 :为什么您说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上,相较于北京、上海,武汉是一个重镇?
邓晓芒:武汉作为哲学的重镇是从李达校长创办武汉大学哲学系时就开始了的,当时也聚集了一批人才,常与北大哲学系对举。这一传统后来一直传下来,西方哲学这一块是江天骥、陈修斋、杨祖陶等老一辈学者奠定了基础,他们的优良学风影响了武汉高校一代又一代的后学,至今犹可见其端倪。
我身上也有文人性格
读 :您在《思想者的随笔性格》一文中提到您和陈嘉映都是知青一代人,能否谈谈您和陈嘉映交往的故事?
邓晓芒:嘉映和我也是老相识了,但其实见面的时间不多,也没有深谈过,倒是通过读他的《泠风集》,我觉得和他有种思想上的默契,很能理解他那种话语风格。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候并不需要什么“故事”,一句话的说话方式就可以拉近两个人的距离。他学术上做的是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或常识哲学,和我有些隔,但他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是翻译得极好的,很见功力。
读 :您的一名学生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不买房不成家,在一间有床垫和开水瓶的房里,不发论文,不评职称,只做学问,您怎么看?
邓晓芒:我不认为做学问就要放弃生活,也不认为不写论文可以叫做学问。一个做哲学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些想要写下来的思想,而只要写了下来,如果真有思想,在今天要发表也不会很难,当然体制的限制有些人为的障碍,但对于一个勤奋的学者这种障碍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这个时代有种种弊病,但真正要想做学问,还是可以有一口饭吃的。所以我常对学生说当今时代是中国几千年不遇的可以做纯学问的时代,要珍惜。
读 :您对哲学还像年轻时那样有热情吗?
邓晓芒:不存在“我对哲学有热情”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我。没有哲学思考,我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我说过我身上也有文人性格,这是文化和传统的烙印,没有办法的事,但也没关系,只要我意识到这点,它就会限于只是我的哲学研究的形式,而不是反过来,让哲学成为它的形式。我周边的朋友各色各样,但也多少都有点文人性格,而且大都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转换,所以他们仍然面临有“我对哲学”怎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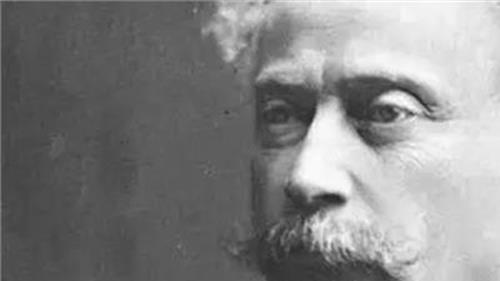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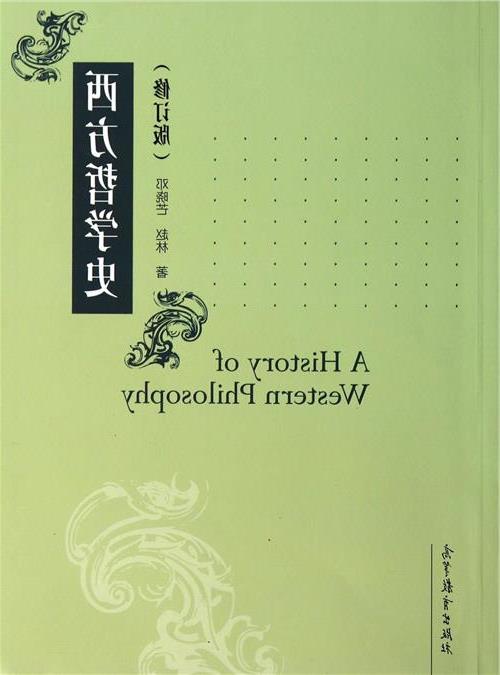

![>《邓晓芒教授著译作系列》文字版+影印版[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4/02/4023d87b5bd996bb048e57ea52104f3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