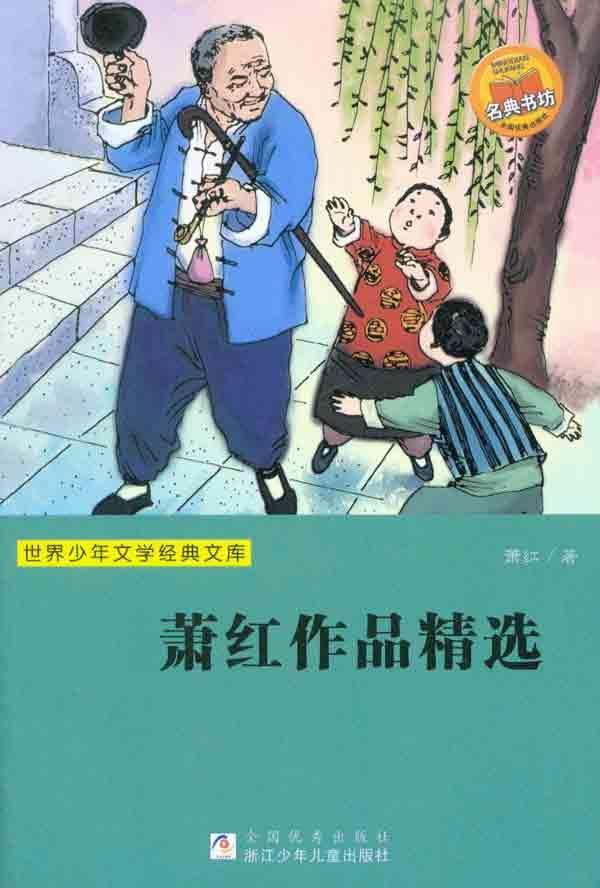端木蕻良的孩子 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不虞之隙”
1938年9月中旬,萧红拖着怀孕八个多月的身子,一个人到达重庆。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委实难以想象。萧红曾对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端木蕻良此时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之邀,在新闻系任兼 职教授。
萧红便先到江津的白朗家中待产。这期间,萧红每天不是给端木和朋友写信,就是裁制衣裳,还给即将诞生的孩子做了小衣服。
在当地一家私人妇产小医院,萧红生下一名男婴。三天后,孩子死了。 所谓“小哀喋喋,大哀默默”。当意外事件已经超越人的承受力量,至情之人,不会有祥林嫂式的表达。曹雪芹最为心仪的阮籍,在母死之时,便曾有过不近人情之态。
人生穷途的“孤寞忧悒”,又岂是世俗辗转中渐渐麻木恣睢的人所能懂? 出院后,萧红离开江津回重庆。临上船时,萧红与白朗握别,凄然地说: “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萧红惊问着,接着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1938年底到1939年,一年多的时间,萧红与端木蛰居重庆。
萧红与端木的相处,在旁人眼中,有着各样不近人情之举。众矢之的,自然是端木。在武汉,除了前文所述的“撇下萧红去重庆”事件,还有“萧红独自提行李”事件,同样引人非议。 这是绿川英子因听到池田幸子对萧红处境的惋惜、感慨,而在头脑中想出来的一个悲剧的印象: 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
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
她只得时不时的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 从绿川英子的行文中可以看出,这是她“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一幅带有象征意味的、用“同情与愤怒”的情感渲染过的画面。画面上不是生活的动态场面,而是构思的静态图景。她是有了对萧红与端木先入为主的看法,才有了这画面。 到重庆后,又有了“端木嘲笑萧红”事件、“端木殴打佣人”事件的发生。
据靳以所述,有一次他来访萧红,见萧红刚放下笔,便问:“你在写什么文章?”萧红一面脸微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低低地回答:“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这声音引起正在睡觉的端木的好奇,他一面揉着眼睛一骨碌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又一次,重庆难得放晴,端木推开窗子,发现邻家的女佣把一双脏兮兮的旧鞋子搁到了他面前的窗台上。
于是他猛地一下把窗子推开,鞋子就掉下楼去。不料泼辣的女佣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
端木门一开,二话不说,一巴掌把那个女人推了出去。对方借势倒在地上耍赖,闹到了大街上。端木却潇洒地关门了事,反正听不懂那女人的四川话,就当与己无关。然而事情终得解决,萧红跑到楼上,向靳以求助,说:“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地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了钱了事,这些琐碎又麻烦的事都是萧红一个人奔走。
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不像“萧红独自提行李”事件只是文章作者的想象,重庆的两件事是确实发生的,也为端木本人所承认。回忆者因着同情萧红,鄙薄端木的成见,行文中的情绪也在所难免。 长期以来,端木都遭到众多同行朋友的杯葛,他在众人之中属于“异类”,为身边的人们所厌恶。
在其他人眼中,他既有激进的“左翼倾向”,又像潦倒的“传统文人”,还是个懒散的“资产阶级分子”。平日里“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就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 众人对端木的攻讦实属冤枉,但端木也绝非没有他的问题。而这,大概与他从小便受到《红楼梦》极深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