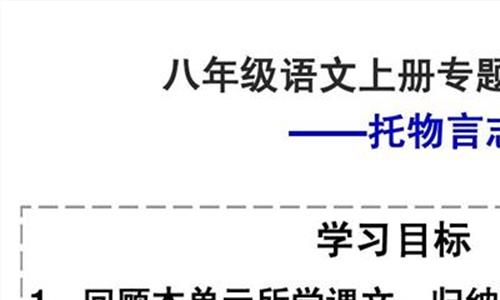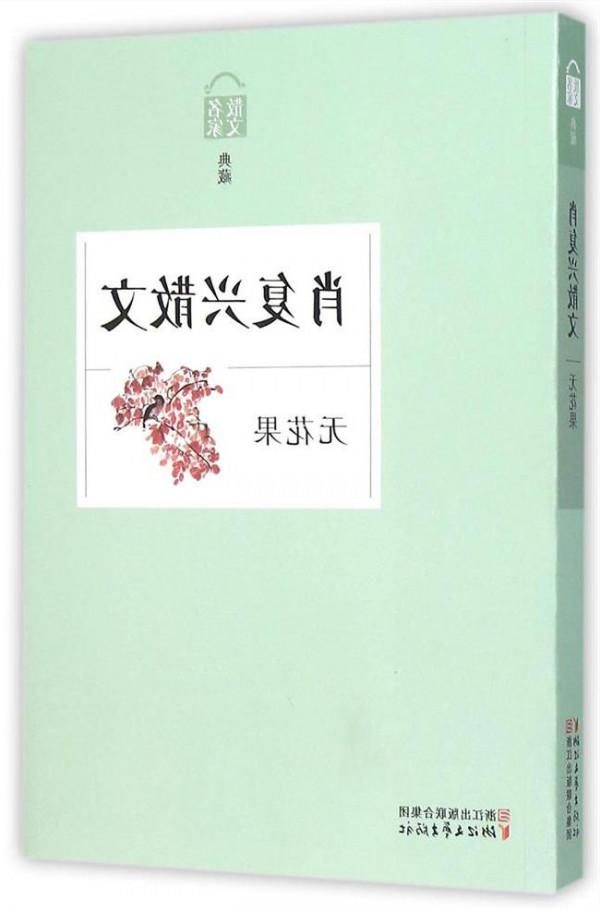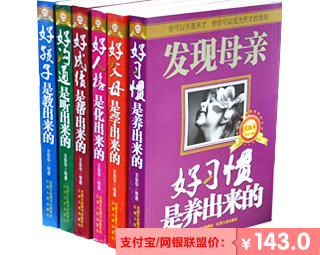母亲肖复兴 肖复兴:白葫芦花
从北大荒插队刚回北京的时候,我搬家到陶然亭南。那里新建不久一排排红砖房的宿舍,住着的都是修地铁复员转业落户在北京的铁道兵,住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之所以从城里换房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很清静,而且,每户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小院。母亲最喜欢这个小院,可以种些蔬菜吃。
那时候,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里的街坊在报纸上看到,见到母亲时,常常夸我,让母亲很有面子。在这片地铁宿舍,我算是有点儿文化的人,颇受这些淳朴的街坊们尊重。
夏天时一天晚饭过后,一位街坊来到我家拜访。是一个中年男人,很瘦、很黑,很客气。我第一次见到他,才知道他就住在我家后排,姓陈,湖南人。落座之后,他直言相告,想求我帮他写个状子。我问他要告谁呀?他垂下了头,沉吟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告诉我,是要告他老婆。
我问他为什么呀?一日夫妻百日恩,什么事情过不去?他对我说:哪天有工夫,你来我家一趟,我给你看看东西。然后,又对我说:我歇病假,哪天都在家,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望着他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我家的小院,我心想,什么东西,石头一样压得他这样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下午没课,我从学校回家早,去了他家。他见我就说:你来得正好,家里没人。说着,他趴在地上,从床铺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在箱子里的一个土蓝色的包袱皮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是几封情书,另外一个男人写给他老婆的。他从中找到一封,对我说:你重点看看这封。我看后,明白他要告他老婆的最终原因了。这封信里白纸黑字说孩子是他老婆和这个男人的。这是压倒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叹口气,瘫坐在床头,对我说: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她在村子闹出这样的事情,每次回家探亲,我都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不,我和她闹离婚好几年了,她一直不同意,一口咬定孩子是我的。她不知道,这几封信我早都看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是信任我,才找我帮他写这状子,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帮他写。我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从来没像宋世杰一样写过状子呀。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接着对我说:我现在病了,不瞒你说,是肝病,挺严重的,说不准哪天就不行了。可越是病了,越觉得忍不下这口气。你说要是你,你忍得下吗?
我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孩子的笑声。他赶忙把信塞回包袱皮里,藏好在箱子里,把箱子推进床铺底下。
他送我走出屋门,我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向他跑了过来;小姑娘的身后,站着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女人,我格外注意看了她一眼,长得挺俊俏的,是那种惹人怜爱的女人。她的头顶是一个铺满绿叶的架子,午后的阳光,透过密密的叶子,在她的身上跳跃着斑斓的影子。她冲我笑笑,说:是肖老师来了,怎么不再坐会儿?我挺尴尬的,有些做贼心虚地说:啊,坐半天了,老陈要找我下盘棋。
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忍不住又瞟了她一眼,不巧和她的目光撞在一起,她依然在笑,我却更有些尴尬,慌不择言地指着架子说:开这么多的白花,这种的是什么呀?
老陈走过来说:是葫芦。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葫芦开花。满架的绿叶间,白色的葫芦花开得像一层雪,风吹过来,像是一群翻飞的白蝴蝶。
这里每家的小院里,住着的都是勤俭持家的人,大多和我母亲一样,种蔬菜的多,种花草树木的少。大多人家栽的是一些扁豆、茄子、黄瓜、丝瓜和西红柿架子。那时,我见识很少,以为种葫芦不能吃,只能看着玩,最多做成瓢。后来,我对老陈说过这话,老陈说:葫芦也能吃,到时候,长出青葫芦来,请你来吃清炒葫芦。
老陈又找过我好几次,在他的坚持下,我帮他写成了一个状子,也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总觉得和我写的小说散文不是一路活儿,写得挺耙劲。老陈把状子拿回家看后,又找到我,说我写得力度不够,这样到法院真的打起官司,赢的把握悬乎。
我趁机劝他,你自己都觉得悬乎,干嘛非得要告你老婆。一封信上说的话,就能证明那孩子不是你的?人家法院就能信?再说,你把孩子都养了十来年了,你舍得不要了,给别人?接着,我又问他:你老婆对你好不好?这么漂亮的老婆,你也舍得不要了,给别人?他不说话了,我看得出,他犹豫,又不甘心。
告状这事,老陈一会儿气哼哼地非告不成,一会儿又瘪茄子不吱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就这么自己折磨自己,有时候摔盆摔碗和他老婆闹,常常是他的闺女跑来找我去他家劝架。就这样,好好坏坏,一直闹腾到了秋天。
一天傍晚放学回家,他的小闺女跑到我家对我说:我爸要你去我家!我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去了他家。老陈要请我吃清炒葫芦。是他老婆炒的,新下架的葫芦切成片,放了几片红辣椒,喷了点儿香醋,真的挺好吃的。清脆,又一股子清香。我连连称赞,夸他老婆厨艺好。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葫芦,回味不已。我不知道,那时候,老陈的肝病已经很严重,已经到了肝腹水的程度。他行动不便,很少出门,到医院去看病,都是他老婆蹬着平板三轮车,驮着他,穿过沙子口的粮库和地道,到永外医院,一路不近呢。最后,他住在医院里,已经无法出院了,也是他老婆一夜一夜守着他。我去医院看过他,对他说:有这样一个女人,是你的福气,别再提离婚的事了!他不说话。
那一年冬天,老陈病逝。他老婆料理完后事,准备离开北京回湖南老家。我问她还回北京吗?她摇摇头。
临别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来我家一趟,对我说:我知道你帮我家老陈写状子告我的事情。尽管我也劝老陈不要告她,不要离婚,但见她这样直面说我,还是非常尴尬。她接着说──她比老陈能说多了:老陈的心情我理解,搁谁也都会打离婚。不过,这事你信吗?然后,她这样反问我。
见我一时语噎。她接着说:我来找你,不是来和你掰扯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的,是来给你送东西的。
送我的是用半拉葫芦做成的瓢。
她说:是老陈临走时嘱咐我做的,他说你稀罕这玩意儿!
她离开北京后,她家的房子换了主人。新搬来的人家,把葫芦架拆了,改种一个葡萄架。偶尔路过时,我会想起老陈和他的老婆。我再也没见过白葫芦花,没吃过清炒葫芦,老陈老婆炒得确实挺好吃的。老陈送我的那个葫芦瓢,一直在我家放了好长时间。那时候,自来水管在院子里,冬天冻了,得用开水浇一次水管,要接水存放一天。我家有一个水缸,那个葫芦瓢在水缸里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