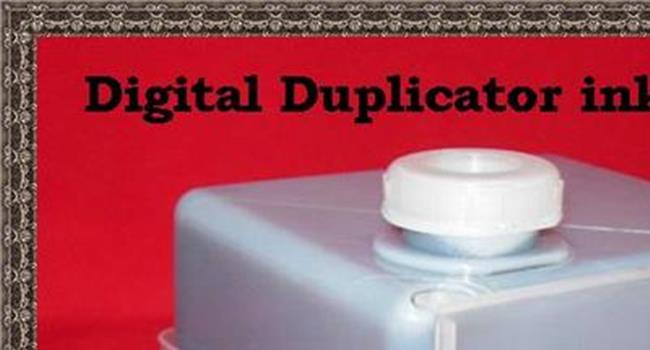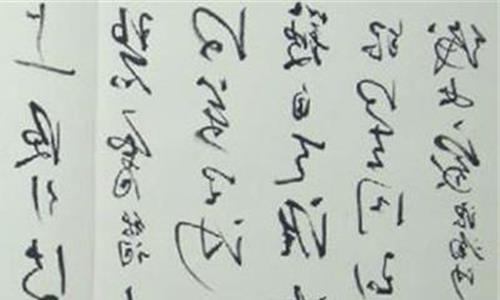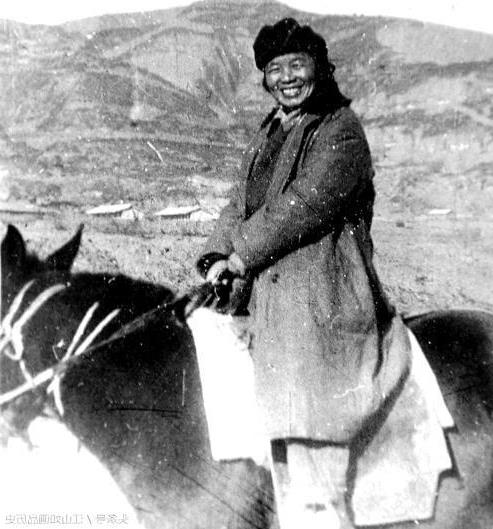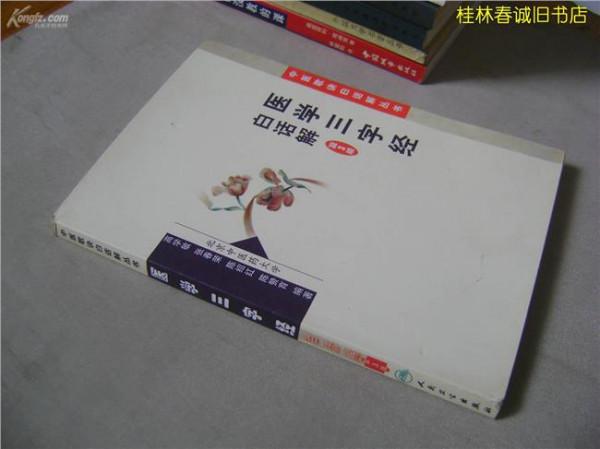张景岳的错误 为什么陈修园那么反对张景岳?
我们现在学习的八纲辨证,就是张景岳他总结出来的。“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这是整篇《景岳全书》核心中的核心。喷张景岳的医者,怕是没有仔细通读他的书吧?不错张景岳最为人诟病的是写了一篇《类经》,公然给自己的书名冠以“经”字,这难怪后人不爽。

但仔细看《类经》和《景岳全书》无一不谨守内经框架,无一例越出内经理论的。他所发挥的,都是临床医理,都是为了打通理理法方药此四事而著的。且看张景岳自己是怎么看的。以下引自《类经》自序:
奈何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 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期冀夫通神运微,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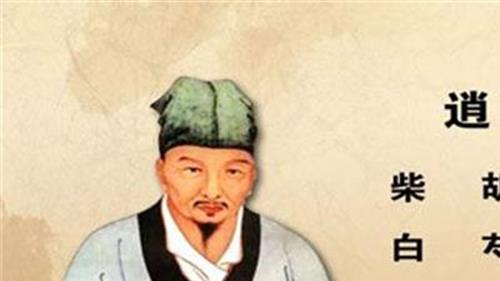
自唐以来,虽赖有启玄子之注,其发明玄秘尽多,而遗漏亦不少,盖有遇难而 默者,有于义未始合者,有互见深藏而不便检阅者。凡其阐扬未尽,灵枢未注,皆不能无遗憾焉。及乎近代诸家,尤不 过顺文敷演,而难者仍未能明,精处仍不能发,其何裨之与有?初余究心是书,尝为摘要,将以自资,继而绎之,久久 则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因奋然鼓念,冀有以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而公之于人,务 俾后学了然,见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原,斯不致误己误人,咸臻至善。

于是乎详求其法,则唯有尽易旧制,颠倒 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庶晰其韫,然惧擅动圣经,犹未敢也。 吁!余何人斯,敢妄正先贤 之训,言之未竟,知必有阚余之谬而随议其后者,其是其非,此不在余而在乎后之明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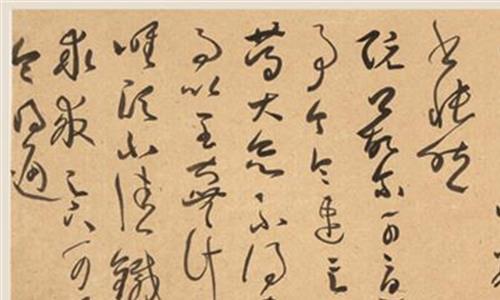
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断流之水,可以鉴形,即壁影萤光,能资志士,竹头木屑,曾利兵家,是编者倘亦有千虑之一得,将见择于圣人矣,何 幸如之!
独以应策多门,操觚只手,一言一字,偷隙毫端,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所谓河海一流,泰 山一壤,盖亦欲共掖其高深耳。后世有子云,其悯余劳而锡之斤正焉,岂非幸中又幸,而相成之德,谓孰非后进之吾师云。
正如下文 Timi 截图所说的,是要治病留人,还是留人治病。张景岳所著,通篇强调医者要治病之前,必须首先看看病人本身,目无全人是不对的。“而不知汗之出与汗之收,皆元气为之枢机耳。故余纪此,欲人知合辟之权,不在乎能放能收,而在乎所以主之者。 ”,这个原理的提出,比黄元御的中土回环论早了一百多年。以今天的中医经验看,治病的时候注意保护脾胃,注意保护病人的正气,这些经验正是张景岳承传而来的。
其实看张景岳的书,完全可以抛开他的新方八阵,直接从他的医理中心入手,再结合原有的伤寒、温病等临床理论,那就真正可以做到张景岳所说的“不在乎能放能收,而在乎所以主之者”。如果后人见人用熟地,也不分青红皂白也跟着用半斤熟地,那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了。即使要学,也要清楚张锡纯反复强调的:
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 、《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 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 治吸不归根之喘逆; 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 加苏子、浓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时病患服之觉有推荡之力,后制参赭镇气汤治此证更效,又尝减茯苓、泽泻三分之二,治女子消渴小便频数(《金匮》谓 治男子消渴以治女子亦效,案详玉液汤下), 又尝去附子,加知母、白芍,治阴虚不能化阳,致小便不利积成水肿; 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 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 加五味、枸杞、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之说; 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 用熟地四两、 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 又尝于一日之中用熟地斤许,治外感大病之后,忽然喘逆 ,脉散乱欲脱之险证(此证当用后来复汤,彼时其方未拟出,惟知用熟地亦幸成功 ,是知冯楚瞻谓熟地能大补肾中元气诚有所试也),且不独治内伤也; 又尝用熟地 、阿胶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二剂,济阴以应其阳, 使之自汗(详案在寒解汤下); 并一切伤寒 外感,因下元虚惫而 邪深陷者,莫不重用熟地,补其下元,即以托邪外出。
惟用以治阴虚劳热之证,轻者可效, 若脉数至七八至鲜有效者。彼时犹不知改图,且以为地黄丸,即《金匮》之肾气丸,自古推为良方,此而不效,则他方更无论矣,不知肾气丸原用干地黄,即药坊间之生地也,其桂用桂枝,即《神农本草经》之牡桂也,与今之地黄丸迥不侔矣。
其方《金匮》凡五见,一治“香港脚上入少腹不仁”;一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一治 “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一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一治 “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
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 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
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用生黄芪 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
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 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芪 、知母,莫不随手奏效。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 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
黄 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 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 ,此不治之治也。
况劳瘵者多损肾 黄芪 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 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普也(黄 、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 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如果不清楚其中原理,即使像张锡纯这样的大师,也有用熟地失手的时候,后来才恍悟阴阳阴阳者,必须阳中求阴,阴中求阳,偏颇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看前人写书都是这样的,人家写书,是把自己最为独创的那一点见解写出来,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单独把某一个人的医书来出来喷,那自然是很爽。可是别忘了,即使像叶桂叶天士这样的大师,当初跟徐灵胎开撕,一开始也是以为人家的徐灵胎乱作方子,“有吴江秀才徐某。
在外治病。颇有心思。但药味甚杂。此乃无师传授之故。”,后来叶天士自己看到了《外台秘要》,说“我前谓徐生立方无本。谁知俱出外台。可知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