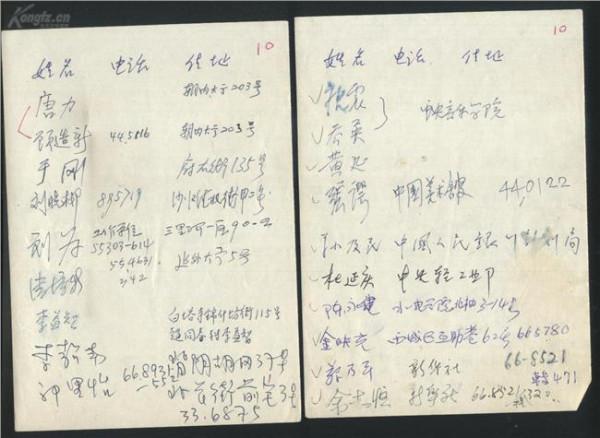中国的道路李慎之 李慎之的检讨书
在历次运动中,我参加了一些,但是都参加得不多,我总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十分积极的,我心里总是怕过火、怕伤人。我总是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我总希望看到我们专政的宽大的一面,而不愿看到它严肃的一面。我总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各项工作、各种制度。我并没有真正站稳过无产阶级立场,而我的右倾思想是十年一贯的。正是这些思想的日积月累,一直到形成我今天一系列的反动思想,自己也成了一个十足的右派。

我的思想问题逐渐进一步暴露而发生新的变化,是在1953年与1954年之交。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以为,1954年以后,我过去所崇奉的日丹诺夫的许多理论,在苏联东欧都开始有了翻案,我自己屡次出国,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觉得过去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未必对。

同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也连续发生了一些事件,如柏林事件、贝利亚事件、纳吉上台下台事件、苏南建交事件等等,因此,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怀疑。
拿这来比附中国,就觉得思想战线上的许多是是非非很难说。同时,觉得从那时起,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化政治问题上的怀疑抵触就多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入一点看,不为无因地巧合的是,这正是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时候,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统购统销这样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对这些,我并没有什么抵触,但是,社会的这些变动必然要在人们的意识上得到反映,而党也就着手来解决这样意识上的问题。
因而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改造都加紧了。以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
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胡适学术思想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报刊、杂志上批判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这是一场又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是革命深刻化了,一方面是我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性已经发挥完了。而我的留恋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已经开始露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现在看起来是自然的。我原来不过是怀着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目的而参加革命的,实际上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固然,我自己并不是资本家,我并不要求保持物质财富的私有制。
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把知识看成是个人的产物,个人的资本,因此实际上要求保持精神财富的私有制。而我所谓的精神财富,又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些东西是无产阶级决不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决不能容纳的,因此必须批判它们、改造它们。
然而这样的改造就触动到了我的阶级本性。各种各样的批判在我看来都是对我的否定,对我所认为“真”、“善”、“美”的宝贝的否定。本来,如果我能够把那些被批判的思想当作镜子,积极地从这些思想斗争中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话,我就可以跟着党一直前进。
但是我却不去利用党给我的这种大好机会,反而因为这些运动没有直接牵涉到自己而站在一旁窃窃私议,表面上是吹毛求疵,实际上是怀疑抗拒。
我现在还没有回忆分析自己到底在哪些具体的思想问题上滋生了抵触,这个工作我今后一定要细细来做,但是,总的说来是这样一些感觉渐渐积累起来了:“党管思想管得太多了”,“思想学术上的花色品种减少了”,“运动伤人了”,“思想批判太深文周纳,成为诛心之论了”。
久而久之,我就感到这是一种“思想统治”,这是“从来没有的对思想的压抑”,我不去看看到底统制了谁,压抑了谁,是不是该统制、该压抑,是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而是以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本能,感到这样下去会造成“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会“蔽聪塞明”,会没有智慧。
这样,我就认为我们的社会里“民主”太少了,“自由”太少了,个性太受束缚了。十分明显,当我向帝国主义、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还有点进步性革命性,当我向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就只能是倒退的、反动的了。
渐渐地,我感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我所要的,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却不能满足我的理想了。我渐渐暴露出我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市侩本性,因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牙齿发痛,而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了。
然而,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我思想上的这种抵触与怀疑还没有明确地、直接地牵连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上去。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国际上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逆流,我身上原来顽强地保持着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在这些外部因素的触发之下急速地发展起来。
我大量地吸收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然后一下子把我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牢骚不满都明确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上去。
而当我抓住这么一个反动的中心思想之后,又把我过去的一切反动思想固定化、扩大化,推而广之延伸到我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广泛的方面去。我狂妄地以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为根据,公然要靠制度解决问题。
而到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就形成了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这时,我已经不是仅仅抗拒思想改造,而是要想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和社会主义了,这样,我就直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到今年年初,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以后,我的狂热就越来越高。我把从中央听来的片言只语,一概按照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串联起来,作出极端夸大,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的了解,来设想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都要作改变的新局面”要开始了,要“从上而下”地变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的领导,发疯似的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向人贩卖自己的反动主张,以此来炫耀自己,影响别人,希望别人同我一样来怀疑、来议论、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
到中央决定提前整风以后,由于我对运动一贯害怕,我一度还有些情绪低落,但是后来看到社会上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好像正是向着我所期待的改变制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就接受了“风气论”,以为就是应当像社会上那些右派那样来大鸣大放,来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写出了点火式的墙报文章,积极地同人谈话来散布自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过去曾把自己的言行的动机说成是好的,实际上我想的就是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我也正是这样做了,这时,我一年来在政治上的激烈动摇就最后导向了完全的堕落,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5月底,我的反党言行因为社会上的右派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使我恐惧,因为党的警告而开始收敛,然而错误已经永远地铸定了。第一次使我感到警惕的是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最后发言,他说:“有一些共产党员证明只能作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能作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而现在,十分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我经过了民主主义的革命,然而却没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这是我的耻辱,我的悲剧。然而,这却正是一个对党忘恩负义,不听教诲,一意孤行,拒绝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得的惩罚。
我的发展道路清楚地说明了我的罪是我自己造成的,是必然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时期以后,我曾经怨恨党会整到我身上。然而反本求源,不是党有负于我,而是我重负于党。党多次伸出手来要带动我前进,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我拒绝了。历史的车轮不能待人,我在急转弯的时候摔到了车外,正是我自己应当从这里头吸取毕生的教训。
三、我的反动政治主张的实质是什么?
关于我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同志们已经在六次大会上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言行思想的反动本质,并且给了我以马列主义的武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同我自己的反动思想作斗争。我可以向同志们表示,在几个月来党的教育下,特别是在大家的批判以后,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已经彻底破产,我决心全部地、永远地抛弃它,向党、向同志们缴械投降,至心归命。
当我现在要在这里批判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可能重复同志们已经提到过的许多论点。但是,正如刘修学同志在《前进报》上所说,我过去是给别人也给自己搭了一座“迷魂阵”,我陷害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现在我应当亲自来拆掉这座迷魂阵,让它在同志们面前,也在我自己面前彻底消灭,不留残迹,永远地不再害人害己。
我打着追求社会主义的“民主”,防止“个人崇拜”,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等等漂亮的旗号,然而要是以马列主义来分析我的各色各样的实际主张,那么,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分析下去,都可以看出,我所要求的东西结果都只能通到和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都只能是破社会主义,而立资本主义。
我在自己思索和向人宣传自己的这一套政治思想的时候,常常还自欺欺人地说自己的目标是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但是要是坚持我的这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就根本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就只有再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说:“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我所想的、所做的就正是这一点。
最后,我把过去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考虑都说成是“忧党忧国”,好像自己所设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然而实际上,我哪里曾经丝毫懂得或者想去懂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的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荒谬绝伦的照搬,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
再剖析一下,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给我种下了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它一方面培养了我的自我扩张,把“个人”看成是高于一切,一方面又把“自我”深深锁闭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小天地中,而不去同伟大的集体同呼吸、共甘苦。
我的日常生活充分表现了我的这种人生观。我一方面是狂妄自大,一方面又是离群索居。我不要说不参加工农的集体生活,连知识分子的集体生活也不爱参加,以一个膨胀浮肿的自我,同二三知己胡吹乱捧,高谈阔论,这就是我所沉醉的小天地。
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千百万群众在热火朝天地行动的时候,我不拿自己的身心去参加这样的变化,却只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冷眼旁观,评头论足。我拒绝接受新事物,不要说是今天激动着千千万万从青年到老年的新的社会活动,就是新的文艺小说也从来不看,甚至连戏剧电影都要别人强迫去看。
我身上充满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霉烂的臭气和顽固的偏见,这样我就看不见也看不惯新事物。偶尔看到一首新诗、半篇散文、几段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不相信那里面所表现的新社会新人物的新感情,而对之投以轻视,我熟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里面的死人要比熟悉我眼前的活人为多。
社会是在飞速前进,群众是在飞速前进,而我的双脚却被坟墓中的死人拖住了,在骸骨之间徘徊迷恋。名义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成了一个没落阶级的遗少,心里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腐朽的思想使我睁着眼睛看不见我们的人民今天享有的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当我的这种腐朽的思想感情被触动的时候,我就以为是没有民主了,没有自由了。
只有到今天,到大家以大量的事实和道理来证明我的极端愚昧无知、落后反动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沦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
这三个月来,我第一次以憎恶的感情来看待我过去那么迷恋的一切,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来从头认识。(名义上说来)我也算曾出过一份力量参与缔造的新社会。
我曾经一直是这样一个为斯大林所说的“甲壳里的英雄”,然而我还有所追求。从我少年时代起,在封建教育的影响下,我的理想就是隆中待顾的诸葛亮,是扪虱剧说的王猛这样的人物,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平步登天”的道路。
到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大学教育以后,我的理想就自然地变成了像凯恩斯、拉斯基那样在我看来好像能够以自己的学术来左右国家政策的人物。我看不见群众,看不见集体的智慧,只崇拜个人,崇拜专家的钻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样热衷于议会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李慎之中国的道路 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https://pic.bilezu.com/upload/b/0b/b0b493d7106b9cf0b840d62d1bc6feb6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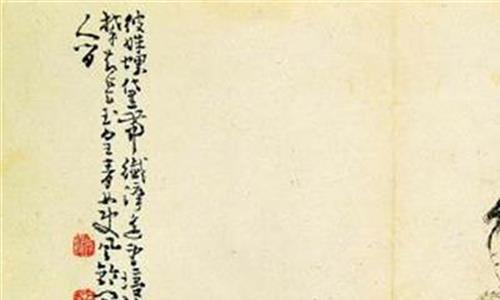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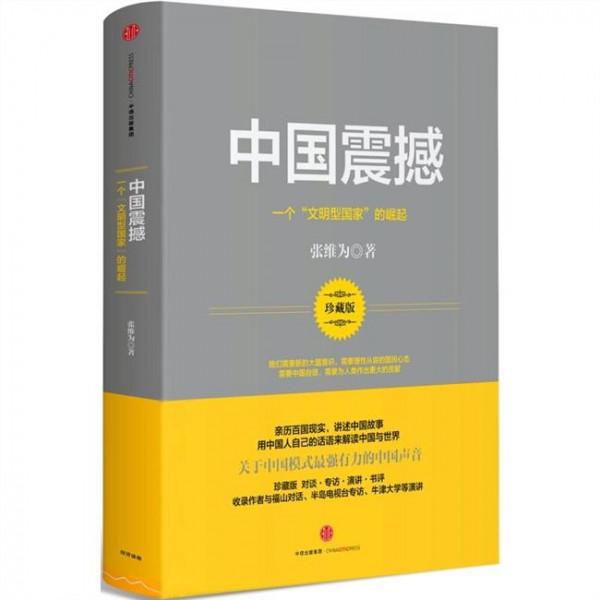



![>杨建荣上海科协 上海交大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仪式暨中国高校科协建设论坛举行[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1/52/152fc5b4fec385603b5433a7e330d31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