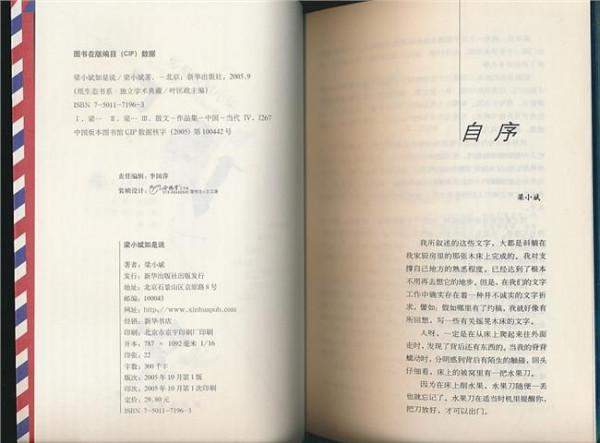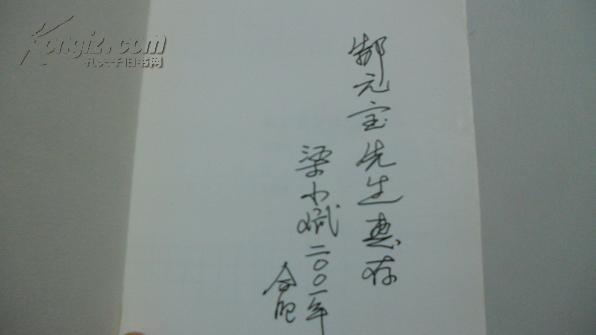梁小斌地洞日记 地洞笔记:被世界开除杭州日报
事实上,人的终结是被世界抛弃的,世界总与人的主观愿望相反,世界是活的,在于它善于发现你在世界的怀抱里并不老实。
语言,改变物体的位置。
人,从来就是从纹丝不动的姿态变为运动的姿态。被扭曲了的姿态,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姿态。
信仰,等待筐里的面包。因为我相信了他的话,因此得有相应的回报。因为信仰,我们离开了温暖的地方,朝向陌生地带,我们所有的所谓有目的行为,都是接受任务般地加以完成。如同儿童学习科学知识一样,1 1=2,对于孩子有何作用,完全是陌生化的感受。
教导是温和的,但是教导中的内容,却是冷冰冰的,这就说明,任何教育的内容必须是修饰成为温暖柔和的面貌而出现。但你长大了,温柔的面容从生硬的教育内容上移开,你难道单是以3个小白兔来代表数学概念吗?
我体会到贫困人的心态,他在有空调的房子里心里不得安定。于是,他回到了闷热、需要摇扇子的房子里。或者坐在外面乘凉,他心中毫无动荡。
哪怕是富有的人,他在舒适的地方居住,毫无不稳定感。但是富有的人,仍然有类似于贫困人的那种感受。只是,他们所忧郁的目标不同。所有人在退一步中,显得无限安详。因而,当我们获得某种幸福感或者稳定感时,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曾经是从哪里来。
而且,在那个地方曾经感到无限的困苦。我们有时隐瞒了我们某处很不成功这一弱点,如同很熟练的工作是从很不适应的工作中逃逸出来的道理一样,人,确实隐瞒了自己。因而任何一种幸福感和稳定感都是从某处逃脱的结果。
越是舒适,越是物质化的闪烁,越是有此时的欢悦,我们都体会到此光芒即将消失,有那么一种不会消失,你无须去奋斗,无须扭曲作态,即可获得的心灵平静。
识 别
你蜷缩在任何理论的地洞里,你必定被识别出来。我把画家用来当静物的苹果吃了。
任何终极理想,例如宗教中的以求正果,也如同要抓住的蟋蟀,与人的意愿相反,很难确实地得到。我将拂去尘念,尘念却经常打扰。我如果想在今世有幸福,我受欲望煎熬,却经常感到欲望却又渐渐消亡。
峰巅的灵光里如果有人在接受沐浴,灵光也会被弄脏,如同清水被弄脏的道理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遵循,只是偷偷摸摸躲在阳光里,太阳能够晒黑我们,但它并不承担晒黑我们的任务。它只晒黑有限的几个人,这也得有个前提,它并不知道,有人夹杂在阳光里,种子夹杂在风里。
掌握了人间正果的人得迅速离开正果。人,命里注定摆出了得到了真理的姿态,或者表现出精神的安详。就像怀中有武器的人,走路并不装张,大模大样的闲散心态,证明这个人怀中有术。得到正果后更彻底的伪饰在于显示出笨拙无能的心态。总之,或者显示出来,或者表现出来告诉我们他已得到。
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有尘念的人是否幸福呢?我们逃不出在追求幸福,让身心得到休息和安详的最终目的。尘念与信仰的关系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信仰,因为追求幸福的方法有些奇异,被多数人放弃了。
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时间,我们本身没有时间,我们寄生在他们的时间中。他们在忙别的事情,还没有忙完,所以暂时没有收拾你,所以你有时间忙自己的事情。譬如:这是太阳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这是妻子上班的时间,在她还没有回来之前,我可以忙些别的。我们说:“我有一段时间是自己的,其实已经想过了,这段时间内,有些什么情景还不会变化,于是就说有自己的时间。世界还没有醒来之前,我有自己的时间。”
一个稻谷成长的时间,我们不去碰它,悄然离开,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晨 霜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晨霜了。坏人如同晨霜一样,稍微去迟一点,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现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坏人,出现在一个晨霜凝重的早晨。
寻找思想的人,偶然碰上了什么现成的思想。实际上这个现成的思想在走它自己的思想之路。寻找思想的人,只能偷偷地抓住思想的绳索,不要惊动那个现成的思想;寻找思想的人,如果试图在那个现成的思想里出现,立即就会被重新丢到井里。
我们常说的沉浸在某种思想之中,还不如说我们躲藏在某种思想之中。把躲藏在思想中的杂质剔除出去,这就是指看上去僵死的思想却是活的,因为这个思想缔造者发现了有其他动机混杂其间。思想在活动,其要义是:剔除完了就不会再活动了,如同吃完饭了就不动了一样。
一个思想,为什么常常被我们拥有后抛弃,觉得这是过时的东西呢?
因为埋葬在思想其间的人躲藏得很深,至今没有惊动思想,这就是思想在沉睡的道理。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完毕的思想,就是一个沉睡的思想。按照思想在行动,按照房子怎么建的事先考虑在行动,还不如说在沉睡中行动。
有时,这个人也偶然睁开眼睛,看看谁妨碍了房子的修造,妨碍了人的思想沉睡。原来,有一根朽木混在木料之中。所谓活跃的思想也就是考虑如何把朽木从其间剔除出去,然后又进入沉睡般的思考之中,这就是敲击木鱼的时候了。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人的思想在发展”的叙述。思想在发展,似乎很像一棵树上结了许多果实,这是值得兴奋的事情。依我体会,除非你能完全掌握你的思想发展,否则,这个发展的思想如同底舱已经开始渗水的船,你得想办法离开你的思想。
思想家往往不愿离开他发展着的思想。主人牢牢地控制着仆人,仆人为主人忠实服务。思想家最好能够让自己的思想为自己的意图服务,但是,思想往往反抗思想家的意图。思想家对自己的思想成果很满意。
融化到此为止
被你一脚踢下河滩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块冥顽不化的冰。这块冰在大海上,像是一块白色的光斑。阳光对付它,根本用不着曝晒,周围的空气,还有暖暖的海水就可以使它逐渐缩小。阳光靠近一点看,这块冰在消失之前,可能会像一条鱼那样翻动,时而露出鱼肚白。但这块冰只能变黑,变得坚硬。这块冰在变小,它应该融化在水天一色的俗套诗意中。但是,偏不!原来,这冰块的内核是一块黑色石头。
上面刻着几个字:融化到此为止。
逃避生活
仅仅因为我害怕在黑暗中找不到座位,所以我很少看电影。我跟在步履矫健的朋友后面走,我终于觉得我不应该跟他们去舞场。我虽然也盼望学会跳舞,但一直没有勇气模仿别人的舞步,哪怕是偷偷地模仿的勇气也没有。我知道生活的情趣附在我身上,我就会感到沉重,总觉得身上有一股我不熟悉的气息。
凭着我的自然天性的萌发,我被染上那种陌生的气息也还能够走几步,但不久,就会感到失魂落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需要我具有能力,在黑暗里找座位就是本事。既然我没有能力,这个能力就变为我以外的怪物,时刻要吞噬我,我不小心就会被它吃掉。
我逃避生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没有办法克服我的胆怯心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我要学会克服障碍的问题,而是生活里所有的技能要压碎我,这个事实横在我面前。我读过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他们为了加入生活,拼命挖掘自己生命和意志的潜力。照这样的榜样,我也应该勇敢一点才对。但我想,我是一个在生命和意志上没有丝毫潜力可挖的人,我彻底地承认我的懦弱,为什么要羞于承认呢?
如果心理不胆怯,行为也就果敢了。但我细想,我的胆怯既然已经是先验的,那为什么非要让“勇敢”把胆怯挤跑呢?有些英雄少一条腿,有些英雄眼睛瞎了,他们想办法弥补生理的残缺就行了,而我的残缺,我的心理的变形是任何矫正术都无法使它恢复常态的。
生活如同女人
生活如同女人,她漂亮你就想接近,并且是不负责地接近。她丑陋你就想回避,离她越远越好。这是一个对生活的理论概括,实际情况是生活不论漂亮还是丑陋,你都要和她打交道。你命里注定是逃不掉的,这样就产生了无法逃避而派生出的人生观。
生活的形象给人以视觉的美感,这是美好信息,是人接近生活的首要前提。人如果脱离不了生活的制约,自然希望生活变得美好起来,这就是宗教。我的诗也曾经散布过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是一种期望,一种需求,一种自身无力的表现,但他至少还相信他的呼吁是值得的。
人的虚无的意识,就是欣赏生活的意识。人究竟要欣赏生活的什么呢?显然,人要欣赏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所谓文学是回忆,就是站在较为安全的地带,对无法介入过去的回顾。这样,人成为自我分裂的人,他首先在实际生活着,另外还要欣赏自己的处境。
挖地洞
我要在完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为自己挖个地洞。我被“深深掩埋”这个词所蕴藏的内容吸引。我深知,我现在是一个在偷偷摸摸挖地洞的人,这是我的精神氛围。
我要在完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为自己挖个地洞。我被“深深掩埋”这个词所蕴藏的内容吸引。
挖地洞掘出来的泥土如何处理,如何不至于在黑夜里传出掘土的响声,地洞的出口处蒙着一块可以推开的草皮,草皮上最好做一个沉重的脚印。挖地洞的时间要细细盘算,在别人以为我睡着时,我却是醒着的,并且在干活。
在外人面前,我还不能暴露出一丝一毫的疲倦之感。身上不得有任何泥土。因为长时间握锹把,手上如何才能不长硬茧,这也得考虑。最关键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在面部表情上显示出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要时刻装成流行的压抑的样子。
让自己不至于喜形于色,还比较容易做到,这到底还是浅层次的伪装。一个人的心灵要长久地沉浸在做一桩事的想法中,那么,我敷衍外界公事时,思想肯定要走神。所以,为防止万一走神,我还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走神”做注脚。我深知,我现在是一个在偷偷摸摸挖地洞的人,这是我的精神氛围。
■书边杂识
与这个世界对视
潘 宁
初读梁小斌,一个略嫌拗口的梁小斌出现在眼前——句子与句子之间似乎找不到必然的关联,就像跑错了地铁的出口,重新跑回来,也就是重新再把那些句子读上一遍二遍,出口才显现出来,一小方块的光亮,越向上走,所有的光线都向你涌来。
地洞笔记。
谁愿意躲在地洞里写作呢。
梁小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北岛顾城舒婷齐名的朦胧诗人,他写过一首绝不拗口的诗,从第一句开始就打通了所有黑暗的地道,光明,铿锵,没有死角。那首诗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那个时候,梁小斌丢失了钥匙,却在原野与大地上写诗与呐喊。
而今天,倘若他的钥匙已经找到,他也不需要了,他去地洞深处思考,写作,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而他似乎已经打开了大地的锁孔,大地之下,无边无际,那些无边无际正向他涌来。
沉寂多年,他以抗拒这个世界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地洞笔记》虽说是旧作重拾,但是,他为旧作取了一个犟头犟脑的副标题,“被世界开除”——一个被世界开除的人重返世界,还有比这样的归来更牛的么?
1984年,作为诗人的梁小斌被单位开除,打小工,打零工,靠朋友的资助,离开所有人的注视,在他自我认可的“地洞”之下写作与生活,这个被单位被世界开除的人,一个在现实中生活得很失败的人,反而将他的自我保存得相当完好。
去细读他那些不甚明了的拗口的文字,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诗人,将他的不肯驯服一笔笔刻进汉字里——有种就来读我啊,这个被世界开除的人在他的文字里傲慢地挑衅着我们,跟所有的庸常较劲。
被世界开除的另一层意思,是去年发生在诗人身上的一场更大的苦难。他再次受到关注,他因脑梗在北京紧急入院,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和社保医保,导致难以承受高额医疗费,经诗人叶匡政披露,“引发一场社会自救热潮”。
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梁小斌看上去已然苍老,才60岁,整个人显得克制而沉默。
他与这个世界相互打量,他们之间,默然而敏感,他们彼此对视,瞳仁因为过于执着而放大——这个看上去像是早已放弃整个世界的人,其实,他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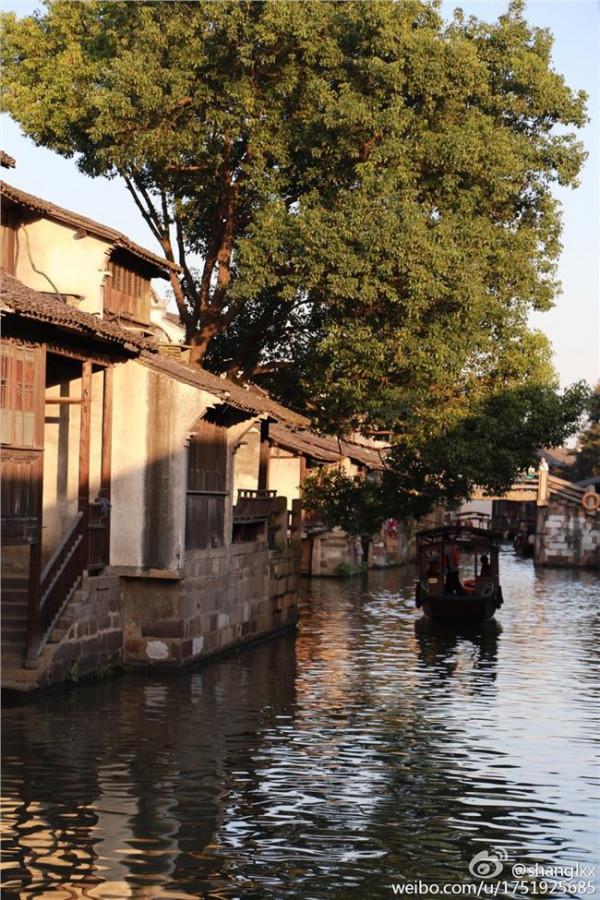














![[诗歌散文]梁小斌诗选](https://pic.bilezu.com/upload/6/63/663e1913e19e6ba2cc77638f3dee4a5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