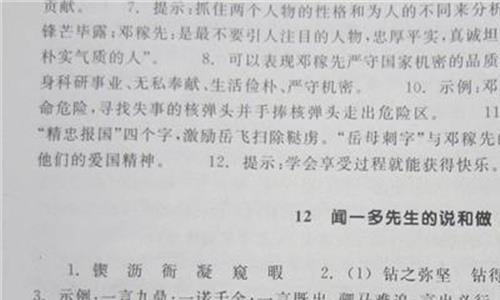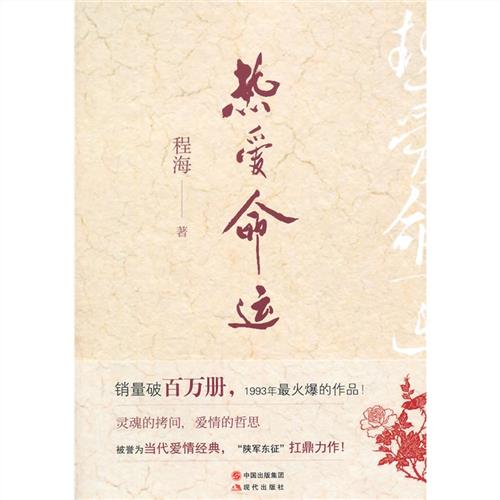闻一多中学 闻一多:在包办婚姻中收获爱情
“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
———闻一多
新婚:“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在闻一多才八九岁时两家便订下了娃娃亲。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

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
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在准备婚礼的过程里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 结婚那一天,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
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回到清华大学。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
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携手:“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诗人的怨愤叛逆的情绪宣泄完了,闻一多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在他的恳求下,闻的父母后来送高真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
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
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
”最后没钱时,高真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牺牲:“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
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