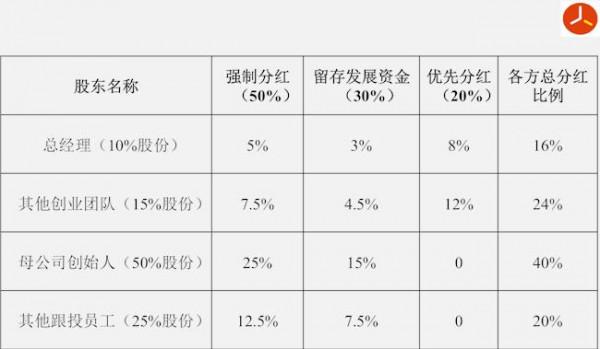邓晓芒为什么离开武大 邓晓芒详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如何开端
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通常的形式逻辑不同,因此有许多人否认他说的是逻辑,说他只是在谈形而上学、本体论。
其实在黑格尔看来,传统的形式逻辑才是不彻底的逻辑,因为这种逻辑把自己的开端问题交给了非逻辑的东西,如经验命题或自明的公理。

形式逻辑不管大前提,它的逻辑总是到某个大前提上就止步了,就让非逻辑的东西和大家公认的东西来作主,所以它的逻辑不是一贯的,而是片断地使用。
而一种逻辑却不肯一贯地使用它,这种做法本身是违背逻辑精神的。因为逻辑本身本应该是一贯的,按照古老的传统,逻各斯应当是“一”,是一贯到底的,不应当是断断续续的。

所以形式逻辑的开端总是还有待于论证的,这样的逻辑总是不彻底的。
真正的开端就应当是逻辑上一贯的,即由于开端本身的性质,它是绝对的,不再依赖于别的证明。它不以任何别的东西为根据,因此它本身“没有根据”,而是“直接的东西本身”。

当然,这种直接的东西不能有任何具体的内容,因为任何具体的内容都有待于证明,所以,开端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决心”。
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要讨论哲学,这个“要讨论”就是开端,它是不必讨论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讨论哲学,那也就没有哲学的问题,也就没有哲学的开端问题了。
这样一个开端甚至不是主观上设定的,而是客观上给予的,就是说,从客观上看,凡是想要谈哲学问题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种决心,要有一种能动性,要去追求,哲学思想不会自动地进入到你的心中来。
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上升到哲学,并不是不想,而是没有决心,他们以为反正什么都“说不清”,想又何益?
这种人与哲学无缘。黑格尔讲的决心并不是像费希特讲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笛卡尔的“我思”,而是哲学本身的自行开端,用不着哲学家去预设任何东西。它“没有任何前提”。
虽然黑格尔也承认,从哲学家个人的立场看,也可以把这个前提表述为“自我意识”或“我思”,但之所以能够这样,还是由于哲学本身客观上就是这样的,它不仅对张三李四这样,它对任何人、对万物都是这样。
因为哲学的对象是万物的本原,所以真正的开端不能仅仅满足于哲学家的自然意识,而必须从中把握到那种本原性的客观的东西。
不过,反过来看,这种进入哲学的态度或决心在哲学上虽然本身并没有任何前提,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却是发展出来、形成起来的」。
在意识的层面上,进入哲学就是进入“绝对知识”,这是在他的《》的最后阶段中所揭示出来的。
《精神现象学》他称之为“意识的经验科学”,它是进入真正的绝对知识即《逻辑学》的一个“梯子”。
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开端虽然在哲学的层面上没有任何前提,但在“意识的经验”上却是有前提的,即人要能意识到这个开端必须经历过漫长的历程,甚至经历了整个人类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发育史,到黑格尔才真正悟到了哲学的开端,才能下定决心从头开始地来探讨哲学。
所以,哲学的开端在他看来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思想几千年来奋力追求的结果。只是黑格尔自己尽量想掩盖这一点,当他通过精神现象学把人的思想引到他所提出的哲学开端以后,就试图把这个开端说成是天上掉下来的。
他达到了目的以后就把这个“梯子”撤掉了,就“过河拆桥”了,他以为他所说的这个思想就是一种“客观思想”了。
后来的人,包括他的一些弟子,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个“客观思想”、“客观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即上帝制定的,那你黑格尔又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
《精神现象学》并没有保证这一点,因为它只是意识的一种内在体验,而不能证明一种客观理念的存在。
马克思则指出,实际上,《精神现象学》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没有什么上帝,哲学的开端就在人类的历史中,在人类意识的发展中,开端“已经开端了”。
但如果承认这一点,黑格尔哲学的“绝对性”就荡然无存了,他就把自己的哲学放进历史过程中来考察,乃至于必须探讨哲学、自我意识和一切意识形态本身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形成机制。
而这是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不相容的。所以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他有一个突然的跳跃,他非得把《逻辑学》说成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便掩盖他的哲学体系在起点上的“缺口”,保证整个体系的封闭性。
但尽管如此,他的《逻辑学》开端中仍然保留有这种发展出来的能动性的痕迹,他也只要有这种痕迹就够了,就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
所以,当黑格尔说哲学的开端是一种“决心”时,他其实表达了一种能动性的思想,即你要探讨万物的本原,你就必须发挥你的主体能动性,必须投入你的自由意志。
只有自由意志是没有根据的,绝对的,无法论证的。万物的本原不会让你守株待兔地等来,而必须你自己去求得。
而最初求得的无非是这个“求”本身,即你要去求纯知识,但在开端时还只是“求知”的决心本身,还未获得任何具体的知识,因此在开端时还只是像苏格拉底所说的,“自知其无知”。
自知其无知本身是个悖论:一个无知的人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无知呢?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相反,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知识。
要知道自己无知,必须有了丰富的知识才做得到,他会觉得自己的那些知识比起知识的大海来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苏格拉底的意思还不只是这一层,而是说「自知其无知是真正知识的开端」,是对自己的无知的第一个超越。
黑格尔的意思也是这样,无知就是无知了,但知道自己无知,这本身就是第一个知识,就是纯粹知识的开端了,所以是“有知”。自知其无知确实是个悖论,因为有知的和无知的都是同一个主体,所以这种有知就是从无知中自我超越出来的。
如果无知是对“知”的否定的话,自知其无知就是对“无知”的否定之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不就是悖论吗?
苏格拉底自己也说过,如果是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怎么去寻求呢?我连我要寻求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寻求得到呢?
但如果我已经知道了的东西,我又不必去寻求了,我已经知道了还去寻求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的悖论”。
但如果从能动性来理解,它就不是什么悖论,而是一切认识的本质,其实也是一切运动的本质,一切自由意志的本质。认识就是要寻求那种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只有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才会去寻求;但如果我全知道了,我就不会去寻求了,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会去寻求。
当然,黑格尔从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中要引出的不是心理学的结论,而是客观本体论的结论,所以他引出“有知”以后,便把“知”这种意识层次的因素去掉了,隐藏起来了,而显露出了“有”这种本体论范畴。
他表明,虽然在我心中“有”和“知”是伴随着一起出现的,但“知”这种思维是被同一于“有”或存在之中的,“有本身”才是真正的最直接的开端。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有”就是一切知识、一切思维的前提,它通过认知的“决心”而出现,但它本身不依赖于主观思维,而是客观的“纯有”。
这种论证有些像的从思维推出存在,或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但这样推出的存在并不包含任何实际的内容,不像笛卡尔的“我在”或“上帝存在”成为了一个经验的事实,或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者,而只是一种空洞的决心,一种冲动,要深入自身、寻找自身,要开始“回忆”自己、挖掘自己的内容。
这样,这个开端就不是一个静止的端点,不是一个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动作、一个过程。
歌德在《浮士德》中写道,浮士德在翻译《圣经》时,把《约翰福音》中第一句“太初有道”挥笔改为“太初有为”:Der Anfang ist Tat,就是这个意思。“有”就是“有为”,“无”就是“无为”。这句话也译作:一开始是行动。
“有”、“存在”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在起来”的行动。
海德格尔也说,存在不同于存在者,存在应当理解为“去存在”的行动,应当看做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
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从黑格尔来的,所以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个范畴,一个开端的范畴,就是“有”,或者译作“存在”、“是”。
“存在”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词,很难把握它的意思。这个词来自希腊文 on,相应的拉丁文为esse,德文为Sein,英文为Being。
它本来是西方拼音文字中语法上的系词“是”,只是把语词和宾词联系起来的一个中介,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单独看它也有动词的含义,即“有”、“存在”,同时又还有名词的含义,如“本体”、“实体”和作为名词的“存在(者)”等等。
麻烦的是,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系词,主语和谓语的联系是通过语序来表示的,如说“伯夷叔齐者,古之贤人也”,也可以去掉“者……也”,单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而不说“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
“是”字在古代汉语中通常表示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这个”,如“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个是表示“正确”,如“是非”、“实事求是”。这两个意思与古代汉语中的“有”、“存”、“在”、“实体”毫不相干。
所以在翻译Being 这个词时,不论我们用动词“有”、“存在”还是用名词“实体”、“存在者”来译,它作为系词“是”的逻辑含义都被丢失了,而这个含义正是它最基本的含义。
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建议用“是”字来强行翻译这个词,但又把它的动词含义和名词含义损失掉了。
“是”字在现代汉语中固然已起到了一个系词的作用,但当它作系词用时就仅仅是系词而已,其他的含义都不具备,也不像在西方语法中那样可以表示时态。
所以直到今天,这个词的译法还是五花八门,就在同一个作者的同一文本甚至同一句话中,都不得不采用不同的译法来表达同一个词。
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中能够与这个词层次相当的只有一个词,那就是“有无之辨”的“有”。
但这个词与西方的Being 也只是在“存在”这一点上相交,它的其他含义如“具有”、“拥有”、“带有”则是西方的Being 所不具备的,西方人另外用have(英)和haben(德)来表达这个意思。
目前比较能够兼顾各方面的译法我以为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动词兼名词的双声词,拆开来单用一个“在”,也可以表达系词的部分含义。
当然还有一部分含义仍然表达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还是一词多译,加上注释来补救。我在讲课时多用“存在”和“有”,交替使用,有时也用“是”来强调它的系词意义。
在西方哲学中,on 或 Being 这个词正是从它的逻辑含义中、即系词含义中引出其动词含义的,因为西方人最初所理解的逻辑含义本身就具有动作的意思,系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联系的“动作”。
陈村富先生指出,希腊文on 的词根eimi 原来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系词的联结作用时也明确地说:
“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惟一的一个不能通过客观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己去完成的表象,因为它是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
这实际上就揭示出了逻辑底下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含义。西方的逻辑特别在早期,本身就具有本体论的含义,不像中国人理解的逻辑就只是一种嘴上功夫、一种“巧言善辩”的狡辩术。
所以,西方人其实并不是单凭逻辑思维就建立起了他们的ontology 的,要使逻辑上的系词on 成为最高的形而上学概念,还必须逻辑本身、包括on 本身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能动的超越力量。
海德格尔所谓与“在者”不同的“在”就是这种力量,即“在起来”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使一个逻辑上抽象的系词成为了“存在”或“本体”。
可见西方人之所以重视逻辑思维,根本说来是由于他们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重视个体自由精神,逻辑、语言被他们看做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的手段和方式。
而在语言中,“是”字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联系起来的关键动作,是一切命题、表述和言说的基础。
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想要存在就必须说,不说就不存在,懒得说就是懒得存在。“言论自由”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具有根本的存在论意义。
与此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语言学精神和逻辑精神,而这表明的正是缺乏个体自由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也就是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以来的现实,就是只有一个人能够“说”,其他人说了是不算数的,说了也白说,甚至是不准“乱说乱动”的。
所以黑格尔说“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惟一的一个人的说其实也没有“说出来”,而是隐藏得很深的,随时可以“虎变”,因而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悉心体会、细细揣摩和猜测,但却始终神秘莫测,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专制集权的高压之下,“说”是没有普遍性的,当权者自己可以口含天宪,朝令夕改,老百姓却只有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的份,只有被动的说,而无主动的说,也就不成其为说,于是就“懒得说”了。他们成了鲁迅说的“沉默的国民”,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所以在中国,语言根本不算一回事,更重要的并不是说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即使说了也要看是谁在说,而不在于说的内容。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历来没有把“是”字作为一个固定的联系词,这是因为在语言中说“是”或“不是”根本是无足轻重的。
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西方哲学的两大原则:“一条是:它是,它不能不是”;“另一条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
相反, 在中国人心目中通行的原则却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这里省掉了一个关键的主语:谁来“说你”?谁有资格“说你”?当然是“有权者”。
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时候,湖南的一位领导人对省广播局的副局长说:“你说你不是右派?我只要把干部群众叫来,让你往中间一站,你就是右派!”
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够坚持说自己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等等的人极少,因为说自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确实很难,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常常是生命的代价,不仅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是亲人的生命。
人们把这种人叫做“不会转弯”,也就是不灵活,不会指鹿为马,不会自我糟蹋、自打耳光。
可见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霸权话语”,话语只是霸权的工具,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不是自由言说的渠道,更不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
不依赖于某个权威的语言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价值的,语言的逻辑如果妨碍了权力的运行,则被弃之如敝屣,甚至越是逻辑上言之成理,越是被视为“妖言惑众”,必须“全民共诛之”。
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字和它所联结起来的语言既不是“本”,也不是“体”,而只能是“末”和“用”,即某种霸权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镇压异己的单纯政治工具。
在古希腊,巴门尼德以后讨论存在和非存在的话题多了起来,但直到柏拉图那里都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对“存在”的各个不同含义和层次未加区分。这也是存在,那也是存在,“红”是存在,“花”同样是存在,甚至“非存在”、“缺乏”也被看做一种“存在”。
亚里士多德对此非常不满,他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存在论”,首先必须对各种各样的“存在”加以清理,分清它们的层次,最后找到一个最根本的“作为存在的存在”。
但如何清理呢?显然不能凭内心体验。他是继承巴门尼德以来的逻各斯传统,以我们日常的说话方式标准来着手这件麻烦的工作的。
他认为,我们平常说话最基本、最常用的句子就是“S是P”,其中S是主词,它代表这个句子所表述的主体或“什么”;P则是谓词,它是这个句子中用来表述主词“怎样”的。
“怎样”和“什么”都是“存在”,但通常我们只有先了解了“什么”才能了解它“怎样”;“怎样”是依附于“什么”才得到了解的。所以这个“什么”就应该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第一存在”,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作“实体”。
“实体”的希腊文是Οντότητα,它与 Ον 即“存在”同字根,又译作“本体”。于是,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句子的逻辑结构的分析,给实体下了一个定义:
“实体,就其真正的、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
这个定义包含有两层意思:
一是“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这是一个纯粹逻辑上的规定,即实体必须是一个绝对的主词,而不能作其他主词的宾词。
显然,只有个别事物的“专名”如“苏格拉底”、“张三”、“赤兔马”等等才是这样的“第一实体”,而种、属、类,如“人”、“动物”等等虽然除了作宾词外也能作主词,但这种主词只能作为“第二实体”。
至于性质、动作、状态、时空等等则只能是宾词,即实体的属性或偶性了。
二是“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这是对个别实体的本体论方面的规定。
如“白色”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存在于个别事物如“苏格拉底”里面作为他的属性;但苏格拉底却不存在于任何别的事物里面,而是独立自存的、与其他个别事物相分离的。
可见,所谓“第一实体”就是指个别的东西,唯有个别的东西才是分离地独立存在的,也是一个命题中其他成分赖以生根的基础。
上述定义中的第二个规定可以看做第一个规定的根据,也就是说,本体论上的规定是逻辑学上的规定的根据。
为什么实体“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正是因为它“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而是本身独立存在的主体。
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和本体论共同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体现了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一种完美的结合。
其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从来都不是后世所谓的“形式逻辑”,而是与本体论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而作为系词的“是”在他那里总是具有时间的“存在”维度。
例如他的“实体”一词,他经常把它解释为 to ti en einai,英译通常作 What it was to be,里面包含一个过去时态,中文直译则为“某物曾经是什么”,吴寿彭译作“怎是”,意为一物是“怎么是起来的”,即它“原来”是什么。在拉丁文中该词组被简略地译作essentia,即“本质”。
这个词组最令人困惑的就是那个on的过去时,其实,如果从时间和实体的内在相关性来看,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亚里士多德所要寻求的是事物的第一实体,而唯有能够说明这事物“何以成为该事物”的东西才是第一实体,这就是它的“本质”。本质之所以是真正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因为它表明存在“原来是什么”。一个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就要看它原来是什么,即它是从什么中形成起来的。
我们通常把这个“什么”称之为这个事物的“原因”,也就是“原来”的那个“因”。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采用存在的“过去时”来表示“实体”的奥秘。
在德文中,“本质”即Wesen 这个词就是从“存在”即Sein 的过去时、也就是gewesen 变来的。所以黑格尔在谈到从存在论向本质论的过渡时也说:
“语言用存在(Sein)这个助动词,把本质(Wesen)保留在过去式‘曾经的存在’(Gewesen)里;因为本质是过去了的存在”。
尽管他说这并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而是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即本质是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但毕竟表明了“存在”这个“助动词”本身所埋藏着的本体论意义。
然而,不论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那里,“存在”的这种本体论意义同时都又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就亚里士多德而言,当他寻求事物“何以成为该事物”时,他列出了该事物的四种“原因”,即“四因”,包括质料因、形式因、致动因、目的因;而在这四种原因中,“终极”的原因就是“目的因”。
一个事物的“过去了的存在”即“本质”实际上就是它的在先的“目的”,即它原先想要成为的东西。
但目的虽然是“过去了的”,它却并不是消失了的,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的,因为一个事物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事物的实现过程中随时作为内在的驱动力而发生作用的“动机”;而在“实现了的目的”中,目的更加不是“消失了的”,而是以现实的方式存在着。
所以这个“过去了的存在”在整个过程中都随时“在场”。海德格尔后来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直接翻译作“在场性”,即Anwesenheit。
目的因与其他原因、例如和“致动因”的不同就在于,致动因总是在先的,其结果则总是跟随其后的,不可颠倒次序、“倒因为果”;而目的因则相反,最先的同时也就是最后实现的,最后出现的反而是最先起作用的。
亚里士多德说:“事物‘后于’发生过程的,在形式上与实体上是‘先于’,例如大人‘先于’小孩。”
小孩当然要长大成人,他后来终于长大成人了,但作为目的,小孩一生下来就已经包含大人在内了,所以长成大人就是小孩存在的根据,没有这个根据,小孩根本就不会存在。这个意思海德格尔后来发挥为“先行到将来”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以这种目的论的方式表达了实体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是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开端的存在概念的一把钥匙。
黑格尔的存在就是提出了一个目的,一个先行到将来的决心,但它现在还什么都没有,还未能实现出来,还有待于实现。
所以后来的范畴都是它的实现过程,直到最后一个范畴“绝对理念”,才是它的完全实现。
所以抽象地看,一切范畴都未逃出存在的手心,都是存在的某一个层次上的表达;但具体地看,存在范畴却越来越丰富,丰富到最后突破了逻辑范畴的形式而外化成了自然界。
要了解这样一个具体过程,请关注「哲学人公号」后续推送的「《逻辑学》开端的第一个三段式」,它生动地表达了存在本身的合目的性结构,形成了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最小构件或模板。
推荐阅读:
邓晓芒:不想当上帝的哲学家不是好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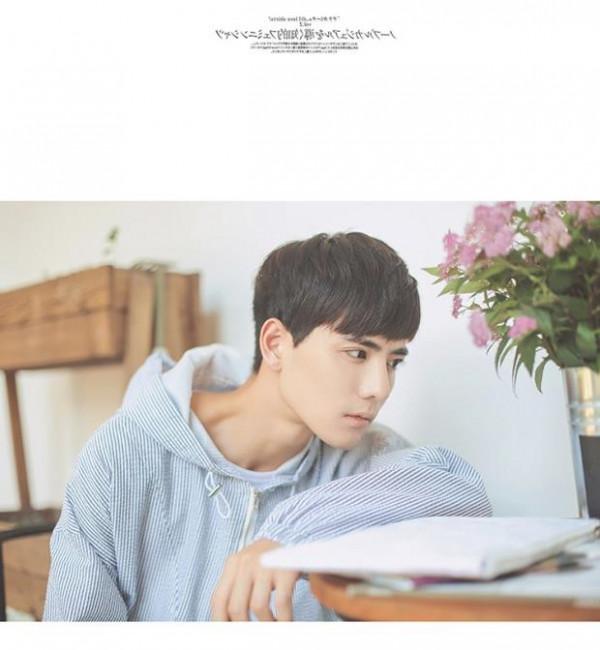



![>历史论坛:[原创]详解毛泽东的亲人们](https://pic.bilezu.com/upload/2/33/2335cfdf609a4c2b1db9d847ff0d2b9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