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评价邓晓芒 邓晓芒评陈嘉映和赵汀阳│思想者的随笔性格
思想的确是有性格的。当一个人把思想当作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或”副业”时,他的真正的“本我”就最真实地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尤其是那些不经意地、无拘无束地写出的文字中。所以有经验的读者想要真正了解一位思想家,就会热心地去读他的随笔或散论。

东方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思想散论”丛书,汇集了四位学者陈嘉映、倪梁康、孙周兴和赵汀阳先生的四本随笔集(因篇幅所限,本期“无处不哲学”只摘选文章中邓晓芒老师对陈嘉映和赵汀阳两位的评价介绍给大家),从这里,我们可以走近在他们自己的翻译和论著中以其成就和学识令人肃然起敬的思想者。

陈嘉映:随处可见的底层智慧
陈嘉映和我同属“文革-知青’的一代人,就从他的《冷风集》谈起吧。该书中的“摘自旅行人信札”部分,我读得特别仔细和投入。这是作者1981年为作研究生论文遍游南方大半个中国时所写的笔记和书信。我并不羡慕他游的那些名山古刹,我缺少他那种骚人墨客的思古幽情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我感到惊叹的只是他那么早就已经了悟到人生的真谛:

“悟得一切皆空抑或悟得万法若若,我总以为还是后一种悟性要来得更透彻一些”,
“了悟一切皆空的人,未始没有,但我们凡人,谁真能悟到一切皆空?更须一问的是,谁始终悟到一切皆空?若始终悟到,那还是悟吗?我们尚在贪生之时,干吗多讲求死之念?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是万法若若。但饿了仍不受嗟来之食,这也是万法若若。
最怕的是口说一切皆空,实则只把他人看空了,于是自己的生活反倒实得没有了转换的空间。生孩子过日子,就要说修道、作诗的是空;修道、作诗的,就要说常人的生活空洞。生孩子要好好生孩子,作诗要好好作诗,这就是万法若若了。”
显然,这段话直击禅宗六祖慧能的要害,炼成那锋利匕首的无非“始终”二字。历来讲“顿悟”的人,都回避这两个字。连鲁迅都说,人最怕的不是醒来,而是醒来以后无路可走。“顿悟”了“以后”做什么?这是最要命的问题。
嘉映那时正研究海德格尔,也许正是海氏的“时间”概念给他提供了走出禅宗陷阱的线索。顿悟以后还有时间,还有生命,还有未来。只要人活着,未来就不可知,你怎么知道未来仍然是一切皆空,而不会“无中生有”,不会产生奇迹呢?除非你现在就死。
但死了也就谈不上思想,更不可能“了悟”什么了。既如此,就没有什么“顿悟”,只有冒死而活着、冒险而创造的生命过程。这实在是一种很“硬”的思想。“海德格尔说,人生存在未来中。这种人恐怕太坚强了。
那么,沉湎于往事的心灵,诚是些柔弱的心灵!这段惆怅不去,就永远是个孩子。”嘉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写的《初识哲学》中回顾当年:“那个坚冷的年代,的确要求心里有某种坚冷的东西和它对抗”。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说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温柔的年代”,不再需要那种“坚冷”’了。
嘉映是以翻译和研究海德格尔著称的。现今弄“海学”的人不少,往往一开口就是反理性、反科学、反逻辑,就是诗化语言和后现代。但嘉映没有这种毛病。要说“诗化”,他是很有本钱的,他的文字朗朗上口,诗意盎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顶尖级的文体家。
但同时他的表述极其清晰明白,决无装神弄鬼,倒不乏下层百姓的直截了当和机智。这除了显出他曾受到英美日常语言学派和分析哲学影响的痕迹外,也许与他质朴的性格及长期的底层生活有关。
他治海德格尔哲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力图使海德格尔回到常识,回到平常人的生存智慧。而常识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日常的理性。“人讲道理,人有理性,而道理和理性把人引向间接的生存……人失去了一部分直接性,这也许是一件让人叹息不止的事情。
但这是人的宿命。”“自从人有了语言,自从人生产工具,我们就开始通过中介和世界打交道了”;“理性和科学不是一切。为了防止科学主义统治我们的生活,我们绝对有必要认清事实和论证的局限,从而能有效地发扬科学精神,坚守理性。
相反,用非理性冒充讲道理,用作伪掩盖事实,不但不能减轻科学主义的统治,反而与科学主义联手加深了这种统治。”所以嘉映不但批评“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对抗科学主义,实质上却在与科学主义“共谋”,而且对人们津津乐道的海德格尔后期思想颇不以为然。
书中最后十来页讨论了“海德格尔语言思考的一些疑点”,提出了八点质疑。据我看,这八点最基本的是两点,即:一、“既然明知道独特的东西是讲不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保留在心里,而非要尝试把它讲出来”?二、“离开了概念语言,思究竟还有没有自已独立的言说方式”?这两点实际上就是维特根施坦的原则:把凡是(用概念语言)能说的都说完,对不可说的则应保持沉默。
与维特根施坦不同的是,嘉映在这两点的基础上还归结到第三点:三、“海德格尔再三声称,存在需要人,语言需要人,但是在他的思想脉络里,我们始终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因为他始终不去留意‘世界的’或‘世俗的’语言具有何种建设性的意义”。
“如果语言自己就会说话,我们就不知我们凡人能对语言做出何种贡献。
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之言那样自足,我们简直看不出为什么还需要人的言说,哪怕是诗人的言说”。这就是说,嘉映的根本视角还是不那么时髦的“人学”、“人本主义”,以及由于坚持人本主义而坚守理性的基本立场。
我们之所以非要把不可言说的东西说出来,并非因为某种(如维特根施坦所言)语言运用的错误,而是因为我们是人,是“理性的动物”或“说话的动物”,只有说出来我们才“存在”。“概念语言,虽然不能概括“诗”的语言,但无疑诗也不能完全取代思的概念。
海德格尔自己虽然也作诗,但毕竟只是偶尔为之,他的大童作品仍然是概念语言。更何况诗所借重的语言本身根本说来无一不是概念,即一种与世界打交道的作为“中介”的符号。诗的直接性是以语言的间接性为前提的,而间接性是人的“宿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不过我这样说也许就对嘉映解释过头了,赶紧打住。
赵汀阳:哲学家…
四人之中,惟有赵汀阳的《长话短说》在“作者简介”中标明:“赵汀阳,哲学家……”他的这本文集也的确有大家气派,不像前面三人的书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专业是哪个方向。在才气方面他似乎也超过前三人,往往会有一些令人击节的佳句。
如“心学和佛学一样强调内心领悟,但远不如佛学圆满,关键在于,佛学拒绝了俗世观念,因此开放了虽然不清楚但却天宽地阔的体会,而心学固执于一些特定的俗世要求,就很难想象和证明为什么自由广阔的心灵非产生儒家的世俗要求而不是别的世俗要求。
”真是聪明绝顶!又如谈到白话文为什么成功:“现代白话文的成功建立在古典白话和西方科学—逻辑表达方式的顺利结合上,而它们能够顺利结合则是因为科学—逻辑表达方式就其本性而言是可以普遍转达的语言方式”。
这种解释似乎还没有人说过。再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创造出新思想,就甚至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传统思想。这在吸收西方思想方面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思想,我们拿什么去‘吸’别人的优点呢?”太对了!
我想这也是汀阳做哲学一贯的宗旨,他的有些书就是一个注释也没有,全部都是从他的头脑里凭聪明和天分创造出来的新思想,然后用这些新思想去“吸”古今中外的一切东西。所以他反复说:“一个人或者本来就是或者永远不是哲学家。”不过对此我总还有一点疑惑。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哲学家。就我来说,20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也从来不以为自己能够搞理论。只是后来看的书多了,做了无数的笔记,才想起自己是不是也来写一点什么。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还只是:我正在从事哲学工作,至于我自以为创新的那些思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前人早己经说过了,至少是想到过了。
世上的聪明人大大地有,人脑的发达两千年来基本上没有进展。即使“本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也只有拼命努力去吃透别的聪明人的东西,才能成为自己“本来就是”的人,甚至才能知道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
所有的哲学家思考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因此一个哲学家如果真正“吃透”了另一个哲学家的东西,以至于比另一个哲学家更好地理解他自己,那么这个哲学家就创造出了不同于另一个哲学家的自己的哲学,这样反过来我就可以说。
我之所以能够“吃透”另一个哲学家的东西,正是因为我创造出了自己的哲学。汀阳说的没错,但他只说了一面。任何事情偏于一面是要翻船的。
汀阳的毛病就在于把自己的天才看作一个固定的点,只用来“吸”别人的东西而从不被别人的东西所“吸”,结果吸来吸去,只吸到了自己对别人东西的一些“猜想”。例如对西方社会契约的“猜想”:“人们最感兴趣的恐怕是制造一种例外的利益,即建立‘一种以平等为基本精神的社会契约来保证基本安全和利益,同时设法使自己获得非法或例外的不平等优势。
”这就完全是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去利用人家的信义大捞油水的心态了(如有位大学教授在美国一年内免费开了好几辆崭新的车,每次都是在三个月试用期满之前退掉,又换开一辆)。
又如把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解释为“他人的肉体是重要的,精神就算了。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主体性原则和个人主义、普遍主义、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等在逻辑上并不矛盾。
”按照这种“逻辑”,其实他还可以说,西方人权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思想霸权主义(思想专制)也“并不矛盾”,如果“现代西方观念”要克服其“根本局限”的话,就得把一种奴役人的思想也视为“同等级别的真理”。
汀阳特别厌恶“普遍主义”,说“普遍主义是最坏的思维方式,它的齐一化和标准化正是对思想生态的根本破坏”。但我想他肯定不会反对“普遍的自由”,而去主张一些人自由、另一些人不自由的“人吃人”的“生态”。其实,反对“一切”普遍主义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普遍主义”了,是最坏的“齐一化和标准化”,不知道聪明如汀阳,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
至于汀阳白己的哲学思想,我这里不可能作出全面评估。从这本书中看,他有时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如他说“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是那些能够造成‘实践性’事实的思想观念”,“精神必须能够变成物质,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历史,而物质化了的历史才是决定未来存在面貌的一个因素。
”他发明了类似这样玄妙的句子:“哲学必须成为语言的引诱者而不是被引诱者”。这话要用普通人的话说出来会干瘪无味,无非是说哲学要立足于事实说话,对语言要“听其言观其行”。
他有时斥责哲学只不过是“脱离生活”的“大话”或“胡话”,似乎他从此不打算搞哲学了。但有时他又把“大话”加上引号,说这是“有意思的‘人话’”,还说古典哲学是“关于世界的胡说”,现代哲学是关于“思想的胡说”。
这时贬义词全都成了褒义词,有些像王朔说“我是流氓”,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在贬自己,他得意着呐。也正是出于这种两面讨好的立场,他有时说“想象的东西虽美,可是不切实际”,可有时又说“我们需要想象力”,甚至说“各种荒谬的想法、一厢情愿的白日梦和放纵的想象,都应该有同等的学术权利”(而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因为“所谓文化的美学品性,就是它那种能够提供不可还原的想象和感动的方式”。
他由此在唯物主义的效用标准上加上了审美标准,认为“实际上只需要最诚实的直观和推理,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对生活的根本期望是一种美学的期望,因为好的生活需要生活能够产生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尤其是意料不到的感动,可以说,存在就是被感动。
”这才是“真诚对待生活的意义”。可是,用“美学的眼光”真能“更为宽容”地“超越许多思维障碍或局限性,特别是能够克服由于陌生感而引起的对他者文化的恐惧和抵制”吗?若如此,每个不同审美趣味的人(包括菲律宾的“猎头族”〕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语言的“引诱”了。
顺便说,汀阳有些哲学思想之所以显得很新,只是由于他还没有来得及用它去“吸”人家的思想。例如,他1995年开始写《一个或所有问题》,认为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之间的循环关联是他自己的一个突发的“灵感”,其实这不过是所谓“解释学的循环”的老问题,西方哲学已经讨论一百多年了。
又如他的另一个“从艺术家的工作方式那里获得”的“灵感”:要建立“以动词为核心的思维”而不是名词思维。但如果我们读过海德格尔的书,将其与胡塞尔的“名称论”比较一下,也不难见出这一差异。
何况恩格斯早已指出,欧洲一切语言中的名词都是由动词变来的。再如他主张把“应该”从伦理学中排除,只考虑“怎么做”,并称这种“做人主义”是一种“新思路”即“新目的论”。
他说:“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而不是表态和劝世。什么是好或者坏大家都明晰,真正费力的事情是怎样处理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但这种“新思路”在两千年前就由苏格拉底提出来了(他为此而送了命),所以苏格拉底才说“知识即美德”,也就是要寻求一种使人人都懂得的“善”能真正实现出来的“技术”(关于善的知识)。
当然,汀阳有时也会碰上一些真正“新”的灵感,只是一般人若没有他那样的才气,最好不要去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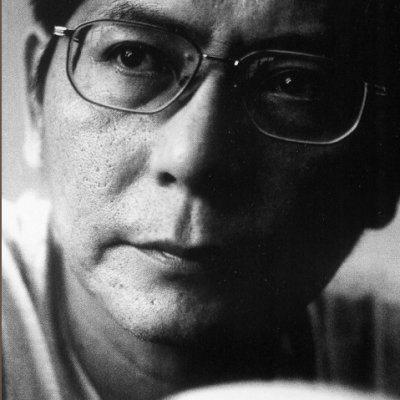

![>陈嘉映]陈嘉映 周国平](https://pic.bilezu.com/upload/0/72/0725457507eb935c5e97395ded42714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