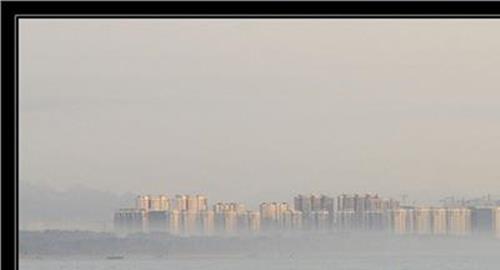万箭穿心电影解析 城市文化的光影交汇: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解析
电影,作为科技与艺术的结晶,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馆”放映了《火车进站》等短片,标志着西方电影的诞生。1896年8月11日,“西洋影戏”第一次在上海徐园内的“第一村”放映,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起源。可见,中西方电影都起源于现代城市,都在城市里获得发展,都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张英进在论述中国电影的起源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时说道:“一方面,城市不仅为电影这一西方技术文化在中国的引进、扎根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而且城市也迅速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另一方面,电影的普及与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城市文化的结构,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城市观念。”[1]

随着电影研究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市电影,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陆绍阳在《新城市电影影像特征》一文中指出:“城市生活最能呈现当代人的精神内核,是电影挖掘的重要‘?鲇颉?,城市电影是以当代城市生活空间为叙事空间,表现人与人、个性自由与制约个性发展的外部条件之间冲突的影片。

”[2] 从这样的界定来看,《万箭穿心》可以被称作为一部城市电影,透过这部电影,我们对电影故事发生地的城市文化能有所认知。
一、电影《万箭穿心》的地域空间建构
2012年底上映的电影《万箭穿心》改编自湖北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是20世纪90年代的武汉,主人公李宝莉下岗之后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适逢李宝莉的丈夫马学武所在单位分福利房,李宝莉一家搬进了新居。

然而,新居位于数条街道的交汇处,风水上称之为“万箭穿心”。李宝莉偏不信这一套,她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然而事与愿违,搬进新居并没有给李宝莉的生活带来新的快乐和幸福,反而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以至于她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改变。
丈夫马学武对她日益疏远,进而发展到出轨,在事情败露后马学武先被降职后又遭遇下岗,对家庭和人生彻底失去希望的马学武跳江自杀了。为了挣钱养家,李宝莉毅然去汉正街做了一名“女扁担”。十年后,儿子小宝考上大学,就在李宝莉以为苦尽甘来的时候,小宝却痛斥她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对李宝莉满腹怨恨的小宝决意与她断绝母子关系并将她逐出家门。
《万箭穿心》的故事从头至尾都发生在城市,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城市――武汉。在电影中,城市文化的空间建构通常包括社区空间和家庭空间,最能体现社区空间的是街道。“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体现了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特征,也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主要空间特征之一。
街道上流动的人群,面貌不同,身份各异,行色匆匆,互不相识,在游动中擦肩而过,并以此呈现街道两边橱窗式的建筑/商业/文化景观。”[3]32 街道作为现代城市典型的空间形象,在《万箭穿心》中多次出现,但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武汉有名的一条商业街――汉正街。
汉正街是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的一条商业街,以批发和零售各类商品闻名全国。20世纪90年代是汉正街商业繁荣的鼎盛期,每天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商贩云集于此,造就了汉正街当年的繁荣和辉煌。
林立的商铺、琳琅满目的商品、摩肩接踵的行人,电影《万箭穿心》真实地还原了汉正街当年的历史风貌。拥挤、嘈杂的汉正街是码头城市武汉的一个缩影,凌乱、繁忙却又充满生机,汉正街以及汉正街上生活劳作的人们一同凸显了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
电影用影像纪录了汉正街的时代变迁以及变迁中的各色人等,街道与街道上的人们体现着城市文化的发展,以及被城市文化的演变所裹挟的人生日常。
在电影《万箭穿心》中,城市文化的家庭空间建构主要体现在女主人公李宝莉的家中。因为赶上丈夫单位福利分房,李宝莉一家搬进了新家,在这个新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长江,这是武汉人非常引以为荣的事情。同时,在阳台上往外看,也会看到多条街道汇集于此,形成风水上所谓的“万箭穿心”。
住上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电梯房让李宝莉陡增一种幸福感和高贵感。然而,她的幸福很快就被痛苦所取代。餐桌是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和谐的地方,可是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一家从来就没有开开心心地吃过一顿饭。
丈夫马学武长期受到李宝莉的压制,在饭桌上总是保持沉默。马学武出轨之后,李宝莉经常借用吃饭的机会对马学武含沙射影,冷嘲热讽,家庭氛围日趋紧张。
马学武自杀后,李宝莉的婆婆掌握了家庭的话语权。饭桌上的交流仅限于李宝莉对小宝作业完成情况的过问以及李宝莉每天向婆婆上交自己一天的劳动所得。这样的家庭生活单一、乏味、沉闷,缺乏正常家庭应有的融洽、温情和温暖。影片中偏暗的室内环境以及清冷的色调控制呈现了家庭空间的压抑和冰冷,这样的家庭空间已经丧失了为人的灵魂和精神提供休养和补给的功能,仅仅只是人们用来安放身体的栖身之所。
二、电影《万箭穿心》中人物的身份焦虑
《万箭穿心》里面的人物不多,但他们都经历了身份的迷失和转换,这些变化是随着人物的生存处境变化而变化的。李宝莉虽然是城里人,但其出身低微,没有读过多少书,这使她年轻时对知识分子很景仰,她后来如愿地嫁给了从外地考进城里的“文化人”马学武。
但中国社会多年来的城乡观念又使得李宝莉在马学武面前有一种“城里人”的优越感。“城里人”的身份使她在婚姻生活中占据着心理上的高地,对马学武的颐指气使成了家常便饭。面对强悍、跋扈的妻子,“乡下人”马学武选择了忍气吞声。
唯一能让马学武在家里感觉到温暖的是儿子小宝对他的依赖和信任,只有为人父亲的身份还能让马学武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一丝尊严。随着马学武职位的提升,马学武的“身份”终于有所改变,他对李宝莉不再逆来顺受,而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抗争――婚外恋。
有一天,李宝莉跟踪马学武,发现马学武和一个女人在旅馆幽会后,极端的愤怒使李宝莉做出了一个有悖常理的举动,她打电话报了警。失去理智的李宝莉忘记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她的身份由妻子变成了旁观者,正是这一瞬间的身份转换给她的家庭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灾难。
“家丑”外扬后,马学武从厂办主任被降回车间继续做技术员,在家要忍受妻子的冷嘲热讽,在外要面对工友的揶揄嘲弄,马学武度日如年,精神一蹶不振。
随后,马学武的单位进行人事改革,因为“作风”问题,马学武首当其冲被精简了。从春风得意的厂办主任降为技术员,又从技术员变成下岗员工,马学武的社会身份不断被降格。
当马学武得知电话报警的女人就是每天同床共枕的妻子李宝莉时,马学武完全陷入了绝望。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已经无处安放,马学武最后跳了江,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份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李宝莉辞去了在汉正街帮人买袜子的工作,毅然决然地做了一名“扁担”。买袜子虽然也是收入不高,但在李宝莉看来,至少比做“扁担”体面一些。从片中她对“女扁担”荷嫂的怜悯和照顾可以看出,她在“扁担”面前还是有一点优越感的,就像她曾经在马学武面前有优越感一样,可如今为生活所迫的她也“沦落”成一名在街边等活、与其他“扁担”抢活、看雇主脸色的“扁担”了。
放下身段的李宝莉凭借她的爽快、泼辣和勤劳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角色,在汉正街,不熟悉李宝莉的人根本看不出她是城里人,她不修边幅、面色粗粝、风风火火,每天累得回家就躺倒,完全无暇顾及小宝的学习和生活,她作为“母亲”的身份,在小宝的成长岁月中渐渐离场。
李宝莉的离场让曾经看她眼色行事的婆婆逐渐占据了家庭生活的主动,进而掌握了家庭的话语权。婆婆提出让李宝莉将房产证上她的名字改成小宝的名字,以此剥夺她的财产权。在小宝高考前夕,婆婆竟然以李宝莉在家影响小宝心情为由将李宝莉打发出门。
对这些无理要求,李宝莉都忍了,也都认了,在她看来,只要是为儿子好,任何牺牲都值得。“母亲”的身份是她前行的勇气和动力,支撑着她继续为她的家庭打拼奋斗,可惜她的希望被小宝无情地击碎了。
小宝考上大学后提出和李宝莉断绝母子关系,并示意她搬出房子。小宝的话令李宝莉痛不欲生,李宝莉坐在江边想了一整夜。和马学武不同,她是一个会自我开导的人,她终于想通了。
第二天,李宝莉回到家,生平第一次给自己当了一回“扁担”。她挑着行李,没有给小宝留下一句话,平静地离开了十几年来用心血支撑起来的家。李宝莉的黯然离去意味着她放弃了“母亲”和“儿媳”的身份,但她没有放弃作为“人”的身份,只要这个身份还存在,她就有理由继续生活下去。
随着剧情的发展,除了李宝莉和马学武的身份遭遇变换与困惑外,剧中其他人物的身份也经历了某些变化和困惑。建建在电影出场的时候是一名街头混混,是李宝莉熟识的街坊邻居,因为打架事件,建建被判刑入狱。十年后,建建与李宝莉在街头重逢。
一来二往,在一次半强迫半自愿的情况下,他们突破了男女之间的防线。李宝莉后来在街上碰到建建时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让建建颇感诧异,他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虽然后来他们同居了,但李宝莉和建建是否是情人关系一直让人疑惑。
同是底层人物,他们之间没有卿卿我我,只有相互取暖。电影并没有展现他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在一起似乎只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即便在电影结尾,建建开车接走了无家可归的李宝莉,观众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谁知道李宝莉的后半生是否就从此安稳和幸福了呢?建建和李宝莉的关系的模糊界定给观众以思考的空间,真实地反映了都市男女在面临生活和情感时的身份困惑。
片中李宝莉的闺蜜万小景的身份也经历了迷失和困惑。万小景嫁?o了一个有钱的男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并不幸福,因为她经常遭遇丈夫的背叛和家暴。这个男人从未在电影中出现过,但他却时时左右着万小景的喜怒哀乐,控制着万小景的人生。
作为妻子,万小景对她的丈夫充满了厌恶和憎恨,但她又不愿意离开他,因为她在经济上依附于这个男人。万小景的悲哀在于她放弃了独立女性的身份,一味地屈从和依附一个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卑贱地靠着男人的施舍活着,她的尊严和幸福遗失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中。
三、电影《万箭穿心》中的城市方言
纵观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以及21世纪的《天下无贼》、《手机》、《疯狂的石头》、《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等电影,不难发现,这些电影都包含了方言元素。近年来,方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辅助性语言,在电影中的分量和作用日益明显,其价值也越来越受到电影人的重视。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言,可以通过对“方言及其他形式加以重视,重新挖掘本土文化,并将多种文化不分高低地呈现出来”。
[4] 方言在电影中出现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电影对白采用普通话,只是在普通话的语言背景下带有一些方言词汇和语调。另一种是演员对白采用纯方言形式即使用方言词汇和方言语调。第二种形式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部分演员使用方言对白,另一种是所有演员使用方言对白。
《万箭穿心》属于第二种方言电影中的后者,在电影《万箭穿心》中,所有演员都讲一口武汉方言。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它传承千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某一地方的方言最能体现该地区的文化特色。
武汉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它直接明快、生动诙谐,能充分体现武汉人豪爽火爆与侠肝义胆、热情耿直又机敏利落的个性。在电影中,武汉方言对刻画人物形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电影《万箭穿心》开始不久,在一个炎热的天气里,李宝莉请搬家工人搬家,丈夫看到工人们很辛苦,递了几只烟给工人抽,这个在常人看来合情合理的举动却引起李宝莉的强烈不满,她跑过来一把夺过马学武手中的烟,对马学武一通斥责:“马学武,我出钱他们做事,天经地义。
刚才在那边坐地涨价你怂倒,现在你跑出来发烟,你自己看一下他们做的是么事。烟不要钱?汽水不要钱?你当是在厂里搞招待?生得贱!”用武汉方言说出这番话,李宝莉泼辣强悍的性格顿时活灵活现地显露了出来。
在马学武跳江自杀后,坚强的李宝莉没有流一滴眼泪,她对闺蜜万小景说了一句:“我不得叫我的屋散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宝莉的坚韧倔强与勇于担当。和很多武汉女人一样,李宝莉虽然在家里对丈夫颐指气使,但她的心思都放在家庭里,当她的家庭遭遇变故时,李宝莉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得更勇猛,她用不屈不挠的精神撑起一个家。
讲着武汉方言的李宝莉让观众觉得这样的武汉女人鲜活、真实。
除了刻画人物形象之外,方言还以其丰富的词汇和独特的语调传承和宣扬着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在《万箭穿心》中,剧中每一个角色都说的是武汉方言,观众透过他们口中的方言俚语能近距离地了解武汉独特的地域文化,进一步体悟到武汉独特的社会民生和风土人情。
“当代电影中的方言是一个牵涉到地域、文化、历史、人类等诸多方面的课题,在表现上有着巨大的表现力。”[5] 随着近年来方言电影的增多,对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将得到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 四、?Y语
电影《万箭穿心》虽然是在武汉全景拍摄,但电影并不是简单地再现武汉的城市面貌。“电影中的城市,并不是现实中城市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因为究其本质,电影所建构的空间是由一种由二度平面形成的空间幻觉,是一种想象的产物。
”[3]30 电影对于城市空间的建构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建构,更多地是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建构。借助城市电影这一载体,创作者往往意在展现现代城市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以揭示社会变革中现代城市人的困惑与顿悟、迷失与寻觅、迷惘与坚守、焦虑与从容、绝望与重生以及痛楚与欢欣。城市电影的创作者应该去“体验、挖掘、表现城市人的精神症候,在文化认识方面重新建构城市和城市电影的意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