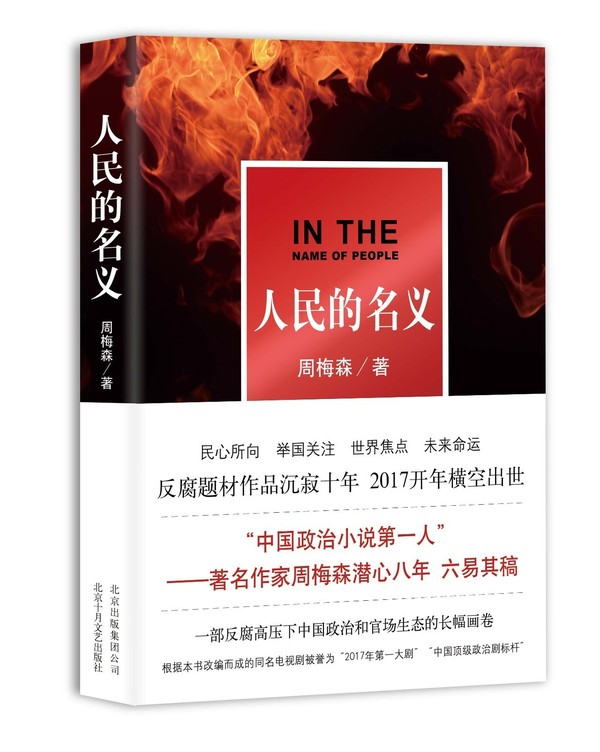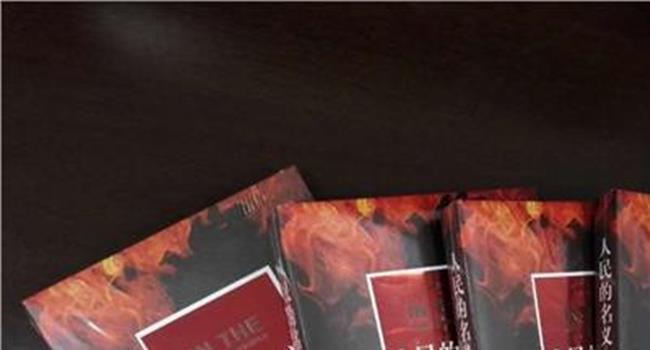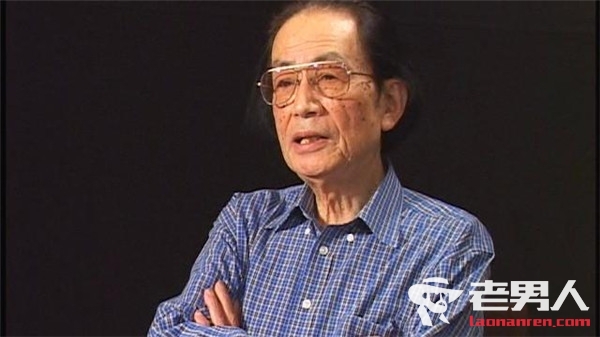陆天明作品集 独家专访著名编剧陆天明:当代反腐题材作品要深入思考人性
南方日报:您认为,《人民的名义》与十几年前的反腐剧作相比,有哪些进步之处?
陆天明:毫无疑问,《人民的名义》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但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写自己的作品。我不敢看别人的东西。所以不好做具体评价。但从种种反应来看,这部剧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和启迪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和人民大众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地,又合法地说真话,社会就取得了真正的进步。
人民不能仅仅被别人以他的名义来说话,而要能自己站出来说话。这里头包括作家和艺术家,而不是被允许说一点真话的时候才能出来说点真话。反腐也是如此,要让人民得到这样的可能,直接依法参与反腐,真正地发挥主人翁精神和监督干部的作用。而不只是让别人用他们的名义来反腐。
具体到艺术创作上,我认为如今反腐剧的创作要跳出多年来一直在沿用的老套路:靠在一个行业上面,树一个清官,破一个案子,抓一个贪官的。反腐题材的创作也不可能再在贪官的级别和所谓的大尺度上下“赌注”,而是要慎重考虑中国的反腐怎么才能深入,如何才能构筑出一条“钢铁长城”,把贪官挡在我们队伍门外?我认为,关键是要靠法律靠人民。
南方日报:现实剧作特别是反腐题材,特别讲究讲故事的技巧。对于如何把握好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尺度,您有哪些心得和思考?
陆天明:依我看,写反腐题材作品一定要把握好几点:首先,不要回避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在体制下进行写作,必须要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确实仍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它正在被完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政党,是热爱人民、以为人民谋利为宗旨的党,有自纠自治的决心和能力。创作者在创作中,一定要充分显示出这一点,要对体制有信心,要反映体制的本质,不要被腐败官员和一部分阴暗的东西迷住了双眼。
其次,要把握好“反腐”和“腐败”之间的区别。我们写这个题材是为了反腐,而不是为了更腐。所以就一定要在作品中避免蓄意展览腐败,更不能把玩腐败,售卖腐败。更不能蓄意展览腐败去消蚀党和人民大众反腐的信心。创作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反腐这个“反”字上,深入探讨怎么反腐能反得更好。
这两个基本点把住,从艺术创作上,我们要探索新的形式,不要把反腐戏仅仅写成破案戏。破案戏永远可以写。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把反腐戏“推陈出新”,就像俄罗斯战争文学,如今到了第四代,战争戏已经不着重表现战场上子弹横飞、血肉拼杀的场面了,而是着重表现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怎么捍卫人和人性的尊严,怎么维护人与人的爱。
反腐题材也是如此,如果仅仅写贪官用权力谋了多少私利,这是浅层次的。当今的腐败带给人的变化,不仅仅是贪欲,而是特殊权利导致了人性的变化。
人发生了变化他带来的是民族忧患。比如,现在的腐败不再只是官的腐败了,我在《高纬度战栗》里写到的是民族质感的变异。每个的人变异,就像托尔斯泰《复活》里面讲的每个人内心都有的那种兽性和人性的纠葛。我认为,反腐题材创作要向前跨出一步去,就应该从这些方面来思考。当然,要写好反腐题材,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要提一下,那就是说真话的勇气和决心。
南方日报:听说您近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还在构思一部反腐剧,能否透露一下内容和进度?
陆天明:是的。近期一直在写“中国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写中国这四十年,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直写到今天,总共三部,写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和人性变化。现在第一部快杀青了。写了两年半,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无法违逆的意愿要替我们这代人说说话。
我们这代人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和我们党一起经历了所有沟沟坎坎,荣幸地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如今我们能开上私家车,经历互联网时代,有时我真的觉得像做梦一样。可见,无论从物质上、生物学上抑或从人性的角度上,我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大家思考,也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轨迹。
其实,在《人民的名义》创作的同时,一些反腐部门和机构的同志也找过我。还有很多公司、电视台找我拍反腐剧。但我当时正埋头在这部小说上,不知道我这部小说能不能顺利完成。就暂时推迟了反腐写作。因为这部小说是我这一生最后一定要写出来的东西。我怕我这年龄,不抓紧做这件事,以后没有力气完成。
如今小说第一部大概五月初要写完了,我接下来就考虑构思一部反腐剧。我希望能有一点突破。这是我一向对自己的要求。以往我写的每一部反腐作品我都要求自己有突破,其实按照之前的收视率来看,我的前四部反腐作品出版和播出后,都可以立即写续集,但我没有写,就是因为当时找不到突破点。
下一部反腐剧突破口在哪儿?还在“人性”上做文章。在国人必须“救人和自救”上做文章。当然,这样的戏如何呈现?难度很大,光是理论分析还不行,需要更深入地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