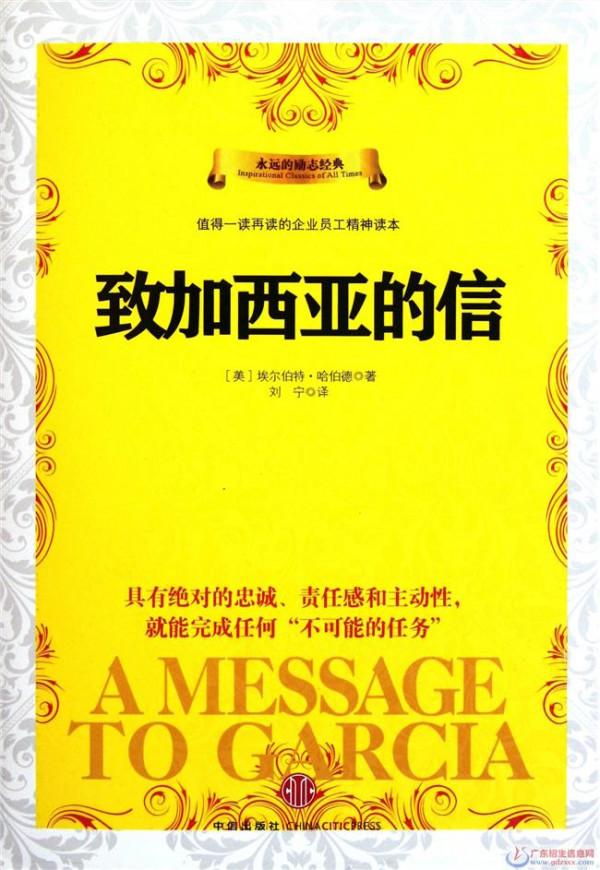邓晓芒事件 邓晓芒:做一个有反省精神的中国人
按: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于2017年3月17-19日举办了“陈家琪与当代哲学”学术研讨会,以庆祝著名哲学家陈家琪教授几十年来在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在研讨会间隙,我们专访了陈教授的多年挚友邓晓芒老师。

1:邓老师好。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都知道您跟陈家琪老师在77、78年高考之前做过了很多事情,您也从事过很多的职业,我们特别想知道在那个历史转折点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选择考大学?
邓:哦,那是顺便的事情了,我不知道家琪怎么样,我本身就在学习,自学。不管是下放农村当知青,后来回城做临时工,当搬运工,我觉得那都是维持生活的手段。我主要关心的是哲学,不光哲学,那时没有界限,就是思想,文史哲不分家,这些都关心,最关心的是哲学、方法论。

所以哪怕没有高考、没有考研这一套东西,我还是会一直学习下去,那是我一辈子关心的一个事情,甚至不是业余,人家说业余哲学家、民间哲学家,都不是,那就是我一辈子的职业,就是想搞这个事。
后来我当搬运,纯属是为这个服务的。那时搬运三级工,35-36元一个月,维持生活够了,解决了我糊口的问题。然后就是精神上面的一些探讨和享受,如果没有高考的话,打算就这样一辈子了。

2、就是边做事情,边追求自己的理想?
邓:对呀。搞搬运是为了养活自己,独立,凭力气养活自己,凭脑子来干自己的事情。后来突然说77年可以高考,我确实兴奋了一阵子,但当时湖南政策规定超过25岁就不能报考,我已超过了,所以就打消了考大学的念头。那时感觉也没什么遗憾,因为我们受的苦太多了,这算什么。
以前招工农兵学员,也没我们的事,也没什么好遗憾,因为出身不好嘛,觉得很自然。有些人改了年龄报名考上了大学,但我是想都没想,不上也没关系。后来1978年考研,我倒是真动了心。
考大学超龄,考研还是可以试试,也就去试了一下。那根本不是我选择的,是我碰上的。1978年算是考上了,但政审没有过关,1979年又考了一次,考武汉大学,当时父母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了,政审通过了,我总算入武汉大学了。
3、那您比陈老师晚一年进入学校?
邓:对。我是他的师弟。他78年,我79年。当时我们的共同的老师陈修斋先生对我们两个是最看好的,在所有招的学生里,第一届78年是陈家琪,第二届79年是我,本来他们准备第一届招了,不打算招了,隔一年再招。后来发现我没没有被录取,因为我报的第一志愿是中国社科院,第二志愿报考的是武大,但是中国社科院政审没过关,也没有把我的材料转到第二志愿这里来,等到开学了,中国社科院把我的档案材料退回了我单位,而陈修斋先生还以为我考上了社科院。
4、那时陈修斋先生已经知道您这个人了,是吗?
邓:我给他写信了,1978年考研,我给第一、第二志愿的导师都写了信,而且寄了两篇文章,业余写作。陈修斋先生蛮看好我,他本来第二年不招学生了,后来考虑到我还没考进来,于是第二年连续再招了一届,我就被招进来了,也算是了了陈先生的一个心愿。这样就和家琪成为同学,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5、那后来您跟陈家琪老师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
邓:因为完全是同类人呀。其他人呢,有的太年轻了,根本不是一辈,还有的呢追求不一样,我跟家琪,还有陈宣良三个人都有相似经历,说什么话都是在一条路上,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在武大就成为三位一体。
6、我记得陈家琪老师回忆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你们三个人绕着东湖,一个是讨论阶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邓:喔,他记得太清楚了,我都完全忘记讨论的内容了。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每天都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我已经很早停止记日记了,我原先记过,但觉得这太恐怖,你记得心里话都要被检查,要交心,太恐怖了,“文革”以后我就终止了记日记。他还一直在记。
7、你们在读书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邓:最难忘的就是那次东湖远足,还有就是每周一次讨论课,实际上就是漫谈,但非常有目的。陈先生会提供一个题目,肖捷父先生、杨祖陶先生,中西哲三个元老,当时中西哲没分,叫哲学史教研室,我们在一起讨论,由他们设计这次讨论什么,下次讨论什么,那个讨论热烈的不得了,现在的人无法想象,每个人都争着发言,面红耳赤,有时吵起来,各持其见,每人都有自己一套。
8、会不会觉得原来您可能觉得思想是您生活的一部分,但进大学后,讨论的氛围让您觉得不虚此行。
邓:那肯定是,上大学肯定是对的,不然你找不到这么多谈话的对手,也有些朋友,但那都不成对手,到这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对手,每个都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们年纪都挺大的,我考研时都31了,家琪也是31了,都过了三十而立之年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比较成熟的世界观。
一谈问题,只要摊开来谈,那肯定是要碰撞的,所以我们几个导师,陈先生呀,满意得不得了,我们这些学生根本不用教,就是提供一个场所,让我们来讨论,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学生了。
我记得当时每次讨论完非常满意,有一次,那是一次西哲的研究生讨论,陈先生就说我们的这些讨论都是国内一流的。就是说他参加的学术讨论,陈先生参加的学术讨论肯定是很多,他说我们这个研究生的讨论是一流的,当时我们非常自豪。
毕业以后,家琪到了华工,我留校当老师,有一次陈先生还把我们几个人召集起来,编那本人民出版社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每个人写了一章,整整三天的讨论,每个人嗓子都哑了,都在那里争论。
那个学术氛围现在不可想象。我跟家琪没有大的分歧,只是我们两人的思维方式有点区别,我是比较理性的,他是比较感性的,所以张念说我是“行走的概念”;陈修斋先生也是比较冷静、理性的。
9、您是研究康德哲学这方面的大家,您是一开始就关注康德哲学,还是慢慢的有个过程?
邓:我最开始关注的是黑格尔。我自学的时候,全文读过黑格尔的《小逻辑》,做了详细的笔记。进大学以前也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那是从图书馆借的,后来别人又送给我一本蓝公武译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个东西看不进去,文言文,意思也不贯通,真看不进去。
《实践理性批判》倒是做了详细笔记。入大学以后,我当时关心的是美学,所以选的方向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而且为了这个,我还自学了德语。其实当时我要考陈先生的博士太容易了,他知道我的兴趣不在德国的莱布尼茨,不在英法哲学,而是在德国哲学,陈先生把自己保留的德语教材都送给我了,他知道我的志向,不勉强我,陈先生真是宽厚。
一般来说,导师研究莱布尼茨,学生也应该帮着搞,自己的得意门生更应该搞这个。
陈先生如果向我提这个要求,我是不会拒绝的,我肯定会搞莱布尼茨。而且陈先生研究莱布尼茨,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想法,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不太瞧得起莱布尼茨,因为我觉得那跟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比起来还是差一个档次。
陈先生没逼我,所以我也没读博士。现在有的介绍我说是什么西方哲学博士,我说我不是博士,我是硕士,跟家琪一样,我们都不看重学位这个东西,做学问不在乎这些,这个都是晋升的门槛,只要能干这个事情就行了。
10、那您大学毕业后跟陈家琪老师的交往会有什么变化吗?您后来怎么没去海南?
邓:我们经常交往,没什么变化,华工离武大很近,我经常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晚上跑到他那儿去聊天。我跟陈家琪、陈宣良是最好的朋友,后来陈宣良去了北京,再后来又去了法国,也就剩下我和家琪两个。家琪后来去了湖北大学,我还经常跑湖北大学,一直来往很多的。
到他去了海南,我们来往就少了。他特别希望我去海南,动员我好几次,还跟我爱人做工作。我最后没去海南是因为我懒得动,没必要折腾,我就想安心在那里做一些学问,到海南一切又要重新开始,又要面临很多新问题。
我在武大分了一间房,已经安顿下来了,何必再跑。我前半辈子已经跑够多了,我下放就下放了三个地方:江永六年,转回我老家耒阳三年,后来又转浏阳一年,最后才回长沙,这就十年。
回来做临时工,转了好几个劳动服务大队,不断跳槽,最后去当搬运工,满意得不得了。后来公司发现我喜欢学习,就想把我调去搞供销,坐办公室,我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呢,搞供销那要出差呀,要在外面跑业务什么的,那太麻烦了。
我坚决拒绝,我说我进来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决不跳槽。当时为什么招我去搞搬运,那是因为我的前任闹情绪,说是搞搬运找不到老婆,人家一听搞搬运的根本不跟你谈,公司就把他调到车间当工人去了。这样就缺了一个搬运工,他们招工时就强调不能跳槽,我说我决不跳槽,现在又要调我去搞供销,我不干,搞搬运多舒服呀,每天只要不到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当然得出一身大汗,毕竟是体力劳动,搞完了以后洗个澡就随便你在那里干什么了,我就在那里看书。
干半天活,其实半天都不到,就可以看书了,那多好呀!照发每个月35元工资,一切劳保福利什么照发,多好的工作,我干嘛要去干供销,我愿意这样干一辈子。坐在司机房间的那个小床上,一屋子的人都在那里打牌、聊天、下棋,我就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书。不管旁边的人干什么,我看书是不受影响的,我看我的书。我爱人就问我:“我唱歌不影响你看书吗?”我说绝对没影响,她唱她的,我看我的。
11、1981年的时候,华工开过一次会,纪念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两百多年,主题是“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您当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邓:当时这其实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来的,对康德的批判比较多,所以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批判康德,而不是黑格尔。黑格尔一直是显学,很多人研究黑格尔,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因为黑格尔是马克思的来源,其实康德也是,但很多人认为,康德是不可知论、唯心主义,批评比较多,所以研究康德的人少,研究黑格尔的人多。
1979年李泽厚发表《批判哲学的批判》,那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件,我马上就买了,包括后来的修订版。
李泽厚开启了中国的康德学研究,打开了一个视野,对当时国际上的康德研究,简略地介绍了一个概况,美国有什么观点、苏联有什么观点、德国有什么观点,在里面都有一些蛛丝马迹。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觉得研究康德比研究黑格尔要有趣得多,更符合时代。
所以开这么个会其实是个政治事件,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就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固守传统。当时李泽厚先生是主张要康德的,康德的主体性纲领,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他首次打开的,是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不知道,但是他首次打开,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权利,当然没有说得这么明确,但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人应该有主体性,不应该人云亦云,不应该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这是李泽厚提出的。
第一次好像是在上海开的会议上提出,后来出了一个文集,第一篇就是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他就提出黑格尔太专制,康德还保留了一些主体性。跟现代的存在主义等思想比较能够相通。当然后来考虑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
12、今天您再回头看这个问题,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要康德还是黑格尔?
邓: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如果从学术来讲,我既要康德也要黑尔格,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专门有篇文章在去年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的第一期上,就是谈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确各有利弊,黑格尔确实比较封闭,康德是开放的。
13、我曾看过您的一个采访,有一句话我影响很深,说黑格尔“一不小心搞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是在舍身炸碉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