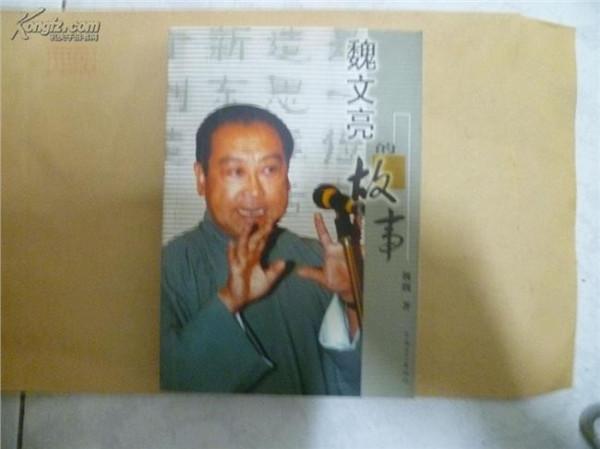魏文亮有烤肉 魏文亮有着自己独特的玩意儿
粉碎“四人帮”,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宽松的环境,和谐的氛围使魏文亮迸发了创作的激情。继《百花盛开》之后,依然与孟祥光合作,又创作了《评戏新貌》、《小太阳》、《众星捧月》等新相声。每一个新作品使了就响,就火。
他在20岁的时候,已经以会的段子多,表演说、学、逗、唱俱佳,技艺娴熟而奠定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三十而立,该“立”的时候,虽然赶上了“文革”,但他另辟蹊径,成功地塑造了话剧《农奴戟》、《槐树庄》两个戏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表演才能大增;四十不惑时又创作出了一批作品。而最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当属《要条件儿》。
有知识性的相声,有趣味性的相声,有针对现实或褒或贬的相声。毫无疑问,这第三种类型的相声应该最受观众的欢迎。而在第三种类型中,“贬”的又比“褒”的更得人心。因为相声就是以讽刺见长。魏文亮创作的《要条件儿》一问世,就给千家万户送去了欢笑,达到了当时所出现的其它相声所无法比拟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强烈效果。
这个相声所以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选材好。他选择了“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可是他并没有从正面去歌颂,而是从反面对亵渎爱情的表现进行了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讽刺、讥笑。
他抓住的是女方要嫁妆的这一普遍现象,从这一亵渎爱情的侧面,对一些人头脑中滞留的封建思想,迂腐的传统行为给予了揭露。其笔锋是锐利的,语言是尖刻的。但并无敌意,于讥讽中给予暴露,但又在讽刺中给予规劝。这个作品完全是讽刺,但有着极为积极的社会意义。
再有,这个作品虽然是个不大的段子,但它的创作非常符合相声创作的规律:它有垫话、有瓢把儿、有正活、有底;它有很多的包袱,包括有几个楼上楼的包袱。而每一个包袱又都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比如底部分:
魏最后还差五分钱。
孟那怎么办?
魏又卖了个酒瓶子。
孟卖了多钱?
魏八分。
孟还剩三分,
魏我又买了棵冰棍儿。
这个底把全段相声推向了最高潮。就应该这样,一段相声的底就是这段相声主题最突出的地方。女方为了要嫁妆已经把男方搜刮得“一干二净”。但仍“步步紧逼”,只差五分钱了,仍不罢休,让男方卖了个酒瓶子。尽管余下三分钱,还买了一棵冰棍儿。
显然这样处理多少有些夸张,但真实可信,因为前边的一系列的铺垫已经勾勒出了这个女人的大体轮廓:视自己为商品,往外出售,已把“爱情”抛到九霄云外,并且欲壑难填。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夸张,才有了包袱,而且不是一般的包袱,是个大的雷子。可以认为包袱是相声的灵魂,《要条件儿》有足够数量,而且是高质量的包袱,这也是这个相声成功的一个方面。
这个相声能够得以迅速传播,是因为作品好。但只是有好的作品,没有好演员,那么作品再好也很难产生很大的影响。是有“活保人”一说,却不是绝对的。同样的一个作品,由不同的演员表演,其效果肯定不一样。《要条件儿》说了就火了,演员也至关重要。
这个相声在进入了正活之后,就开始倒口儿了。魏文亮能倒山东口儿、上海口儿、东北口儿、唐山口儿……很多很多。《要条件儿》使的却是他的家乡语言——天津话。要说天津的演员说天津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如囊中取物。
其实不然。因为《要条件儿》里的天津话是夸张了的天津话,所谓的夸张表现在语气、语调、节奏等几个方面。比如说“买嘛儿”,一连就是四个,越说越快,一气呵成,如炒豆般的脆亮,听起来没有丝毫的噪的感觉,却显俏皮。
再如说“没门儿”,一连说两个,第一个说得平,而第二个无论是语气还是语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门儿”字,在说过去了“没”字后,突然拔高,如异峰突起,就像京剧《四郎探母》中“叫小番……”一段唱里的“嘎调”,很是精彩,很是别致。
何况他学的是女人,用的是女声,语调很尖,嗓音很高,却不噪。这和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很泼辣,有一张刀子嘴的女人说话很是相似,但也有所夸张。而合理、恰当的夸张也就是艺术的处理,加大了讥笑、讽刺的力度,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喜剧”效果。
爱情是神圣的,但一些女人却视自己为商品,其实在亵渎爱情的同时也在亵渎着自己。这并不是生活中的喜剧,而是悲剧。曾有哲人说过:“有许多观点,喜剧是同悲剧相结合的,喜剧唤起的已经不是轻松和愉快的,而是痛苦的悲哀的笑了。
”《要条件儿》所以反响非常强烈,因为它不是从很浅薄的逗笑这个目的出发,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目的是严肃的,手段是轻松的;内容是深刻的,形式是诙谐的;政治情感是炽热的,抒情方式是特殊的。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而使喜剧和悲剧达到统一,这也是《要条件儿》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要条件儿》是一个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它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还得到了一位电影导演的青睐。著名的导演谢铁骊就专程来到了天津,找到了还在北海仪器厂当工人的魏文亮。魏文亮对谢铁骊早有耳闻,知道谢铁骊导演过《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杜鹃山》等许多优秀的影片,魏文亮对他很尊敬。
知道了他要把《要条件儿》搬上银幕,兴奋异常。正是因为他的青睐,《要条件儿》也就成为了电影《笑》里的一个部分。魏文亮已经38岁了,这是他第一次“触电”。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要条件儿》就是。其效果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好。的确,一次,一位与他素不相识的年近花甲的大娘,领着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姑娘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他的家,叩开了他家的门。
甭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他把大娘和姑娘请进了屋。客人来访总是有目的的,不错,原来这位姑娘是这位大娘的准儿媳,还有一个星期,姑娘就要嫁给大娘的儿子了。这一老一小是特地来请魏文亮去参加婚礼的。他莫名其妙,当然要问:“请我去喝喜酒?”
“是,您可一定要去。”姑娘说话有意思,“您不会拒绝吧?也不会说没工夫吧?要是真的没工夫,没关系,就等您什么时候有了工夫,我们就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这可真有意思。”魏文亮说,“我说话您别不爱听,请我们参加婚礼?咱,根本就不认识呀?”
“是您不认识我们,可我们认识您。”姑娘快人快语,也是个敢于“暴露”自己的人,“本来八竿子打不着,可干嘛要请您去?不怕您笑话,原来我就是您说的《要条件儿》里的那样的姑娘。可没有您说的那么‘邪乎’,最后还卖了个酒瓶子,没到那种程度。
可彩礼是真要,要得还真不少。这么说吧,我要的东西,怎么说呢,凭他家的条件,根本就达不到。要是满足我要的条件,就得去借钱。老的疼儿子,不能不去抓摸钱。真要是把老的急个好歹的,您说我这不是缺了德?听了您说的《要条件儿》,不只是听了一遍两遍,越听越觉得我是真不对,越听我是越脸红。我爱他儿子,逼着要彩礼,那还叫‘爱’吗……”
大娘接过话茬儿:“我这儿媳妇可是真好,彩礼该要还得要,可没那么多了。就说手表,原来她是真要‘罗马’。现在呢,有一块咱天津出的‘五一’就行了。还别说别的,就是这一块手表,省出了三桌酒席的钱。魏老师,我们还真得好好谢谢您。瞧得起我们,您就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去!一定去!”
大娘和姑娘都大笑。走了,是心满意足地走的。
魏文亮和孟祥光如约参加了姑娘的婚礼。
这样的事可真不少,有为数不少的老人都对魏文亮说现在儿媳好了,有的还没结婚的,彩礼要的少了;有的已经结了婚的,儿媳孝顺了。一段相声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效果,魏文亮的《要条件儿》的作用很大。这是一般的相声段子所无法比拟的。
在短短几年里,魏文亮和孟祥光合作创作了十多个相声。他们的作品不同于专业相声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相声演员,对相声结构的把握准确,对所制造出来的包袱有没有效果,能够估计出个八九不离十,而且自己创作的作品就一定符合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因此,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无须进行二度创作,可以直接搬上舞台。他们是相声演员,也是相声作者,说得确切一点:他们就是相声作家。一段《百花盛开》、一段《要条件儿》、一段《评戏新貌》、一段《小太阳》……就完全可以确定他们“相声作家”的地位。但他们却把这点看得很轻。就当练练手。
如果说创作、表演了《百花盛开》是魏文亮艺术生涯的第三个里程碑,那么至《要条件儿》的诞生这一阶段就是他艺术生命旺盛,形成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期。
魏文亮从张文斌那里知道了什么是相声,并且开始了艺术的生涯。在这个阶段,他是说相声了,但也只是“说”相声,尽管也能有自己的发挥,但只是偶尔。“鹦鹉学舌”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因为他还不能——也可以说还不懂把相声和自己的思想、意识融为一体。
魏文亮是武魁海的徒弟,他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是因为师父技艺全面,无所不能。名师出高徒,他跟师父学了不少的传统活,也继承了师父使活最突出的特点——爆、脆。在这个阶段,他跟师父学,同时甘当诸位前辈,哪怕是同辈的学生,广采博收,使他的表演水平大增。也逐步有了自己的特点。但,还很不明显。
魏文亮创作、演出了《百花盛开》、《要条件儿》等新节目。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明显的风格和特点。首先,魏文亮没有俗气。
相声是俗文艺中的一种演出形式。相声里的这个“俗”并不是俗气,不是俗套,更不是贫嘴呱舌。而是通俗、易于接受。具有“大众化”是相声的“俗”的典型特征。相声是不能离开“俗”的,如果变“俗”为“雅”,势必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但相声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旧社会,相声艺人根本不懂得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把说相声作为了谋生的手段。这是非常正常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要取悦观众,甚至去迎合一些低级、庸俗的观众的需要,在一些即使是很好的相声段子里,也要加进一些低级、庸俗的,甚至是很不健康的内容。
除此,同样是为了取悦观众,在表演上也有很多的俗气,比如点头哈腰、作揖什么的。这并不是什么错,在旧的社会里,艺人要活下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时代变了,旧社会的艺人成为了新社会的人民的艺术家,演出的性质也随之改变,由为了谋生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需要演员的表演也要改变,符合新的时代的需要。但是,有一些老艺人似乎根深蒂固,一些低级、俗艺人愿意抛弃,但似乎已经成为习惯,很难改正。
更有一些新演员却视一些旧的东西为精华,本来没有,却努力去学。毫不客气地说,这是这些演员的悲剧。魏文亮已经说了30年的相声,也算是个老艺人了。但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低级、俗气。是什么原因呢?
魏文亮懂得如何去提高相声的艺术趣味。相声是“逗笑”的艺术形式。逗不笑观众就不是好的相声演员。但,逗笑了观众也未必是好演员。因为“笑”多种多样。要让观众笑,这是他的职业所决定的他的职责。可是他非常清楚给观众的应该是健康的笑,而不是小市民庸俗趣味的笑;给观众的应该是真心的、会意的、长久的——就是让观众在听过相声后,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还笑,而不是强笑和那种一笑了之的皮笑肉不笑。
不给观众低级、庸俗的笑,是因为他没有低级和庸俗的表现;不让观众强笑和皮笑肉不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神圣职责——寓教于乐,宣传的是真善美。
他心如明镜,观众是热爱和尊重演员的,因此,他要对得起观众。他绝不自轻自贱,更不把自己当成供人取笑的小丑,摆出一副庸俗,甚至猥琐的样子,来换取观众廉价的笑声。
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是会换回笑的,可是更能刺伤观众的感情。观众的笑不是发自内心,只是笑这个演员无能,是对这个演员的惋惜和批评。他注重的是格调。
不否认还有个别的观众希望看到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可是他从不去迎合。他知道相声是艺术,而不是“下三烂”的玩意儿;他知道一段好的相声都有一个严肃的主题,都有一种炽热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要用无聊的、庸俗的包袱去冲淡,甚至是湮没严肃的主题呢?让炽热的思想感情扭曲,甚至变形呢?他更清楚像什么伦理、生理方面的玩笑,猥琐、鄙陋的打诨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也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一种不折不扣地破坏艺术的表现。
相声是俗文艺,但他表演的相声于大俗中见大雅,又于大雅中见大俗,雅俗共赏。就因为他所追求的是高格调、高品位。他是旧社会过来的相声演员,但他毫不留恋旧的艺术趣味,这是他的道德观念、文化修养、审美观点、生活情趣所决定的。也是他在这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相声演员是应该脱俗,远离低级趣味。但,对于一些演员来说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一些演员如果真正地脱了俗,离开了一些低级的东西,可以说几乎就不会表演了。魏文亮则不然,他靠的不是俗气,不是低级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懂得相声演员让观众笑,就要笑得酣畅、轻松、机智,还要含蓄一些,而要让观众得到这几种笑,那么演员就得有能耐。于大俗中见大雅,又于大雅中见大俗,雅俗共赏,这是他的艺术风格和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博采众长,但并不拘泥于某一“流派”(笔者认为相声艺术并无“流派”存在),某一大家,某一前辈,而融为自己所独有的表演方法,这是魏文亮的相声艺术的又一大特点。他会的相声很多很多,传统的、新的,少说也会一百多段(在他这个年龄,能会这么多活的演员极少)。
听他的相声,是听不出来说这段像谁,说那段像谁,魏文亮就是魏文亮。比如他的柳儿,学京剧里的老生、花脸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似乎有侯宝林的特点。但,又不同,学唱里有包袱,而且很脆亮,又有他师父武魁海的脆和爆的风格。
学前辈,也学同辈(比如他“偷”学小立本的《学评戏》),不是学了就用,而是先经过消化,根据自己的条件,一些地方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这个基础上再搬上舞台。
毫无疑问,这就是他自己的了。尽管只是一个小段,比如传统小段《美人赞》,很多的演员都使,他使的就与众不同。相声大师马三立就对他说,“听你说的《美人赞》,有意思,像我,像阎笑儒,像你师父武魁海……到底像谁?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像你自己——魏文亮。你使的好,是真好”。“天下人皆师也”。武魁海在临终前多次对他说过这句话。广撷博收,融会提高,当然这是他能够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的一个主要原因。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人人皆知。在这四个方面,魏文亮都是非常出色的。然而,谈及他的风格和特点,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字:演。“演”就是表演。几年后,一次他和李法曾同台演出,李法曾说:“文亮,我听了你的几段相声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不是说相声,而是在表演相声。
”李法曾不是相声艺术的专家,是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对魏文亮的这个评价,未必是全部正确的,因为“语言”是表演相声的“工具”,语言就是说出来的,还是应该说“说相声”。
但李法曾认为“魏文亮是表演相声”。这也正确,又岂止是正确,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魏文亮在注重“说、学、逗、唱”的同时,还非常注重表演。相声是曲艺艺术中的一个曲种,曲艺艺术和戏曲艺术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一个是“说法中现身”,一个是“现身中说法”。
换言之,戏曲表演是为演员固定了角色,这位演员,假如他扮演的是《空城计》里的诸葛亮,那么他由始至终就是诸葛亮。而相声不同,演员要时进时出。表演相声《空城计》,这位演员一会儿是诸葛亮,一会儿是司马懿,一会儿是老军,一会儿又是演员自己。
李法曾认为魏文亮是“表演相声”,他无论是说哪段相声,只要进入了角色,就再也见不到“魏文亮”了。尽管站在舞台上的还是魏文亮,是说或唱的也是“魏文亮”,但已无“魏文亮”的痕迹,他就是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比如他说的《李陵碑》,表演“碰碑”一场戏,学唱“李陵碑本是石头的,我不碰它它不依。狠狠心肠我就碰了吧”这三句时,无论是唱,是动作还是表情,他就是面临绝境,要以一死而报国,报君的杨继业。
他的唱,他的动作,他的表情已经使观众认为自己不是在听相声,而是在看戏。当他唱第四句“又怕碰破了脑瓜皮”,就迅速地退出了角色,还原了相声演员自身。
就是在这瞬息的变化间,包袱抖响了,完成了相声应有的“逗笑”功能。说传统相声如此,说新相声亦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演员和角色的变换,一次又一次地变换着时间和空间,而在变换中很自然,他是“表演相声”。当然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很奇怪,一掀台帘,你一上台,就把几千观众的眼光都给抓了过来。我得‘研究研究’你。”
这句话出自老一辈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葛存壮之口。从这个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文亮是多么的喜爱,可以看出魏文亮是很有“台缘”,很有“魅力”的。他上了台就把观众的眼光都抓了过来,实属不易。其原因何在?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没有俗气,台风格外地亲切。
无论是穿中山装,还是后来穿西装,就是表演传统段子,穿着大褂上台,给观众的是一股清新的感觉。他一上了台,两只眼睛射出来的是亲切的目光与和蔼的笑,发自内心。他给观众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位演员不错,很新,上了台就这么招人喜欢”。
不曾开口,观众就会被他“调动”起来,继而,就会随着他的“指挥棒”转。也是因为他一上了台,就抛除了一切杂念,全神贯注地进行表演。一旦进入了表演,就开始了和观众的交流,在亲切的交流过程中,完成了一个段子的表演。这不能不被认为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一句话:魏文亮是用嘴说相声,更是用“心”说相声。尹寿山曾因为他在台上打个哈欠就把他撂在台上。为什么?尹寿山说得对:你上了台就要对得起观众。这句话他记住了,记了一辈子。所以他要对得起每一位观众,他是用“心”说相声,这样评价他,恰如其分。
能够和任何一位相声艺术家区分开来,以自己所独有的风格和特点出现在舞台上,魏文亮就是魏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