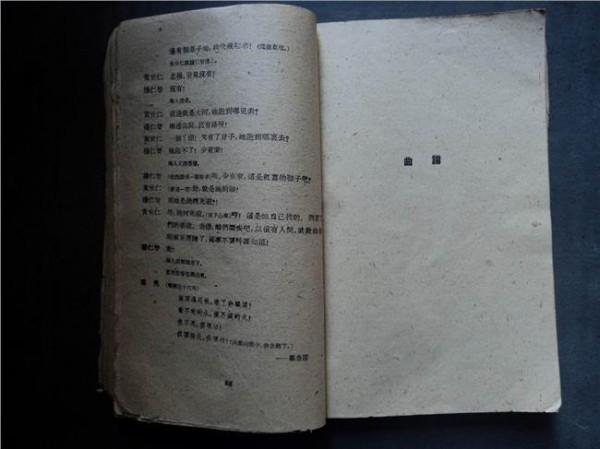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 想起那西去列车的窗口
1963年,郭小川和贺敬之、柯岩夫妇来新疆采风,目睹了上海支边青年奔赴边疆的壮举。为此,贺敬之在阿克苏写出了激情澎湃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
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郭小川、柯岩已先后作古,当年来到兵团的上海支边青年也大都退休回到了生养他们的故土。蓦然回首,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还不时会在我的眼前浮现。
由于我的父亲曾在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正中书局当过编辑,1966年6月起,他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写交代材料。因为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忧虑,思量再三后,我决心以鱼姗玲为榜样(鱼姗玲是首批上海支边青年,1965年7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她的事迹,并刊发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实现“脱胎换骨”。
1966年7月26日下午,随着一声高亢的汽笛,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上百名妇女组成的合唱队,手拿红花,齐唱《高歌进新疆》。车厢内,穿着新军装的年轻人,纷纷把头探出窗外,不少人挥手时泪流满面。来送行的亲友哭着、喊着,跟着火车跑着,直到看不见火车的踪影。
临开车前,身心交瘁的父亲赶来了,手上提着平时上下班用的旧人造革拎包。面对我这个“立志划清界限”的儿子,他默默无语,留给我的只是那充满忧虑和关切的眼神。当时,我没有哭,只感到周身涌动着沸腾的热血,心里在念着:终于踏进了革命队伍。
这趟车说起来是专列,但跑起来却很慢,几乎是逢车必让。有时为了让别的火车,会在一个小站上停很长时间。为保证行程安全,长宁区劳动局带队干部叶同志,在火车开出不久即宣布成立纠察小队,点名让我当队长。每到停车下去散步时,纠察队员就要提醒各位不要走远,确保开车时不少一人。列车主体是硬座车厢,也挂了几节卧铺车厢,卧铺是我们所有人轮流去睡。那时讲风格,崇尚先人后己。每次轮到我时,我总是让给别人。直到火车快进新疆的那个夜里,一名纠察队员过来跟我说:“叶同志叫你过去一趟。”
我来到叶同志所在的卧铺车厢后,他指着对面的下铺说:“马上躺下睡觉。”我转身要走,他又一把拉住我,并把我按在铺上说:“执行命令!”我服从了。这一夜,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7月31日早晨,火车到达吐鲁番大河沿车站。这里四周是遍地砾石的戈壁滩,上面建有一些简单的院落和商店。三师接待站离车站不远,全是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我们按小队住了进去。刚离开繁华城市的我们,住进了过去只有在电影上才能见到的帐篷,兴奋得就像当了探险家。早餐是玉米面发糕,颜色如同上海的蛋糕,但味道却千差万别。
8月1日,当一轮红日跃出地面时,随着“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边疆”的嘹亮歌声,载着我们的车队便浩浩荡荡地向南疆进发了。纠察队员分别坐在每辆车的车厢尾部,卡车驾驶室的位置留给了体弱和生病的人。在漫长的戈壁沙石路上,卡车行驶起来不是摇来晃去就是上下颠簸。坐在车厢尾部不仅颠得厉害,而且时常遭遇后轮扬起的大团尘土。每到一处停车时,我是最后一个下车,觉得浑身的骨架就像要散了一样。
车队日行夜驻,途经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三岔口、色力布亚,于第6天下午到达三师前进五场(现三师四十五团)七连。3天前先到的上海川沙县(现上海浦东新区)支边青年来迎接我们,争相帮助我们拿行李,领我们进了地窝子。
这一路,我们走了12天。期间,我被评为“行军积极分子”,这对我的父母来说无疑一种安慰。1966年8月6日,大规模的上海支边青年进疆招收工作结束,而我幸运地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没搁盐就是甜的
七连四周是绵延不断的沙包,上面长着稀疏的红柳和骆驼刺。地窝子远看跟沙包一样,露出地面的那半截,里面是芦苇草包着的,外面码着土,再用红柳、芦苇和泥巴盖顶。出口到地面,是一截挖出来的斜坡。下车后,小队换成了班的番号,一个班住一间地窝子。床是木板搭成的通铺,上面铺着防潮的羊毛毡子。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煤油灯。
刚到的那天下午,连队食堂为大家准备了绿豆汤,就放在路边的大铁锅里。我拿着新发的搪瓷碗走了过去,炊事员问:“要甜的,还是咸的?”喝绿豆汤,当然是甜的了。但我接过来喝了一口,什么甜味儿也没有。再问,回答是“没搁盐就是甜的”。大锅边上只有一个放盐的小碗。后来我才知道,淡水就是所谓的甜水。连队食堂后面的唐王渠常年流水,渠水清澈见底,但喝起来又咸又涩。有时没有淡水了,食堂就用唐王渠里的水,烧汤可以不放盐。喝过那水,再喝叶尔羌河引来的渠水,尽管泥沙俱在,还真有甜味儿。糖在那时是罕见的,上海支青从家里带来的奶糖就算是珍品了。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连队在给我寄路费的汇款单附言上就写着:奶油糖,不能忘。
经过短暂的学习休整,我们开始了垦荒劳动,用坎土曼挖红柳平沙包。虽然干得腰酸背痛,手上打起了血泡,但是没有人叫苦喊累,大家知道要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休息时,各班围坐在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狠斗怕苦怕累的“一闪念。”收工回来,每人还要用坎土曼砍上一截红柳根,送到食堂当柴烧。当伙房前的柴火堆成小山后,就往各班的地窝子前堆,准备冬天取暖用。
刚来不久,夜里下起大雨。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后,纷纷把铺在褥子底下的羊毛毡子翻出来,盖在被子上,蒙住头继续睡。毡子上有股难闻的膻味儿,可是人太累,顾不得这些。天亮后,雨停了,地窝子里全是黄泥水。大家就卷起裤腿,光脚来回跑,把淋湿的衣物搬到地窝子外面晾晒。地窝子顶上的泥巴让雨水冲走了,不少人就拿起坎土曼挖土往上甩。值勤的副连长徐福生看到后,急得大喊:“不要再甩了,再甩,房顶就要塌了!”
戈壁滩上风沙多,有时正在劳动,天就变了。当铺天盖地的沙尘狂吼着向我们袭来时,大家就原地坐着,两手抱着头,把脸埋在膝盖中间。风沙过去了,你看着我,我望着你,都忍不住哈哈笑起来了,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跟出土文物一样。
进疆那年的冬天,气温很低,我们出去劳动时,要把棉衣棉裤都穿上。一天下午,突然飘起了雪花。在一块刚被推土机推出的荒地上,全连在进行平地大会战。连队文教拿着铁皮喇叭高声朗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几百人热火朝天大干时,场部宣传股的人来了,拿着照相机拍摄劳动场面。他们来到我们班时,大家都努力表现,战友吉忠楼用一条扁担挑起了四筐土,还一路小跑。
开荒是苦活,给荒地放水压碱更是辛苦。一年开春,渠道垮口了。班里一位同志发现后,立即跳入冰冷的水中,用身体堵在决口上。等大家堵好口子,把他拉上来时,浑身哆嗦得连话都说不清了。回到地窝子,他脱掉满身泥浆的湿衣服,随便擦了擦,就钻进了被窝。
开荒劳动强度大,每个人的胃口都很好,不管粗粮细粮,只要能吃饱就行。馍票不够吃,还让上海家中寄全国粮票过来。伙房里常是水煮菜,让人感到缺油水。尽管每隔10天或者14天才休息一次,但是仍有人结伴外出,到10多公里外的维吾尔族老乡家里买牛羊肉改善伙食。
拉练进了小海子
我在前进五场工作了3年半,随着连队搬了4次地窝子。开完一处荒地,我们就换个地方。
1970年3月,根据三师师党委决定,我所在的连队要迁入小海子垦区新成立的五十二团。那时部队备战搞野营“拉练”,兵团的准军事部队也不例外。全连进行思想动员后,来了一次大多数人事先不知道的演习。我们打起背包走了一段路后,才宣布是演习。
第二次集合上路,是真的了。我们背着行李走了近30公里,来到四十六团团部(现四十五团二营)。行军一天下来,不少人脚上磨起了水泡。第二天,行军方式改变了,连队走到大路上,宣布化整为零,分开搭乘去师部“五七”新村的卡车。就这样,全连先后搭车来到了师部,第三天继续搭乘卡车去巴楚。第四天,全体坐上五十二团派来的马车到了团部。
休整后,连队进了新驻地,番号是五十二团八连,我被宣布担任一排一班班长。八连是个红柳滩,地势比较平坦,四周有不少胡杨林。刚到时,三两人就地挖个坑,上面再搭些树枝,就算有睡觉的地方了。这里黏土多,我们不再挖地窝子了,而是盖一种叫干打垒的土房子。在选好的一块平地上,用一种长方形的木板箱当模具,往里扔土,再洒上少许水,用木夯把土砸实。一截土墙成型后,打开模具箱再接着制一截,直到整栋房子垒成。这样的土房子,比起地窝子要进了一步,至少是建在地面上了。
盖干打垒的房子,大梁和檩条就用胡杨。男生班轮流到胡杨林里去伐木。一天下午,一辆马车回来经过河沟时,由于坡陡,拐弯又太急,突然翻车了。躺在车上打瞌睡的王益民被压在车底下。同行的人用斧头砍断拴马的缰绳,把翻倒的马车扳过来,挪去木料把王益民抬了出来,此时他已昏迷不醒。随后,人们火速将他送往团医院,但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王益民的死令全连的上海支青都感到无比悲痛,在追悼会后,我们都去送葬。墓地就在八连路边西面的一块高地上,坟上堆满了大家送的花圈。
在兵团屯垦戍边的艰难岁月里,我能成为许许多多上海支边青年中的一员,用青春和血汗去唤醒沉睡的万古荒原,感到无比光荣。往事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远去,心中难舍难弃的仍是那段拓荒创业的经历,这是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耳边仍回荡着贺敬之那穿越时空的声响:西去列车这几个不能成眠的夜晚呵,我已经听了很久,看了很久,想了很久……我不能、不能抑止我眼中的热泪呵,我怎能、怎能平息我激跳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