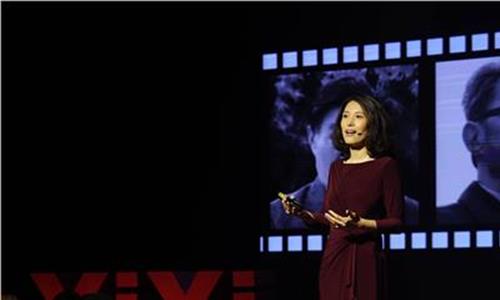吕楠在路上 吕楠:在路上的苦兄弟
在路上的苦兄弟 初识吕楠,往往为混杂陌生和熟悉的矛盾观感而困惑。他历时十五年拍摄的三部曲:《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近两年始为人知。陌生也许源于非常规的题材和构图的完满冲撞而成的紧张感,隐隐透露出不安的氛围。
而悄然浮现的文学影子竟是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旧时欧洲文学巨匠。 被囚禁的赤裸疯女与门外茫然的老妇;希腊雕像无言地俯视沉睡的艺术青年;石桌上发病的疯子难以自禁,四周绕行的病友对此习而不见……我们已准备好面对混乱的场面和失焦、倾斜的构图,可是吕楠呈现的精神病院宁静至极,肃穆至极,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
神圣之感与对画面的控制密不可分,他以极富秩序感的形式给无序的存在赋形。
黑暗混沌的存在被形式的光亮敞开,现身此岸,此时观者心底似曾相识的影像不是现代摄影的经典之作,而是那些更久远的欧洲古典油画,构图、造型和对光线的处理无不处于完满的秩序中。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精神病院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在教堂拍的,随后他进入了对中国乡村天主教徒的系列拍摄。疯狂与虔信本在一念之间,更何况西方宗教传统中,疯子常常是先知的别名。吕楠在疯狂者身上发掘常人常性,又在乡村的匹夫匹妇中铄炼坚韧的信仰。
让我们回到对宗教的一种基本认识,它本是受苦人的宗教,耶稣生于马槽,一生行走于麻风病人、妓女和小吏中间。而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艺中,卑贱者身上往往蕴含了更高的人性,隐藏着人性通向神性更壮丽更神圣的秘密。
信仰最终达乎的只能是以全身心仰望之的肉身,吕楠对宗教的理解最终亦达乎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践行信、望、爱。人物多为老、苦、弱者,或三两老妇人低头祷告,眉目一律低垂而慈悲,似乎不忍于此世的苦难;或乡人聚合送别刚刚离世的老人,逝者安详,生者庄严;或小羊亲吻老妇手中的十字架,人心也被柔软地触碰了一下……漫漫山野,芸芸草民似乎都被这哀悯之情渗透。
目击了非人性和神性之后,吕楠的第三个系列走向了两者的合题:质朴而庄严的人性。行走于藏区的七年,他拍下四季轮回,春播秋收,饮食与休憩,爷孙、母女、夫妻、姐妹的相处相依,人性只有落实到日常生活和基本人伦中才具有稳妥实在的根基。
生活的质地是厚重的,洋溢着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这往往只是后人的追认和他者的想象。看着亦步亦趋复制古典油画的影像,我被理想的生活状态打动之余,不免认为牧歌式的西藏只是一厢情愿。
不再包含悖论和张力的影像在现代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有效性?不过这也提示了吕楠的关怀实则超乎现实,达乎某种更本质更深刻的境界。 纪实至此已然升华出一种抽象,底层关怀其实只是皮相,其作品中细致的物质肌理和写实的人物肖像最终指向的乃是“心灵的思考”——人性中本质和必然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时代的悖论,只能在被放逐者身上寻找人性中根本、持久和本质的部分。精神病人、被压制的乡村信众、化外之邦的农民、金三角的吸毒者,他们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却是“人身上的人”——人类的缩影和象征,他们在代我们受苦,替我们感受这个世界并作出某种反应:疯狂、信仰或庄严地生活。
这也是他和时下大多数纪实摄影的不同之处,“底层”一词如今意指某个分化出来的群体和阶层,对于摄影者和观看者而言只是“他者”和“偶然”。
他们逐渐成为社会有机体中被分隔出去的一部分,成为需要我们投入更多注视和关怀的他者,而“我们”与“他们”不再分享共同的命运,也不再期待共同的神恩。这不是文艺家的过错,只是急剧分化的现代社会中艺术不得不分担的命运。“以一身担天下苦”几成绝响,苦难、劳动和信仰这些基本价值反而远离了主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