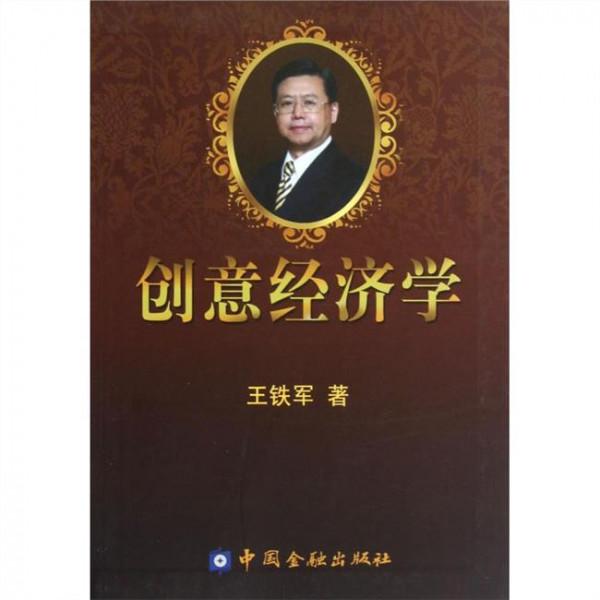王光辉教授 观点公羊夷夏论与天下主义|王光辉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古典书院助教)
来源:《原道》第33辑
(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孔子二五六八年丁酉十一月廿五日癸卯
耶稣2018年1月11日
近年来,“天下主义”观重新为中国学界所倡导。《公羊传》中有关夷夏的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提供了一很好的视角。

一、《公羊传》中的天下观
甲骨文的卜辞中,有“尸方”的记载。郭沫若认为,“尸方”是商民对东夷国家的统称。可以想见,早在商初,人们已经使用确定的称谓,区别与自己不同地缘的人,并通过战争与之发生联系。至春秋之时,“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这种交往更为密切。

从《春秋》三传及相关资料看,这一交往,既是夷狄之国不断蹂躏诸夏,又是诸夏之国不断树立文化自觉、自信的过程。《公羊传》所谓“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与夷狄之获中国”,《论语》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是此过程的写照。

因此,一方面《公羊传》有“攘夷”之义。其以盛赞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为王者之事。并在某些地方,表现出对夷狄的轻蔑,“桓公之于戎狄,驱之而已。”另一方面,与“攘夷”之义相比,《公羊传》又有更高之理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攘夷”只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以华夏之礼义感化夷狄,最终臻至太平之世,才是最终之目标。基于此一目标,《公羊传》中关于诸夏与夷狄之区分标准,不在局限于地域,而更多偏向于是否具备礼义。诸夏之国废弃礼义而有夷狄之行,《公羊传》就“夷狄之”;夷狄之国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公羊传》就“进之以爵”。
其一,“天下”为奉行儒家礼仪制度之天下。此礼仪制度由王者承天制作,布政施教于天下,天地万物奉之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序。具体到人伦来讲,礼仪制度确保天下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一秩序非如现代人所理解的“君尊臣卑”“男尊女卑”,而是在一定情况下要求君要尊臣,男要尊女。如君对于诸父、诸兄、上大夫、盛德之士、老臣,不能直呼其名。
其二,王者率先践行礼仪制度,次及诸夏、夷狄。《公羊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大一统的背景下,设“内”、“外”之别,诚如何休所言:“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此一“渐治”思想于《论语》中亦有体现:“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此亦《大学》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其三,至太平之世,无“内”与“外”,“诸夏”与“夷狄”之分,“中外之治清和咸理,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尤有进者,此太平之天下,“恩及禽兽,泽臻草木”,“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王者之化亦为草木昆虫乃于至山川所感。
“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植,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偕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由是观之,传统儒家之天下观,是由夏化夷,最终皆奉儒家礼义之天下观。
二、天下秩序的瓦解与“天下主义”
在近代以前,中国人秉持此一天下观处理中国与周边民族之关系,无往而不遂,无至而不通。近代以后,西方挟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至少在当时,传统之天下观难以维系原有之秩序。
依许纪霖教授的分疏,传统天下主义发展至近代,产生了“种族论”与“文明论”两种极端形式。种族论“现成地用中国特殊的种族与历史建构国族的‘我者’,但这样的‘我者’却以排除‘他者’的文明为前提,具有‘自我幽闭症’性格”。
文明论“以西洋为标准,夷夏之间换了位置”,其“在获得了‘近代’的同时,却失去了‘我者’的主体性,无法建立自身的国族认同。”许纪霖教授又从种族论与文明论两个极端之间,区分出“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绝不排斥世界的主流文明,同时又追求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新天下主义则“不以中西为沟壑、古今为壁垒,而是追求全人类的普世文明。”从上述分疏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把“夷夏问题”转换为“中西问题”。而无论是种族论与文明论,还是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均以一强大的西方文明为思考前提。
事实上,自一战以来,西方文明同样亦面临“该怎么办”的问题,一如斯宾格勒所宣称的那样,西方正走向没落。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使得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兴起的“战国策派”与九十年代复兴传统“天下主义”的叙述中,来观察此一转变。
1940年,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以“形态史观”对抗“普遍历史观”,认为“没有普遍史,只有诸文化的兴衰起伏,没有人类文化,只有不同的文化体系”,学界称此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派”的产生,自有其国难当头,需挺立民族自信心之背景。
但其用“对抗”之观点来审视中西文明,并没有真正领会中国文化之精髓。1990年后,李慎之、盛洪、赵汀阳等学者重提“天下主义”,郭沂、李纪霖、姚中秋、白彤东、干春松等教授继之。“天下主义”之特点如前所述,一方面,非采取文明对抗,而是承认不同文明可并存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以先进文明“化”其它文明,最终进至太平之世为目标。
三、“天下主义”以自我修德为先
同“战国策派”一样,“天下主义”复兴亦有其社会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多,随之亦需文化上的自信与之相配。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崛起的条件正一一具备,故其一次又一次从文明对抗的角度,抛出“中国威胁论”。
亨廷顿之《文明冲突论》,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及其与伯恩斯坦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是此类论调的代表者。“中国威胁论”者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以崛起之中国会分享他们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天下主义”所主张的并非一己之私利,而是“义利合”“以美利利天下”,让天下之万物各得所利。
更为重要的是,“天下主义”是一种“躬自厚而博责于人”的秩序设计,它内在要求自我修德为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修身”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从横向的角度看,个人先修身、再治国;从纵向的角度看,为政者先修身、百姓后修身,本国先修身、他国后修身,此亦是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区别。
孟子讲“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霸道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即表明为政者修身之缺失,德行之不足,仅仅依靠暴力手段使民服从、使他国服从,此所谓为政者不修身而求百姓先修身也。王道却是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表明为政者修身之不倦,德行之充沛,然后百姓中心悦而诚服。王者以此之民而安之教之,使得人人各遂其性,则“天下主义”于此为备。
学界关于“天下主义”的思想,还在继续阐述着。我们不能因有“天下主义”的理想而忽视现存的“文明冲突”,亦无须“使得人人各遂其性”的太平之世看似遥遥无期而止步不前。于此一高唱自由,极力主张价值多元之世,更需吾人坚守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