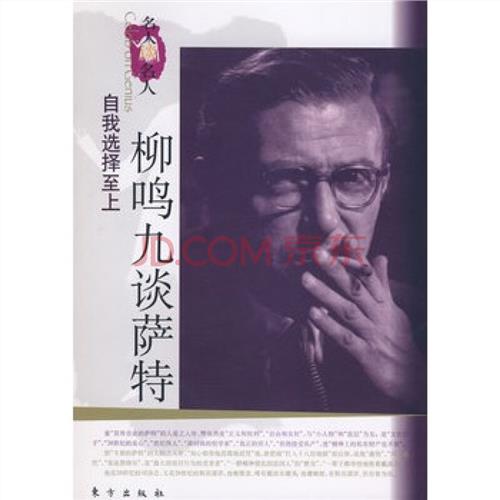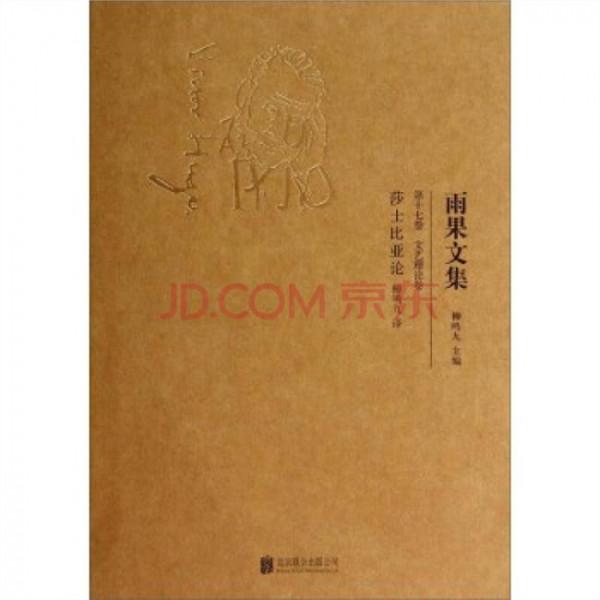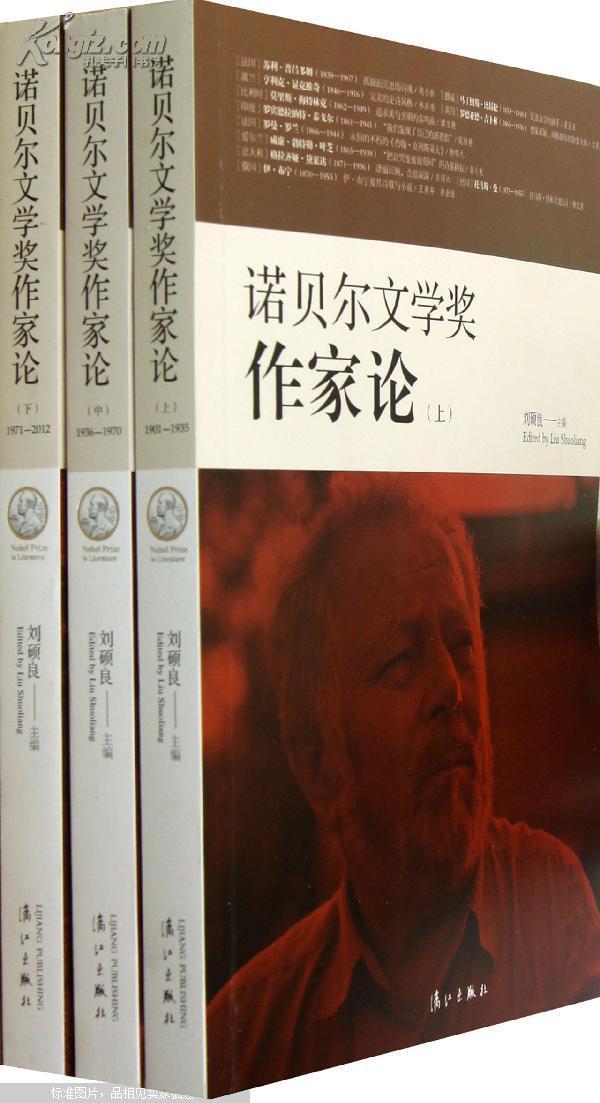思想者自述文丛•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
我的确做过一些事,有了一些学术文化劳绩与社会影响,溢美之词也听了不少,现在轮到我自己来说自己,自己来剖析自己,自己来评论自己,我该怎么办?
综观中外古今的先例与世态,办法显然不止一个。
最通常的做法是:固本守成。既已有所作为,功成名就,最明智的做法是,正襟危坐,不动声色,谨言慎行,不苟言笑。切忌言多必失,敏感的问题一定绕开,有暗礁的险处一定远离,明面的事情讲得周到圆满,风言风语的事情讳莫如深。
总而言之,严谨严谨再严谨。在表述自己、倾诉自己、袒露自己上,保持着高度的理性与自制力,已有作为业绩,何需多言,固本守成足矣,以求善始善终,功德圆满。这是一种无可厚非、本分而正派的常规做法,屡见不鲜。
之二,树碑立传。高奏凯歌,扩大声势,乘胜而为,在已有的作为上,趁势扩充成果。先夯实基础,把不完善的地方修饰修饰,把尴尬的地方掩盖掩盖,把说得过去尚有可取的地方增色添彩,把见不得人的地方涂抹涂抹,把光彩的地方增色增色,形象得完善,高度得上调,成果劳绩的名单得扩充增添,内涵得加重,意蕴得深化,影响得扩大。
总而言之,放大成就,拔高身姿,美化形象,粉饰缺陷,以高、大、全的形象示人,以求对世人有典范教育作用,令人膜拜,甚至流芳百世。
此外,还有一种更加非常规的做法。简而言之,就是报告文学的客观叙述与小说的艺术虚构相结合的办法,补全、增彩、修饰、扩充、想象虚构、艺术构思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这种方式,一般人是做不出来也不敢做的,只有特别胆大包天的勇者,才敢于这么做,而且无一不是为了一个大企图,为了一个大目标,为了一个大用场。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如实说来,直抒胸臆。这是一种最正常、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最不容易做到的方式……如果要举出什么范例的话,我想卢梭的《忏悔录》与萨特的《文字生涯》应该算得上。
所有这些办法,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需要,各自的理由,本来,每个人愿不愿意谈自己,如何谈自己,谈什么不谈什么,这本身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自我选择,甚至可说是他的天赋人权,至于真实度、由衷度,意义与价值,作用与影响,那就只能任他人评说了。
我怎么做呢?报告文学的实述与小说人物虚构塑造相结合的那种奇特的方法,我当然是不会沾边的,且不说屑不屑于、耻不耻于这样做,至少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没有这种自我美化、自我理想化的需要,因为,我既无任何大企图、也无任何大计划。
树碑立传的办法,我也敬而远之。我是深知自己的斤两,自知绝非一块值得树碑立传的料;而且,即使自我膨胀,敢放开胆子去做,也不可能达到“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境界,更不用说“流芳百世”了。我们这个行当就是在文化之桥上干点搬运活,即使是“功成名就”,其影响期不过多则十几年、几十年,如果竟然企图树碑立传,岂不流于笑话?
我也决定不采取固本守成的办法,因为,要细心地包裹自己,周密地层层设防,做起来挺费劲、挺累的。我有些偷懒,不愿意费这样的工夫,而且就年龄来说,已身临墓外,似乎也没这个必要了。
想来想去,对我来说,最适合的办法,那就是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忠于自我,如实道来,直抒胸臆,这样做,省事省力省心,而且有一次自我袒露、自我倾诉、自我宣泄的难得机会,积淀了这么多年,郁结了这么多年,能有一次释放,岂不是一件痛快的事,甚至也可说是一件幸事。
古代治洪有夏禹疏导之策,医术治郁结有舒解之方,安慰悲伤之人有“哭吧,哭出来就好了”的开导语,自我倾诉、自我宣泄,说不定倒有益于健康,有助于延长寿命,何乐不为?
我之所以这样想、这样做,也多少与我的彻悟意识有关。关于彻悟意识,古今中外的先贤,均有不少高论,《红楼梦》中的色空说与《好了歌》,就是中国彻悟意识的形象表述,曾经影响了马尔罗、萨特、加缪的帕斯卡尔关于人的命定性哲理,则是法兰西彻悟意识哲理体系的一个源头。
“彻悟意识”,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种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我生造出来的一个术语。我所理解的彻悟意识,说得俗一点,就是看透了、看穿了、想通了。我在书斋生活中,拾得先贤的牙慧,多少还认识到了个体人是脆弱的、个体人是速朽的,个体人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如西西弗推石上山。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既看不到开头、也看不到结尾,永无穷尽、永无终结的时序中,个体人是渺小到了不能再渺小的程度,就像一根速朽的芦苇。
历史上那么多实在而辉煌的事物,从华丽的宫殿到“笏满床”“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到头来都已经烟消灰灭;历史上那么多典籍都已经尘封泯没,何况是自述文字中故作姿态、做作装扮、添彩美化、虚张声势,最后不过是白费力气,还不如顺乎自然、求真求实。
本来活得实在、活得真实,才是整个人生的真谛,何况写作,特别是写自己乎?这该是有为者的胸襟与风度,这样做,何尝不又是一种作为?
基于以上理解,我在自述中要求自己诚实面对自我、面对世人,讲实话、讲真话、直抒胸臆、如实叙说。关于自己写自己的文字,我钦佩、仰慕两本书,一是卢梭的《忏悔录》,二是萨特的《文字生涯》,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写得真,不掩盖自己的缺陷与毛病,做到了有疾不因自我讳。我曾不止一次为这两本书唱过赞歌,今天轮到我来写自己,岂能说一套做一套乎?
这便是我写《回顾自省录》的基本立场。
当然,我们任何一个人,讲任何话,特别是要形之于白纸黑字的话,面对人群与社会的话,不能不受到时代、社会、人群以及制度规范、人际关系、道义责任等各方面的制约,哪些事能讲,哪些事不能讲,如何讲,讲到什么程度,都大有讲究、大有忌讳。
因此,有些话题能不能碰尚需“与时俱进”,以待时日。要绝对地讲实话、讲绝对的实话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讲真话、讲实话,在很多时候并不决定于讲话的人,而决定于客观的条件、规范、人际关系以及道德标准。不言而喻,我这本书作为自述自省,不能说是完全的,也不能说是彻底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至少可以说清楚我是怎么一个人,我是芸芸众生中怎么一个凡夫俗子,我的一些事情是怎么做出的。我并不想藏在严肃理论与学术术语所织成的意识形态厚厚帷幕的后面;我并不想在富有诗意的文化面纱之后若隐若现;我也不想在我那些人文书架的左右,借文化的光彩照亮我自己;我也不想穿着或闪闪发亮或高雅美观的外衣,呈现为一个光亮的形象。
我想,我也只应该如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赤着膊臂面世。这是思想者的本性,也是思想者的软肋,这是思想者的命定,也是思想者的使命。在这本书里,我正就是着力于讲清楚两件事:我不过是这么一个凡夫俗子式的人;我所做的事,不过是如此这般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