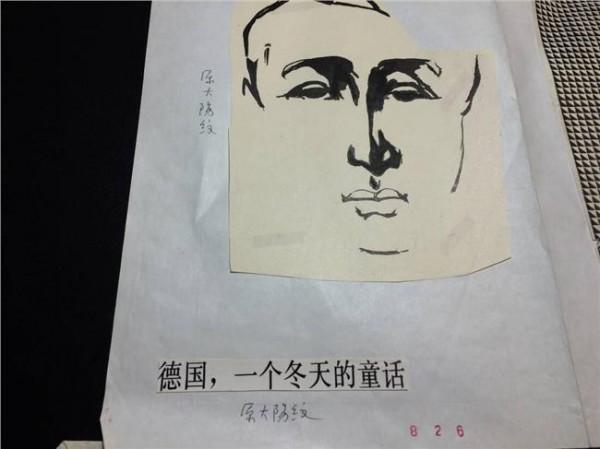遇罗锦的儿子 遇罗文:哥哥遇罗克的故事
对于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从此我懂得了抗争,哪怕对方是硕大无比的\"权威\"。
虽然他的操行评定是\"中\",然而他的品德是那样高尚。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1959年,父亲被教养没有工资,全家7口人(姥姥、父母、四个孩子)只靠母亲的70元工资维持生活。有一天,刚上二年级的弟弟去买冰棍,人家多找了钱,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对罗克说了。罗克严肃地说:\"多找的钱不是你的,你应当送回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带着弟弟把钱退回去了。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比如熟识的人用三轮车送他回家,他会把上衣往上拽,脑袋缩在领子里。他以为人家回头看他,会以为他没了脑袋而吓一跳。他好做鬼脸,甚至还做着鬼脸照了一张相。
他也爱和大人开玩笑,但不失礼貌,称呼都要带着叔、姨、爷、奶,严格要求我们对长辈说话一定要用\"您\"。
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
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 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他高中毕业以后,准备下一次高考那一年,只要姥姥出门,就由他给我们做饭。我们放学回家,先看见他贴在门外的菜谱。每次要做三、四个菜,古怪的名字勾引起我们的好奇,但吃起来全是一个味。还是母亲发现了奥秘,只要家里有的作料,他都要放全。
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这时候,我家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7口人只靠母亲70元工资生活。母亲希望哥哥早日参加工作,协助她共同支撑这个家,但是更希望她这个才华横溢的儿子不被埋没,她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向来心直手快的姐姐说:\"不是就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进了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个简易的桌子和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姥姥和母亲没少为催他睡觉操心。
初入社会的哥哥
罗克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读完一本都要作读书笔记。他每年有一套读书计划,数量是很可观的。到农村后更是抓紧了每一分钟,正如他给自己床头写的横幅:\"分秒必争,珍惜生命。\"
他在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个月回家时都要换借几十本书。同时他也鼓励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多看书,常让我和他一起去借,以便我能挑几本我想看的。因为我那时是初中生,还没资格到市级图书馆办借书证。有时他索性写张目录,让我替他连还带借。
本来图书馆规定非常严,不允许借书证给别人用,可是一看是他的名字,没有人好意思点破。原来他和馆里的人都很熟,每年还参加那里举办的新年文艺晚会。我只看了一次,他表演的是,朗诵陆游的《钗头凤》。
姐姐和弟弟就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俩也想利用哥哥的借书证,姐姐让弟弟冒充哥哥,因为她是女的,装不成男的。弟弟才十一、二岁,与成年人相差甚远,人家不好再给面子。
当时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少量非花不可的钱以外,大部分都交给家中使用。他没有任何需要花钱的嗜好,相反他每月还尽量节省一点钱给我们买些书。在这些书上,他还常常写上一些题词赠言。
哥哥在农村时,有一阶段租住在社员家里。据社员反映,他每天都要看书到后半夜,因此得了神经衰弱。无论分配他干什么,他也总带着书,有空就看。他最喜欢被分配去看水泵,因为看书的机会特别多。在他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对书有了浓厚兴趣,如果有空闲时间不看书,就好象对不起谁似的。
哥哥在劳动中是积极努力的。他到菜园后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有时还带工。我们从城里找他,他也从不放下手中的活或提前收工。有一次我刚到,下起了小雨,社员催他快收工,他故意不着慌不着忙地说:\"房檐流水就回去。\"
我和姐姐在他那里住过几天,晚饭后带我们去散步、体会大自然的温馨。他不无得意地说:\"这里空气多好呵,你们闻,还有一点儿大愤(和)香。\"旁边一位当地青年说:\"我可闻不着\'\'大愤(和)香\'\',只知道大愤(和)臭。\"
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临时工,累得实在不行,原因是缺乏锻炼,干活也不得法。 罗克的群众关系特别好:有人找他哭诉委屈,有人向他倾吐苦衷,有人请他调解纠纷,有人求他排疑解难。甚至一位因为出身不好与恋人被拆散的青年请他为女友写了首情诗:
\"春怀动了,却是春情少。
梦落君边君不晓,风貌依然英俏。
别来不忘叮咛,如今苦借雄风。
何时携君玉手,相凭天上霓虹。\"
他走到哪儿都有社员和他说笑,他们亲昵地叫他\"伊拉克\"(因当时市场上到处销售从伊拉克进口的蜜枣,而遇罗克的名字中又有个\"克\"字,所以社会员们就顺口戏称他为\"伊拉克\"。)他从不摆出有文化的架子,他讨厌说话咬文嚼字。他常对我们说,要增加点群众语言。
他从不歧视任何人。农村有歧视养老女婿的坏习气,罗克则反其道而行之。
据说有一对社员在婚前怀了孕,举行婚礼那天没有谁去参加,只有罗克参加了婚礼。
他也痛恨一种人。那时正是三年大饥饿时期,许多同事凑钱买了两盒糕点给一个住院的病人,由公社一位领导送去。而那位领导在小汽车里偷偷藏起一盒,被司机发现了。哥哥认为这种人比明火执杖的小偷、骗子更坏。
我们只听到过一次他嘲笑那里的人,那就是公社两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后来让台下的听众举手表决以定胜负。
罗克在农村中,更多地看到了\"血统论\"这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它比城市暴露得更彻底。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更使罗克认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更加刻苦地练习写作。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张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都是一样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罗克写了大量的文章投给报刊,但绝大部分或因\"标新立异\"或因\"出身\"而不能采用。发表的只有1962年《北京晚报》上一篇散文《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大众电影》上影评文章《是古代歌仙还是现代歌手》。在当时对影片《刘三姐》的一片赞扬声中,唯独他在影评中提出了该片还存在某些不合情理之处。
他还写过一篇大鼓词《焦裕禄演戏》,北京曲艺团曾演出过。他对焦裕禄还有些赞赏,他总说:不必要求太高,如果每位领导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还想着劳苦大众,就太好了。
美国的黑人,日本的贱民,印度的首陀罗都成了他关心的对象。他想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他非常欣赏印度影片《流浪者》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揭示\"血统论\"的本质:\"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更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中一段精彩的论述而折服:\"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1964年初,罗克的神经衰弱已很严重,他离开农村回到城里,临走前他在自己住的小屋墙上还留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哥哥当时作的两首词,正反映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
游仙
咏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欲把乾坤搂,千古奇峰人共有,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山下渺渺茫茫,来路崎岖征路长,那堪回首眺望。
无题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哥哥返城
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这间小屋刚刚能顺着放一张单人床。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这间小屋又黑又潮,被褥必须经常晾晒。尽管如此,哥哥还是非常满意这间\"书房\"兼\"卧室\"。
他的这间屋,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版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我们那时侯办报,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哪天能出、应该着重宣传的是什么事。所以和哥哥要稿,全是急茬儿。哥哥向我们做了承诺,只要头天告诉他,保证第二天交稿。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一两万字的大块文章,顶多再加一个白天。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三十年了,我永远抹不掉这样一个幻想——也许我再次走进这个院落,又看见从小煤屋门玻璃上透出熟悉的橘黄色灯光,我轻轻拉开门,发现哥哥依然在灯光下,微微驼着背,头也不抬地伏案疾书,还是那样聚精会神地为《中学文(和)革报》赶写伸张正义的文章……为了不让现实打碎这仅有的幻想,至今我也没有勇气跨进这个院子。
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总是严格按作息时间去做,几年来从不间断。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外语、宗教……读书占用了他从早到晚所有业余时间,熬到后半夜是经常的。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也在为自己的事业锻造一把锐利的宝剑。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中国的孔、孟、墨、老,古希腊的柏拉图,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了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可惜,他不能够做到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在他快要被捕的时候,有一次说:\"现在我才知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还正是胜负难分,如果能看到现代唯心主义的著作多好啊。\"
回城两个月后,罗克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编写资料的合同工。尽管任务完成得出色,但\"父母都是右派,本人是社会青年\",已使好心的人望而生畏,不敢长期雇用。后来到蒋宅口小学和小牌坊胡同小学当代课老师,他很热爱这个工作。
虽然只是临时代课,但他对学生非常负责。他曾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书签、玩具作为奖品奖给学习好的学生。他对学生并不严厉,而且善于启发学生,他曾把一个乱班变成优秀班集体,受到表扬。但是,不久也被辞退了——一翻档案,谁敢要父母都是右派的人?但是学生和他一定建立了非比寻常的感情。因为\"文(和)革\"开始,各学校都在打老师,他教过的学生来我家好多人看望他,恐怕他也受到虐待。
一片混乱
1966年初,吴晗首先遭到非难——报刊上对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许多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长者,叹息着断定:\"又要来一场运动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