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司马南
在社会上,我比小混混更混混;在追求知识与认识世界上,我比知识分子更知识分子。
我学的是商业经济,后来一直是搞经济评论的,这有许多人不知道。江湖打头这么多年,有时是身不由己。我并没有刻意要扮演什么角色,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别人给你贴的标签,一经贴上,要改过来也不容易。

不过这也让我嗅觉更加灵敏。神功大师层出不穷,故事就不会完结。前不久的李一水下憋气,意念控制电流,男女双修以达到长寿,全国有三万弟子,知名人士也跟着修炼,我一看就知道又是一个骗局。
方舟子被打事件后,一些媒体要我谈谈看法。我认为方舟子被打是当年的我被打的情景重现。在和平年代,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在,谁愿意不去挣钱而去做这种事情呢?但我觉得男人不在挣钱多少,而在于需要时就要挺身而出捍卫社会正义和真理。

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大胆的怀疑论者,一个不受束缚的理性主义者,有人说看我面相是一脸的傲气,其实我能有什么架子?五短布衣、贫寒人家子弟而已。但我对那些所谓的高贵者是藐视的,我并没有得罪他们,只不过他们从我脸上、眼睛里看不到低眉顺眼的表情罢了。

在社会上,我比小混混更混混,有人说我无赖,无知,无聊,也有人说我是一条好汉,桀骜不驯;在追求知识与认识世界上,我比知识分子更知识分子。
平时我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就是喜欢看书,写字,想事,心里有想不完的问题。

你问我现在在做什么,现在我是一个自由说话人,撰稿人。在大学讲课,北大、清华……在各种论坛发言,在电台当主持人,还当评论人,评论天下热点,没有人规定我,我很享受这样一个表达的过程。
我经常会受到邀请,像入朝作战座谈会,中国马铃薯改良,计算机理论研讨,亚洲金融高峰,泰山文化,美的标准,世界怀疑论者论坛,宗教发展,等。
我没有固定的专业方向,不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我也尝试改变自己。上世纪90年代我应英达之邀,在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扮演从伏牛山下来的司马大师。后来也拍过多部片子,那是在演自己。这几年我也演起别人来,在王好为的大片“徐悲鸿”里,吴刚演男一号,刘晓庆演女一号,我则扮演日本东亚银行的岩下次郎,这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操着生硬的日本“中国话”,软硬兼施胁迫齐白石,那一段台词受到高度肯定。
我说我是老来玩票,不似你们大腕。演戏很快乐,它使我体会到了多彩的人生。
2003年我在北京东城区当选人大代表。我感觉代表难当,官也难当。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2003年我在北京东城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并当选。
原来以为地方代表很好当,了解情况后才发现以往的自以为是很可笑,开始佩服、同情起那些基层官员,进而对基层政权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了理解和肯定。
第一次去参加区人大全体会议。会上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台上的人念到“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我不举手,台上人念到“不同意上述名单的请举手”,我没有举手,台上人念到“弃权的请举手”,我举了手。
当天晚上,好几拨人主动来找我吃饭,就为举手这件事情。这些人希望和我结识,做沟通工作。全体大会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这种事,所以有点乱。主席团也对我说,你干吗举手弃权啊?跟着举手通过就完了。要以大局为重,咱们以前没这个风气,要开成一个祥和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其实海淀区那边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在这边是独一份儿。我并不认为自己举手弃权有什么唐突之处。我一不是反对人大代表制度,二也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所以弃权,是因为不了解名单上那些人。不了解,那么同意和不同意都是没有道理的,弃权才是正常的,对吧。但别人不这么看,他们怀疑我是否另有想法。混熟之后,他们对我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很警惕啊,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开人大会时,区委书记到我们团参加审议。书记很客气,但各单位与会代表一见书记来了,就过分热情了。我告诫书记说,您到我们这儿来,身份是普通代表,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现在应该认真地、耐心地多听一听各位代表对本区政府工作的意见。人家当了代表特别谦卑,我不是。我反感这样,尤其是反感见到当官的一脸谄媚。
干了四年,第二次选举我就没再参选。感觉代表难当,官也难当。以前谁给我点事儿,我老感觉,这还管不了?后来发现没一件好管。这些难管的事儿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小到建公厕、换电表、规范用水、争取低保、捕杀蟑螂、文明养狗……没一件不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的,非有技巧和耐心不能做好。那些发议论太随意的人,应该体验一下基层人大代表的滋味,尝试管管这些最简单的事儿。
当人大代表才发现,现今中国,真的一切都靠竞争性民主投票来决定怎么办,那这事儿就没法办。25年前,说到民主,我觉得这个词简直好到了完美无缺;现在嘛,你说民主,很好,可我一定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人痴迷制度万能,选举万能,以为一搞民主,一切OK,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应该让他去基层当代表,最好直接当居委会主任、街道主任。
我认为假如没有共产党聚沙成塔的作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主心骨,处于紧平衡状态下的转型中国要稳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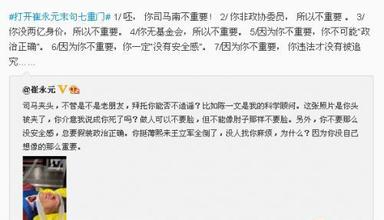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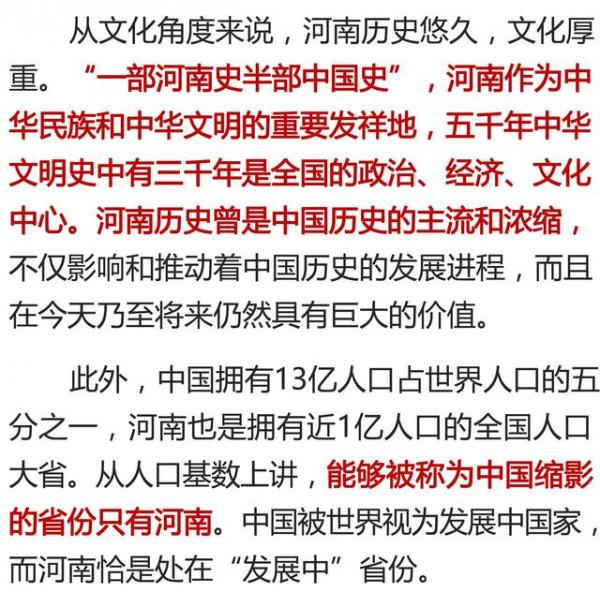


![>司马南为无耻小人 [原创]司马南你做为中国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https://pic.bilezu.com/upload/f/4e/f4eced60800ae09b3d7892e76fbda778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