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精神:上音永远的宝藏
从1980年代起,我的研究领域由中外歌剧史论逐渐拓展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遂通过大量史料的研读,对母校的发展历史及其艺脉学源,始有一些粗浅认识和理性思考。值此母校校庆90周年之际,为不负《音乐艺术》和洛秦教授约稿之忱,乃将它们拉杂写来,献给上音新老校友,共庆母校90周年华诞。

从萧友梅、黄自以降,建校90年来,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文革”10年,还是改革开放至今的41年,上音在各个专业领域均涌现出大批在国内外声名卓著的优秀音乐家,为我国专业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其中,若论与上音艺脉学源最深、对上音建设贡献最大、为中外乐坛所一致公认的杰出代表,当首推国立音专作曲专业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新时期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作曲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社会活动家贺绿汀。

贺绿汀的音乐人生是一部传奇大剧
关于贺绿汀的光辉一生,此前已出版的史料、文献和研究论著汗牛充栋,涉猎他的音乐生涯的各个领域;今天在欢庆母校90周年华诞之际重新谈论贺绿汀,我以为,最为紧迫也最有价值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贺绿汀精神。

贺绿汀的音乐人生是一部充满传奇性和复杂性的历史大剧。它的传奇性和复杂性,首先来自于贺绿汀所处那个颇具传奇性和戏剧性的伟大时代——当他以一曲《牧童短笛》崛起于中国乐坛之际,正逢蔡元培、萧友梅等人以“启蒙”为旨归、大力倡导“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以创造中国专业新音乐,且经牛刀小试便已取得喜人的初步成果的时代;然而随后不久,便因日寇入侵而将中华民族逼入国难当头、全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时代。

中国社会宏观语境的这个陡然反转,在贺绿汀这部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历史大剧中,犹如一个突然闯入的戏剧性事件,在当时中国乐坛的主流话语里,非但由此形成了所谓“学院派”和“救亡派”双流并泻局面,也将贺绿汀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音乐家统统裹挟进来,并且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革”中乃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所谓“救亡派”与“学院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常常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革命”与“反动”等等政治名号所取代而已;更重要的是,在“救亡派”音乐家的心目里和长期以来的左翼音乐语境中,所谓“学院派”,实际上就是国立音专的代名词。
谓予不信,除在大量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极方便地找到这类表述的确凿证据之外,只要看一看1960年代拍摄的电影《聂耳》,摄制组对端坐在考场上那个主考官、国立音专某教授的形象刻画和做派描写,就知道左翼音乐家眼中所谓“学院派”的嘴脸竟是如何不堪了。
如此久而久之,以至于后人读史,导致许多人常常误以为,抗战爆发之际,“学院派”作曲家都是置亡国灭种危险于不顾、躲在琴房玩艺术的逍遥派、怕死鬼,甚或是日寇的帮凶。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大量铁的史实(这里暂不列举)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种看法是某些左翼音乐家横加在以萧友梅、黄自、贺绿汀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家头上、完全扭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不实之词,纯属极左偏见,应予推倒。
“吕贺之争”大剧铸就了贺绿汀精神
在贺绿汀这部人生大剧中,有一位极重要的角色不能不提——吕骥。他与贺绿汀,两位湖南老乡、音专同学、革命同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音协的正副主席,秉承各自的人生诉求和艺术理念,构成贯穿全剧的人物关系,生发出不同的戏剧行动,自1930~1940年代关于救亡歌曲的论争始,到1950年代围绕《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和“拔白旗”运动中对钱仁康“黄自研究”的批判、1960年代关于德彪西问题的“讨论”,直到1990年代在“音乐思想座谈会”前后围绕音乐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争鸣,在两人乃至两个阵营之间敷演出一部横亘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情节曲折生动的连台本戏——“贺吕之争”。
当然,“贺吕之争”并非仅是两个人的戏剧,其精深内涵亦非单纯用“学院派”与“救亡派”的复杂纠葛所能概括。实际上,这部连台本戏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思潮史的生动缩影;正是在这部悬念迭出、精彩纷呈的连台本戏中,铸就了贺绿汀精神。
此剧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就在于,第一,贺绿汀不同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诸人的一个重要特性,他不仅是个热烈的爱国者,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早年加入共产党并投身过湖南农民运动;第二,贺绿汀也不同于左翼新音乐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聂耳、麦新诸人,他在国立音专随黄自接受过系统专业音乐教育,掌握了专业音乐创作所必需的艺术修养、作曲技术与技巧,能够自由驰骋于不同体量、样式和风格的声器乐作品之间。
从这个角度看,贺绿汀既属于“学院派”,也属于“救亡派”,且分别以大量各种主题和样式的优秀作品、理论批评文本和革命活动,证实了这种“跨派”双重文化身份的无可置疑性。
就此而论,在我国1930~1940年代的作曲家中,唯有冼星海(也是音专校友,且有留法学习作曲的经历)可堪与之比肩。然而可惜的是,这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在苏联卫国战争中饱受颠沛流离和疾病缠身之苦,竟然天不假年,中年早逝!
聂耳的命运则更加令人唏嘘痛惜——这位天才的、曾奉献出众多不朽救亡歌曲、被奉为我国左翼新音乐运动领军人物的年轻作曲家,尽管当时有不少左翼音乐家将他神化,但他依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作曲技术武装方面的确存在某些短板,乃下定决心赴苏联深造;若非转道日本时不幸溺亡,又有谁敢断言,学成归国、眼界大开、技术武装全面的聂耳,又岂能将自己的音乐创作领域仅仅局限于“救亡歌曲”或“革命歌曲”这一脉?
与聂耳、星海相比,贺绿汀本就年长几岁,又让他的生命旅程能够行进到耄耋之年,成为中国音乐界为数不多的长寿老人,令他享有较之聂耳和星海更长的艺术生命、更多的创造时空;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苍天又是如此无情,竟在他漫长的艺术道路上,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数十年间,布满明枪、暗箭、地雷、悬崖,随时都有中枪、着箭、踩雷、坠涯的危险。
贺绿汀之所以是贺绿汀者,是他永远不由命运摆布,不信虚妄之言,抱持坚定信仰和爱国热忱,满怀振兴中国专业音乐艺术的崇高使命感和神圣责任感,以精深的音乐素养、职业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每每独立寒秋而作登高之呼,频频身陷险境而发铿锵之论,不以万全求苟且,唯从九死觅新生,由此在20世纪的中国乐坛上造就了这位大义凛然、众望所归的领袖,竖起一面迎风猎猎、永不褪色的旗帜。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鲁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乐坛绝大多数音乐家都将贺绿汀称之为“硬骨头音乐家”,并公认他就是中国音乐界的鲁迅。由此我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概括同样适用于贺绿汀;贺绿汀精神就是鲁迅精神在中国乐坛的具体表现,是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时代语境之下,鲁迅精神遗产在中国音乐界的传承、弘扬和发展。
——以上为节选,更多内容请关注“音乐艺术”!
作者简介:居其宏(1943~ ),男,河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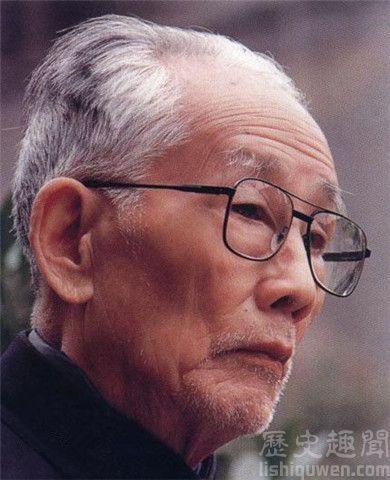

![>[视频]摇篮曲 贺绿汀>>贺绿汀的歌曲>>贺绿汀音乐厅](https://pic.bilezu.com/upload/c/bd/cbd2fff8065ad2184e752eb06176108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