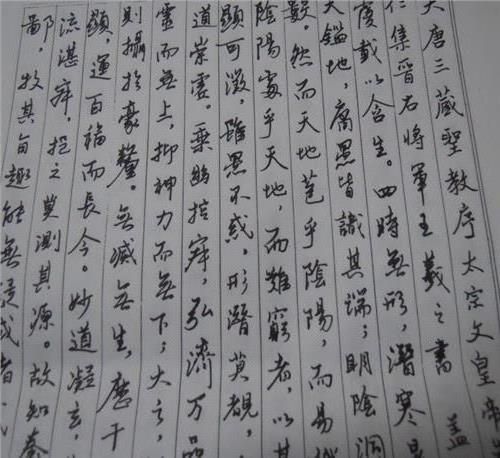王叔文是王安石吗 《谪龙说》“是用来比喻王叔文的”吗?
摘要:张铁夫先生认为:“《谪龙说》并不是柳宗元的自喻,而是用来比喻王叔文的”,其玄机暗藏在“被緅裘白纹之里”中,“緅裘”象征着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品服的深青色,“白纹”表示王叔文正服母丧。
本人认为这是理解拘谨所致。“江州司马青衫湿”以青衫喻司马,柳司马亦以此自喻。柳宗元贬到永州不久也服过丧,服的是唐顺宗之国丧、知遇之丧。除之,还有四条不容否认:一、柳宗元是李唐王朝的忠实奴仆,不可能反对新皇帝及其圣旨;二、王叔文和柳宗元处分的时间差是36天,期间不可能串连,不知道王叔文具体情况;三、他们都明白这是“建桓立顺”,生怕如汉代李固似的祸及自身及其家族;四、柳宗元倘硬要把自己和王叔文粘在一块,就只能和王叔文一样下场,就不会有“八司马”。
因此,《谪龙说》不是“比喻王叔文的“,而是贬到永州之后抒发的一时感慨。
关键词:《谪龙说》;柳宗元;王叔文
关于《谪龙说》的写作时间,普遍的说法是作于贬谪之后,是自喻。只有我的朋友张铁夫认为:“《谪龙说》并不是柳宗元的自喻,而是用来比喻王叔文的。与此相联系,该文的写作时间,也不是在柳宗元被贬之后,而是在被贬之前;写作地点也不是在谪所永州,而是在京师长安。
”①为什么这样说,铁夫兄从“被緅裘白纹之里”中读出了新义,“緅裘”即深青色的帛裘,“白纹”即白色且带条纹的布。该句的全意是披着深青色的帛裘,但其衣里是白色的。
因而指出了理解文章主旨的“关键所在”:一个是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的官阶为从八品下阶,按照唐代严格的等级制,只能服深青色的品服,柳宗元贬永州司马员外为六品下阶,品服当是深绿,由此可见,是喻王而不是喻柳。
二是王叔文被贬期间,其母才死去一个多月,正是居丧期间,因此还得穿上白色的丧服。柳母其时尚在,不存在服丧问题。因此,王叔文在渝州任上,“外面穿着八品官的深青色章服,而里面则穿着白色的丧服”,与谪龙“被緅裘白纹之里”相谐。因此断定该作影射的对象是王叔文。
对此,我以为不然,这是铁夫兄理解文学作品太过拘谨所致。
在2010年永州召开的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铁夫兄提醒我读完他这篇文章再去理解《谪龙说》的影射对象,我便老实地按照他的思路把《谪龙说》再读一遍,关于“緅裘”,尽管我同样理解为深青色的帛裘,想到的却不是从八品下阶深青色的品服,而是白居易那句“江州司马青衫湿”。
白司马与柳司马是同时代人,白能用青衫自喻,柳难道不行!后来我又确实地查了一下“青衫”的意义,标注最详的是“百度百科”,共8义,这里权列相关的5义:1、古时学子所穿之服。
2、借指学子、书生。3、唐制,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唐白居易《琵琶引》:“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后因借指失意的官员。4、泛指官职卑微。5、借指微贱者的服色。这5义皆可成为柳宗元借用这个词自喻的理由。岂能让王叔文独占?
关于“白纹之里”,如果硬要把“白纹之里”象征丧服,尽管柳宗元其母健在,他也绝对有服丧的理由,而且是国丧。因为在柳宗元到达永州一个月之后的“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唐顺宗李诵逝世。除了太上皇的丧举国尽服的常识之外,谁人不知他对“二王八司马”的知遇之恩?身为八司马之一的柳宗元,为这样一位知心皇帝服一回丧难道错了!
否认了铁夫兄仗以立论的两大根据,他的观点便不能成立。尽管后面还罗列了各种皇帝身边的事、为人风格等等问题,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放在任何一位身上都差不多。作为一个稍有个性的封建文人,说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也都相近。
诸如说到“影响重大的四项功绩”:进贤退不消、废除蠹政、反对宦官干政、镇压跋扈藩镇,这些参与革新的,谁不沾边呢?又如“怒而谪来。七日当复”,这些挨处分的,谁不有这样的期待?再如“拟人必于其伦”,所谓“以类相从”,以龙为喻的资格,这些参与革新的年轻新进,谁没抱负?谁不自负?谁不是人中龙凤?喻之为龙,又有谁不行呢!
最后说到居住佛寺,铁夫兄却表现了不该有的主观与武断,用猜测与推理作出结论:这就是王叔文“惟一的精神寄托”,“理想的栖身之所”,“王叔文被贬之后,很可能就是住在寺院里的”,用以比附谪龙“入居佛寺”的文字描写,把“谪龙”即影射王叔文强加给柳宗元。真正住在佛寺的柳宗元反倒不能对号入座了?
我反复在想,王叔文被贬的圣旨下达之后,柳宗元可能写下《谪龙说》以示对王叔文的信任、鼓励与支持,表达自己对唐宪宗处分决定的不满吗?结论是肯定不会。
综观柳宗元一生,绝对是一个标准的、虔诚的儒家信徒,是李唐王朝忠实的奴仆。他与唐宪宗的关系,永远也不是敌对的,对抗的,而是主与仆、君与臣的关系。正因此,他绝对不会反对皇权,不与皇帝唱反调,而唯皇帝的马首是瞻,做皇帝的“孺子牛”。
别看他早不久给王叔文的母亲写过《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对王叔文备加赞赏,那可是唐顺宗在位的时候,王叔文仍然是顺宗的宠臣。现在皇帝换了,对立面都是拥戴功臣,大权在握,王叔文及其盟友柳宗元们,无一不是打击处分的对象,难道他们会选择紧跟王叔文而站在皇帝的对立面?肯定不是,他们衷心期待的只能是皇帝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让他们戴罪立功,此其一也。
接下来对比一下那两次不同处分宣判的时间:
据《新唐书·宪宗本纪》,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右散骑常侍王伾为开州司马,前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永贞元年九月“己卯,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贬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贬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坐交王叔文也”。
从“八月壬寅”到“九月己卯”的时间差是36天。这可是柳宗元们如坐针毡的日子,皇帝下旨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已经向柳宗元们敲响了警钟:当道者正在密切地关注你们,处分马上就轮到你们!
他们因此而诚惶诚恐,因此而不敢乱说乱动,更不敢串连、声援、相互鼓励。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作为领头羊的王伾、王叔文已经处分,业已起到杀鸡儆猴作用,追随者能够全部赦免。
柳宗元能例外吗?面对唐宪宗的圣旨,他有胆量逆旨而行,为王叔文报屈、给王叔文鼓励打气吗?绝对不敢!更不可能打听王叔文贬离长安以后的任何信息,不可能知道贬到渝州的王叔文住什么地方,穿什么衣服和怎样穿。此其二。
据《旧唐书·宦官传》:“俱文珍,贞元末宦官,……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
”这一记载充分表明李忠言、牛美人、王叔文等所谓革新派不是反对派的对手。在他们深得顺宗信任的时候,明知李诵的身体不行,活一天算一天,只有早一点由他们拥立储君,才算靠稳了一个长久的靠山。
然而,他们没有,却让反对派完成了拥立储君的大事,与唐宪宗结成牢固的同盟,彻底控制了朝廷。所以,从反对派拥立储君成功的那一天开始,王叔文集团就已经有了失败的预感。据韩愈《顺宗实录》:“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
常吟杜甫题诸葛亮庙诗末句云:‘出师未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流涕。”这位领头羊业已这样,柳宗元们难道会麻木不仁?还会把病入膏肓的唐顺宗当成自己的后台?并因此和唐宪宗唱一场对台戏吗?应该不是。他们应该和王叔文同时产生失败的预感,没有了底气,丧失了斗志。
又据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证明“永贞内禅”的时候,王叔文等已被隔绝,所谓革新派全被算计。“建桓立顺”的典故出自《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
”其“立顺”过程,可参看《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下》:“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
”其“建桓”过程,可参看《后汉书》卷六十三《李杜列传》:质帝被梁冀毒死,李固等主张立清河王刘蒜,梁冀与宦官曹腾等“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
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鈇锧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州郡收固二子基、兹于郾城,皆死狱中。”王叔文集团中的任何一位都是饱学儒生,谁都知道“建桓立顺”的典故,自然也知道强硬对抗只能成为杀戮对象。后来的结果告诉我们,他们都选择了顺从,只除掉“首恶”一人,其他人得以保全。此其三。
试想柳宗元如果真给王叔文写了《谪龙说》,其胆量固然可嘉,第二次处分就不可能有八司马,只能是“二王一柳七司马”:你柳宗元既然和王叔文关系铁,硬和他粘在一块,对新皇帝处分不满,和新皇帝对着干,你就没有资格享受韩泰、韩晔、刘禹锡等的同等待遇,就不仅仅是“坐交王叔文”,而是王叔文死党,肯定要加重处罚,以至于与王叔文一个样:“贬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或永州)司户”,然后和王叔文一样赐死。
那就没有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了!
这里我要提醒铁夫,千万不能把所谓反动派当成纸老虎,他们既然能够把基本盘翻过来,能够操纵新皇帝,说明他们有心机、有能力。也千万不能期望所谓反动派会悲天悯人,他们正虎视眈眈,磨刀霍霍,盯实了所有镇压对象,稍有风吹草动,必然会痛下杀手。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柳宗元能把自己的头伸向矢志效忠一生的唐朝新皇帝的刀下吗!还是那一个坚定的回答:肯定不会!此其四。
有了以上四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谪龙说》不是为王叔文而写,不是写在长安,而是贬到永州之后抒发的一时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