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法西斯 美最伟大在世短篇小说家乔治桑德斯谈《十二月十日》
问:《十二月十日》是你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你感觉它跟之前那三本书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的,是有所不同。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销量不错。这是件好事,对我来说这很难得。但我认为相对于前三本书来说,它还在语调上面有一些不同。其中那些故事的写作,都发生在一个相当丰富多彩的时期里——在此期间我们家的两个女儿高中毕业,去上了大学。
对于我的妻子宝拉和我来说,这是一段真正的快乐时光,我们觉得这代表着我们某个生活阶段的结束,而我们干得还算不赖。女儿们是我们真正的亲人,我们发现自己与她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没有因此结束或渐行渐远,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非常深厚的阶段。
因此,我们觉得很幸运也很感激——我敢肯定,所有那些能够与自己的孩子建立并保持住真正联系的家长们都会有这种感受,而他们的孩子们也会在外面的世界里活得很好。
这就有点像,哇,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生活中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幸福。我认为这种感受渗透到了这本书里面一些。当然并不很明显——书里没有哪个故事是讲这个的,不过我期盼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能写好一个这样的故事。然而,我的确发现有些与以往不同之处: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当我为故事选择走向的时候,我考虑的选择内容出现了变化——也许可以这么说吧。
特别是我的前两本书,它们可说是我在震惊地意识到生活可以很艰难、资本主义可以很残酷——可以对我本人很残酷——之后的产物。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会是一个新认识,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两本书里的故事说的往往是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以及人们彼此之间冷酷无情等等的情形。它们反映的可能是当时在我头脑里最主要最迫切的真理:哦,妈的,各种事情都会搞砸。而一旦搞砸,有人就会受到伤害,而我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尽管我还是我。
宝拉和我是在读研究生时认识的,我们一见钟情,狂热地堕入了情网,谈了三个星期的恋爱就订了婚——纯粹是典型地被浪漫冲昏了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她是哈克尼斯芭蕾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精英模特公司的签约模特,结过一次婚,曾经游历各地,过得是一种非常激动人心的、众人之上的生活。
我很正确地感觉到,她可以教给我很多东西。于是我们就不管不顾地陷了进去。我们决定马上就想要孩子,于是在蜜月里她就怀孕了——从那以后,一切都飞速地发生着。
我们俩人都是既写作又上班,而且我觉得我们俩都认为我们自己很快就会“出人头地”,取得胜利,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相来说对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去。当我们的长女出生时,保拉正拿着奖学金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师从于托妮·莫里森,而当时我刚开始在一家制药公司上班,工作是技术文献的写作。
但后来她的奖学金用完了,而我的那份工作也没有了。与此同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收获成果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原本计划得更长。
我们搬到了罗切斯特市,我开始在一家环保公司上班,还是从事技术文献的写作,宝拉则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两三节的写作课;我们很忙碌,但并没有出人头地,甚至还可能有点落后了。当然,怎么说这也不算是古拉格式的流放。
我们依然非常快乐,但同时也能感觉到压力,并且认识到,在我们在同类人群里(即周围其他家长们)已渐渐地沦为殿后(尽管大家依然很友好)。另外,我们也可以感到一个严峻的挑战在逐渐逼近,那就是将来孩子们开始上学这事——到那时,金钱以及由它所带来的稳定和灵活性,就会真正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俩都觉得,虽然我们得到了无比珍贵的宝藏——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家——但随后又突然意识到,这一切也是可能真正丧失掉的。我们都明白,穷困潦倒,或者为了避免穷困潦倒而过于辛劳地工作,会消磨掉尊严。而我们也可能会沦为它的受害者。
我认为,熬过这一段岁月并且来到柳暗花明的彼岸,这在我的艺术世界中开辟出了一块新的空间。生活过这25年之后,再去构造一个只有陷阱和不幸的虚拟世界,会觉得虚伪,也不完整。如果你把小说作品当作为真实世界的一种缩微模型的话,那么其中就应该也包括积极的一面,也就是事情比你预想的要好的那一面。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因此,在这本书中,尽管仍然有很多的残酷和黑暗,但我的目光往往被那些事情并没有变得彻底屁滚尿流的情形所吸引,并且问自己,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开始觉得,在书中一些小说的某些关键之处,最有意思的美学走向——或者说情节转折——是摆脱我所习惯了的灾难性结局。
与此同时我也逐渐有了一个写作风格上的演变,这可能跟我所做的以旅行为基础的纪实文学写作有关。我觉得自己不再特别在意非要把每一个句子都写得无比绚丽。这意味着我能拓宽一下,去写一些并不怎么火爆的故事(如《胜利冲刺》、《小狗》或《艾尔·鲁斯顿》),这些故事的背景和情节都更接近现实主义一些。
问:的确,在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在最后都出现了某种解脱、拯救的行为,或者至少是出现了解脱、救赎的希望。不过,这些拯救几乎都发生在千钧一发之际:它们已经与暴力交织在一起,或有可能交织在一起。例如,在《逃出蜘蛛头》的最后,唯一可能的正派行为就是去令人不忍目睹地自杀;再比如在《家》的结尾几行文字里,一个即将大开杀戒的绝望男人却多多少少是在乞求别人来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我想,即使这些故事也还是莫名其妙地濒临屁滚尿流的处境边缘,是不是?
答:是的。我觉得要让一个故事有能力具备拯救色彩、避免屁滚尿流,就是去设想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屁滚尿流的情形。(话说到此,我有点后悔使用“屁滚尿流”这个比喻了)而从上面我所写的这些,某些读者可能会误以为这些故事比它们实际上更轻快更感恩了。
一个故事在写作期间,其实主要就是个技术对象。尽管当我们事后谈论起它时,往往喜欢把它作为什么主题或世界观或意向的化身。或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它是在修改过程中迅速做出的成千上万个决定的结果。我的写作习惯之一,就是老话所说的那种“把孩子放到悬崖边”的方法。
这大概算是从我的呆板天性中诞生出来的一种方法。在一篇作品中,我会毫不掩饰地把情感或危险推向高潮。因此,当我觉得我的小说或作品集“更加充满希望”时,那可能只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说法:孩子还是会掉下悬崖,但可能是落到灌木丛里,而不是落到粪坑里。
不过,所有这些都并非在写作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决定。而是在本书中的某些关键之处,当情节转向黑暗或灾难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时——而且也许是最熟悉和舒适的选择时——我却会觉得那种转向没有什么意思,或从技术上来讲没有什么挑战性。因此,其结果就是(我认为),这本书的整体感觉是更充满希望,或者说,它承认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说我以前那些书中的世界观就错了。我依然持有这样的信念,即资本主义有可能会变成一架贪婪而残酷的机器,会压平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我愿意让这个观点与这本书中那种更温和的感觉并肩存在。我的想法是,即使是在这架大机器的势力范围之内,也许也还是会有快乐、正义和满足——有时你会发现自己位于与车轮车轮之间,毫发无损。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艺术眼光”其实只是他在创作期间真诚相信过的各种具体立场的总和,即使这些立场之间可能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形。我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太过严酷了。但我也相信,如果你恰好是那些幸运儿的话,那么其中也还是有很多的美满,尽管这并不能消除现实存在的苦难。这一切都是同时存在的真实,既细微又崇高。
问:你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写作《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了。它是否更适合那段时期——就是当你认为资本主义非常残酷,养家糊口不易那段日子?
答:是的,其中有很多的例子或细节来自那个时期。而且我发现,那些资金紧张的日子非常难以忘却。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个故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家庭中那种非常真实的温情。他们彼此依靠,即使那位父亲走上了歧途,他对自己的孩子们的关切是真诚的,为他们想得很多很多。
这部分——即那些温情——完全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我在他身上,能看到当年身为年幼孩子的父亲的我所具有的某种不良倾向,那就是:当感到歉疚的时候,往往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为她们买些东西来补偿。
我们确实做了一些故事里那个家庭做过的事情,尤其是在信用卡方面: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应该想办法给孩子们提供一种比我们实际有能力提供的水平高出几步的生活水平,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日后会有能力偿还。
《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里的叙事人只不过比起当年的我来稍稍更为过分了一些。他的心地还是好的,但满脑子都是文化上的定势。因此可以说,当他决定“我必须为家里人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他却把手伸进了错误的锦囊当中。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我笔下的故事跟我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不如说是现实生活偶尔可能会引发我的某种情绪或感觉,然后我发现自己在写作中想要再现或提及那种感觉,并为此而精心地选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细节。
问:是的,通常很难在你的作品中看到明确的自传性成分。我想你以前没有过以参与药物试验来替代服刑,也没有在名人拍卖会上一较高下,或在伊拉克打过仗,或拿绳索穿过移民女工们的大脑。然而,我还是觉得在你的笔下有很多你的影子。包括对我们的文化所做的审视——以期找出美国的伟大之处和糟糕之处——而且还有你更为个人化的尝试,去反映出你对家庭,对婚姻,对抱负,以及对自我定位的感受。
答:很早以前我就发现,每当我试着写出直接来自生活中的故事时,结果往往落空。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语言就是不出彩。因此,后来我对自己说,“忘掉现实世界,集中精力让一句话到下一句话的推进更有动力吧。专注于吸引读者,并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把她留住。
“对我来说,主要手段似乎就是句子。我开始专注于写出两三句令我满意的片段。然后我发现——在写作《摇摇欲坠的内战公园》(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时就是如此——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背景和环境都有些卡通化而且张力十足,但我的真实信念和焦虑在这些虚构的世界中却得到了更有力和准确的(同时也是无意间的、哈哈镜似的)反映,远比以往我进行“真实生活”写作时更为准确有力。
而且事实上奇怪的是,这些新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引导我理解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信念,而这是任何理性思维的方式所做不到的。
问:我知道你以前已经被人问过上百万次了,但那些虚构的卡通化世界是怎么变成为你的写作特色的?虽然在你的所有作品中都有着极强的现实元素,但它们的大背景往往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或全然不同的世界。你作为一个作家,创建出这些亦真亦幻的世界,是不是有获得解放的感觉?你是如何做到在“荒诞”和“完全可能发生”之间的平衡呢?
答:“解放”是个恰到好处的词。当初我之所以开始使用这些怪诞的元素,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强行解放自己的手段,为的是摆脱掉我从事“现实主义”写作而养成的某种习惯性写法,那种写法我用不好:我会自动地带上某种口吻,让作品的潜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营地设在河边。营地里的人们在帐篷里就能听到水声。他们躺在帐篷惦记着流水的声音。不久,他们就觉得想要撒尿。这些人经常要撒尿。“我发现,如果我加入一些怪诞的元素——比如一个主题公园或一些鬼魂等等——就能把事情提高几个层次,让我对作品本身的意图、对它应该如何发展不再那么清楚,而这是件好事:我不再能控制它,而只能跟随在它后面,试图弄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故事以及它会走向哪里。
问:你的一些故事正在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您觉得它们被搬上银幕效果会怎么样?你愿意参与到这个进程当中吗?
答:我把两篇小说改编成了剧本:一个是为本·斯蒂勒改编了《摇摇欲坠的内战公园》,另一个是为导演凯尔·麦克法兰改编了《海橡树》(Sea Oak)。这两部片子都还没有开拍,这让我对电影这种形式的热情多少有些冷却。
但我的确很享受改编的过程。它教会了我超越语句,从更大的结构上去看待一些问题。因为对剧本而言,你就算写出漂亮的句子也没什么用处,而对话最好不要太花哨。所以,这就迫使你去思考故事的整体结构——这种思考的结果,有一部分就体现在这部最新小说集的故事当中,比如《胜利冲刺》和《十二月十日》这两篇,我在写作之初就对其中的活动有了一个基本的构想(对我而言,这很不寻常)。
我刚刚把《逃出蜘蛛头》的版权卖给了康泰纳仕制片公司(Condé Nast Films)。不过我得出的结论是,真正出色的剧本是由那些热爱电影如我热爱短篇小说一样的人们写出来的。所以,我决定我还是继续写小说吧。
问:在这部小说集里,你有没有觉得对哪一篇特别有感情?
答:眼下我觉得对《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最有感情。它是我最后一个写完的,而我写它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虽然它有一点点臃肿满溢,但还是能够不断驱使读者读下去的,这也让我感到欣慰。它为我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让我体会到一部小说应该是什么样——既有向前推进的动力,但也有留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容纳漫画式的旁枝。
问:《时代》杂志在封面上称《十二月十日》为今年人们能读到的最佳书籍。你的读书会也吸引来了大量读者。你即将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这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答:换作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对此假装出一些神经兮兮或内心矛盾的反应。但是,说实话,现在我非常享受这种种。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工作,去写下一部作品。我的读者群有所扩大让我感觉非常好。我也很清楚这当中有很强的运气成分:比如《纽约时报》登了那篇报道;那篇文章写得很漂亮很正面,引起不少共鸣;兰登书屋的安迪·沃德(Andy Ward)和其他各位为书的质量做了大量工作,等等。
我非常幸运。因此我希望把它看作是一次奇特的机会并充分加以利用——特别是考虑到下一本书时,把这当作一种鼓舞,而不是被它所吓坏。
(对不起,稍等一下——我刚刚雇的那个仆人把我那张”表扬桌“上的“金元宝”彻底摆错了样子!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过他:“罗德里克,一定要把我的金元宝按照与大金字塔相同的角度来摆好!”这很难做到吗?显然,对罗德里克来说,这有很大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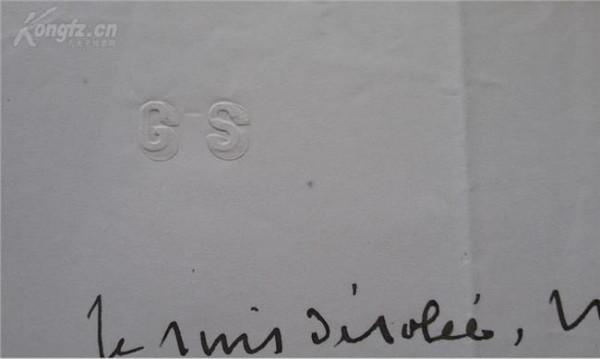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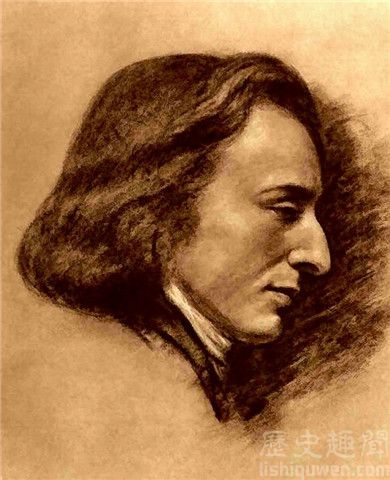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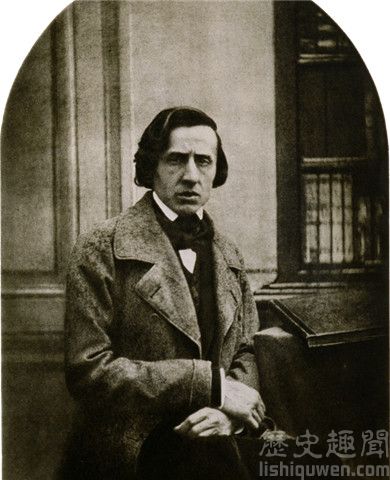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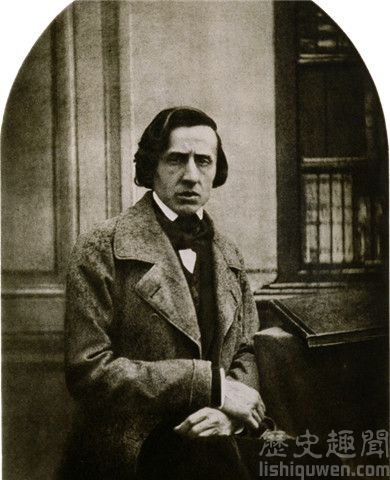




![>乔治桑作品 [精品资料]外国文学评介丛书——乔治桑](https://pic.bilezu.com/upload/9/29/9294b754846347e8f0d0c6f1f7245eff_thumb.jpg)



